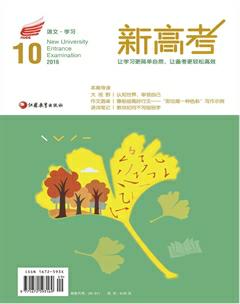祛除狹隘、自大心理的經典“古文”《師說》
陳莉



好老師是了不起的。作為老師,會唱歌的人,能夠教人跟著他唱好;會造房子的人,能夠教人把房子造好;會教育的人,能夠教人跟著他學好。人的天然本性不足以自己完善自己,人總要從師,通過教育、學習鍛造后天所形成的品性、能力,方能成人成材。
韓愈所作《師說》論述了老師的職能、從師的必要性、擇師的標準。標題中的“說”,代表古代闡述事理的一種文體。開篇兩句寫道:“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意為老師是用來傳授道理,講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其中,“受”通“授”。
“傳道”“受業”“解惑”三者有什么不同呢?
一、“傳道”,道統衰落中的大聲疾呼
人行走在“十字路口”會迷惑,該往哪個方向去?所選道路會把自己引向羊腸小道還是康莊大道?所以,“道”引申為途徑、方法、規律、道理、正義。懂得了事物的發展規律而遵循規律,懂得了正確的道理而自覺遵守,做事情就不會背離,不會走向歧路。
老師,就是懂得“道”的人,傳道,布道,薪火傳承。
但是,唐朝門閥制度盛行。門閥制度是從兩漢到隋唐最為顯著的選拔官員的系統。魏晉南北朝時期盛行官修合譜,朝廷舉才先察訪其家譜,任用顯赫人士為官。“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有譜系。”(南宋《通志·氏族略》)各個州郡都形成了一批公認的高門大姓,稱為“士族”“望族”“右姓”等。韓愈是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他稱韓家“世居昌黎”(今屬河北)、“郡望昌黎”。“郡”是行政區劃,“望”是名門望族,“郡望”就是指某一地域的名門大族。
隋唐科舉制的實行動搖了士族的政治基礎,可是,尊卑有別的觀念依然盤踞在世家子弟心中。《師說》慨嘆:“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從師求學的道理(傳統)已經失傳很久了!《師說》揭示了唐朝當時在從師方面的世情:士大夫這類人中,有人說起老師、弟子的時候,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嘲笑他,并說:“以地位低的人為師,足以感到羞愧,以官位高的人為師就近于諂媚。”
寫這篇文章時,韓愈35歲,在國子監任教。國子監是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學,是中國古代教育體系中的最高學府,唐朝時候,國子監學生都是貴族子弟。韓愈寫《師說》正是向他的弟子傳授從師之道,也是對時俗輕視師道的不良風尚進行批判。不從師學習的后果是“愚益愚”,愚蠢的人更加愚蠢。
二、“受業”,通習“古文”而以文明道
那么,學習什么呢?《師說》:“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韓愈贊許李蟠不受當時的時俗影響,而是尊師重道;他肯定了李蟠的學業選擇,認為年輕人應該學習“古文”和“六藝經傳”。
六朝以來,駢文盛行,以對偶句(駢句)為主的文章叫作駢文;與之相對,以非對偶句(散句)為主的文章叫作散文。這種風氣,直到韓愈所在的中唐時期仍流行不衰,寫文章特別講究對偶聲韻、詞句華麗。當時盡管也產生了一些藝術成就很高的作品,但是普遍寫文章輕視思想內容而泛濫浮靡之風。所以,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提倡學習“古文”——先秦兩漢時期的“散文”——以文明道,文道統一。
“六藝”有兩種意思,一種指禮、樂、射、御、書、數六種技能,另一種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儒家經典。從《師說》來說,“六藝”承接前一句的“古文”,應該指儒家經典,“六藝經傳”指儒家經典及解釋六經的著作。
《師說》肯定李蟠“學于余”、虛心向老師“我”學習的做法,這也是向世人傳達從師之道;《師說》贊賞李蟠“好古文”(愛好先秦兩漢的散文)、“通習六藝經傳”(普遍學習儒家經典及其解釋的著作),又是在向世人指點迷津,傳授學業知識,學什么和怎么學。
三、“解惑”,拜師求學勿因小失大
首先是關于“師”含義不清的糊涂。
《師說》指出:“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這句話醍醐灌頂,指出“師”的核心在于能夠傳道,而不是外在的附屬條件。無論地位顯貴的還是低下的,無論年長的還是年少的,道所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所存在的地方。
我們今天往往也會迷惑而糊涂,受偏見的影響而不能虛心傾聽與求教,諸如身份歧視、地域歧視、長幼歧視等。今天讀《師說》,正是在學習如何摒棄偏見,廣納百川,虛懷若谷。
其次是行為上“恥學于師”的糊涂。
《師說》指出,圣人越是善于學習越能超出常人,從而智慧圣明;如今的普通人越是恥于求師,越是愚鈍愚昧。確實如此,“才須學也”,不學不問而能知曉事物,古今行事還沒有過。《師說》寫道:“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愛自己的孩子,選擇老師教導孩子;對于他們自己,卻以從師為恥,真是糊涂啊。
人人都應該崇尚師道,在求師、學與問中,化無能為能,化不知為知。這樣,人類才能進步,社會才能進步。
第三是觀念上“小”“大”莫辨的糊涂。
《師說》指出,那些孩童的老師,只是“授之書而習其句讀”,教孩童讀書、學習書中的文句、斷句而已,“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并不是作者所說的傳授道理、解答疑惑的老師。句讀不知道如何斷句,要問老師;有疑惑不能解決,卻不愿問老師,這是“小學而大遺”,小的方面(句讀)學習了,大的方面(解惑)卻丟棄了,這是不明智的。
“小學”是有特定含義的,主要是指分析字形的文字學、研究字音的音韻學、解釋字義的訓詁學,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就是“小學”的經典之作。
漢代的“小學”是很深的學問。本文對“道”“業”“惑”進行了字形、字義的辨析,是否分析到位了呢?未必。“師”這個字的來歷和深意又如何呢?“傳道受業解惑”,“傳”“受”“解”這三個動詞是否能互換?為什么?這些都可視為“小學”的范疇。漢代的許慎、鄭玄,清代的段玉裁,民國的章太炎都是“小學”大家。
不過,在韓愈看來,“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學習“小”的方面,目的是懂得“道”,解除自己的迷惑糊涂之處。或者說,“習其句讀”是為了通習“六藝經傳”,從而達到明“道”的境界。
韓愈在《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中總結出“治學”四美:“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己不學,既學患不行。”治學的境界在于多讀、深思、虛心而躬行。
就像讀了《論語》“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懂得了這個道理,就應該在生活中真正地虛心好學,不恥下問。而不是背背經典,停留在口頭上,那就是因小失大了。
《禮記·學記》:“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師說》就是在進行傳道、授業、解惑,不遺余力地呼吁尊師重道的重要性。“圣人無常師”,圣人沒有固定的老師;老師就是先懂得道,在某一方面“術業有專攻”的人。
在門閥森嚴的中唐,這樣的思想振聾發聵;在開放開明的當代,這樣的思想依然先進。韓愈所指的“師”,既不是專門學校的老師,也不是指教授字詞斷句的啟蒙老師,而是指在某方面學問和技藝上有專門研究的人,能夠“傳道受業解惑”的人。
這么說來,道,往大了說,是研究治國之道、公道;往小了說,生財之道、養生之道、茶道、花道,都是各有門道。
明鏡屢照仍明,清流風拂仍清。《師說》就是這樣一篇可以讓我們經常閱讀,經常反思,祛除狹隘、自大心理的經典“古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