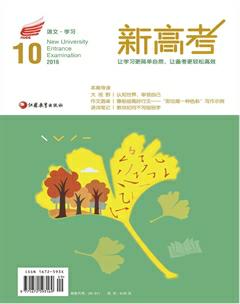詞語探源三則
宋永安
“馬路”是馬走的路嗎?
人們一般稱能夠跑車的路叫“馬路”。但仔細想想,這個稱謂不太符合邏輯:“馬路”字面意思是“跑馬的路”,而“車”和“馬”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東西,簡直是風“馬”“車”不相及,那為什么能夠通用呢?
在現代漢語中,依然存在許多“車”“馬”并行的詞語,如管交通繁忙叫“車水馬龍”;旅途勞頓叫“車殆馬順”;坐出租車、乘飛機、坐火車等交通費叫“車馬費”。但人們只是這樣使用而已,當然也知道這跟“馬”沒什么事情。
根據古代文獻記載,中國早在夏代已經有了車。而且,目前所見最早的漢字甲骨文、金文中,車的形象也有很多。由此可知車在先民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到了信史時代,車在古人的生活中仍然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是交通運輸、軍事活動、信息傳遞的基本載體。
因為車的重要性,人們開始了對道路有了關注和講究。上古時代的規范道路,完全是根據行車的標準建造的:能容納一輛車行駛的叫“涂”(涂容一軌),能容納兩輛車并行的叫“道”(道容二軌),能容納三輛車并行的叫“路”(路容三軌)等。這樣看來,今日所說的“馬路”,即使在上古時代也應叫作“車道”才是,“馬路”之稱又如何能成立呢?
原來,上古時代的“車”“馬”本是二位一體。那時候,馬用于交通,一般并不單獨發揮作用,而總是和車聯系在一起。說到馬,即包括車;說到車,即意味著馬。而馬被用作單獨騎乘,卻是極為罕見的,甚至被看作是怪異的行為。
據歷史記載,漢民族騎馬之俗,發端于戰國時期的趙武靈王一次重要改革——胡服騎射。“胡服”,指的是我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服裝,特征就是短衣、長褲、皮靴,特別適合騎馬。而漢民族的傳統服裝樣式與今天的裙袍很像,不方便騎馬。趙武靈王為了軍事需要,提倡穿胡服,以方便騎射。
雖然單人匹馬的“騎”曾被先民認為是奇異之事,上古基本交通手段自然是以馬駕車,也就是說,馬只是作為車行進的動力在當時的交通中發揮著作用。車馬既然難舍難分,行車的道也就不免成了跑馬的路,稱之為“馬路”也就十分自然了。
中國古代的“道”
古代有關道路的名稱要比今天多。《爾雅-釋宮》:“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所謂達即通,一達指沒有岔道,三達指丁字形街,四達是兩路十字交叉。諸如此類。
一般來說,道、路為通名,凡人、車常走的地方都叫道或路,比較寬闊的叫康、莊(康、莊都有大的意思),岔路多的叫衢、逵。此外,還有一些道路的名稱。
徑,是指小路。《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說藺相如派使者“從徑道亡,歸璧于趙”,就是走的小路,是因為小路一般較大路近,可以更快地到達,更重要的是沒有關卡、人少,免得暴露。最后完璧歸趙。《論語·雍也》中說澹臺滅明“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就是說其人方正,沒有私人之請,連走路也一定要走“正路”。
蹊,也是小路。諺語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說,桃、李樹下的路自然是小路。
沖,是交通要道。現代漢語中有“要沖”,通常專指軍事上重要的地方。
當然,古人在道路上的相關設施也十分周全。他們早就知道大路兩旁應該植樹。《國語·周語》就有這樣的記載:“列樹以表道。”可見古代路邊確實栽樹。
此外,為了行人,首先是為了君王的使者和官員走在路上能及時得到休息,沿著主要的道路還設有不少亭館,有人看管,備有糧柴。大約到了秦漢時期,這種路邊的館舍就叫亭。亭與“停”相通,意思就是供行路者停下休息的。漢高祖劉邦未起事前就是一位亭長。到后代又有長亭、短亭的區別,古時就有“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一說。
“大義滅親”傷了誰的“大義”?
在現代社會里,揭發檢舉有問題的朋友和親屬,或者是懲罰有過錯的親人、友人,往往會用“大義滅親”這個詞,就是在大義之前,可以不顧私人親情,取“義”而“滅”親。這種取舍關系帶有褒義色彩。在這個成語背后,是兩千多年以前一個古老的故事。
《左傳-隱兮四年》:“石碚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說的是春秋時期的衛國國君衛莊公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姬完,二兒子姬晉,三兒子州吁。州吁雖是庶出的小兒子,卻很受衛莊公的寵愛,驕縱好武,成了一個禍害。老大臣石碚對這件事很看不過,多次跟衛莊公談到這個問題,教他約束州吁,衛莊公就是不聽。州吁也就更胡作非為了。
石碚的兒子石厚經常與州吁一起出去打獵,為非作歹。石碚因為這個事兒沒少拿鞭子抽他,還把他關在家里,鎖在房中,不讓他和州吁來往。石厚趁家里不注意,越窗而逃,從此住在了州吁的家里,和州吁更親密地混在一起,堅決不再回家。
衛莊公死后,大兒子姬完繼承衛國君主的位置,稱為衛桓公。衛桓公老實懦弱,能力較差,石碚一看沒辦法,索性自己也告老還鄉了。那位為非作歹的州吁,終于和石厚等一干狐朋狗友合計,謀殺了衛桓公,但是自己的位置卻不牢靠,這讓他很郁悶。在這時,他想起了老臣石碚。于是,他就派石厚去問石碚如何安定民心,讓自己的地位鞏固下來。石碚心生一計,告訴石厚說:“那就要去朝覲周天子,得到周天子的認可就行了。”石厚又問:“那怎么才能去朝覲呢?”石碚說:“陳國的國君陳桓公很得周天子的寵,衛國和陳國又是睦鄰友好,要是你們去陳國和人家說說,讓陳桓公遞個話,周天子就肯定能接見你們。”于是,州吁和石厚就帶著禮,跑到陳國辦這個事情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