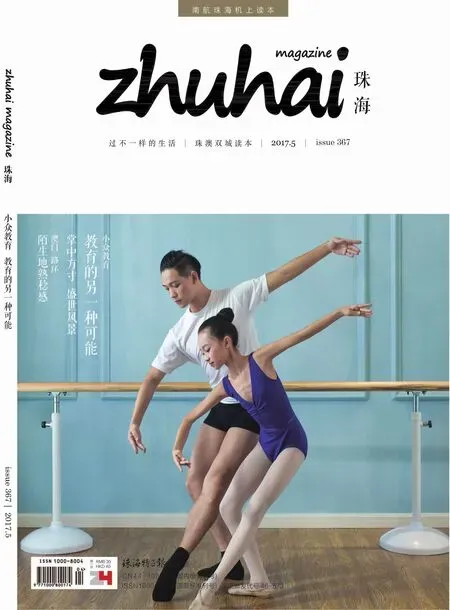自然教育讓生命自在生長
文| 紫夢 圖|E-IMAGE
自然教育讓生命自在生長
文| 紫夢 圖|E-IMAGE
Natural education Be free to growth
我們應該換一種方式讓孩子們看看我們周圍的世界。草長鶯飛、花開花落,無憂無慮地擁抱自然能夠教會我們的,不僅是對個人情操的升華,還有對生命輪回的思考,而這些,我們有義務讓孩子知道。
你有多久沒見過夜晚璀璨的星空了?匆匆而過時,有沒有注意道路兩旁的花開花落?是不是一年四季的變化更替,僅在手機的氣象預報中才能感受?我們都是如此,那我們的孩子呢?眼花繚亂的興趣班,各種各樣的課程作業,應接不暇的考試評比……他們仿佛比我們還要忙碌,奔走在滿足家長期望和證明自己是乖寶寶、好孩子身份標簽的道路上。
當田園變成高樓,土路變成街道,我們的孩子出生在了一個對我們來說都算陌生的壞境中,霓虹燈的色彩比之螢火蟲的點點螢光更輝煌,更燦爛,但卻少了那份天然與野趣。于是,有人開始思考:對于那些在父母小心呵護、用心安排下循規蹈矩的孩子來說,自然和田園,到底意味著什么?
或許,我們應該換一種方式讓孩子們看看我們周圍的世界。草長鶯飛、花開花落,無憂無慮地擁抱自然能夠教會我們的,不僅是對個人情操的升華,還有對生命輪回的思考,而這些,我們有義務讓孩子知道。
讓孩子在草地上盡情地撒歡
幾畝薄田,種菜澆水;雞鴨羊兔,每日飼養;草地上撒歡出汗,坐下來信手涂鴉;讀讀老祖宗的經,練練洋鬼子的話;粗糧淡飯,蒙頭大睡長身體。這樣一段看起來很美好的話就寫在“耕讀園”的招生介紹上,下方還“友情提示”了一句:不招望子成龍的父母。
這就是耕讀園的教育理念,也是創辦人張濤和他的合伙人對如何養育孩子的理解。自己的孩子陸續出生,面對一天天長大的孩子,以什么樣的方式來養育他們,成為縈繞張濤心頭的難題,對此,他也做出了許多關于未來,關于孩子的期許。
“我期許有這樣一個地方,讓他們如此成長:草地上盡情撒歡,汗水痛快流淌;有幾分薄田,讓他們每天都能接觸到土地,種菜澆水看蔬果瘋長,慢慢地知道田地的可愛、汗水的芬香;創意,對他們來講,是隨手拿來的玩意兒,無框無架信手涂鴉;老祖宗的經典得知道些,《弟子規》里有受用終生的信條、《中庸》里真的有中和之道的美妙,他們還小,其中深意現在不能言說,那就先裝進小心坎里,像一顆種子一樣埋在那里。”





不求他有多成功,寧愿讓一切功名遠離他,但必須食可飽腹、精神自由、人格獨立、有責任和擔當、愛自己愛家人愛生活、能感知美、有持續的學習能力。不能管得太嚴,真正的成長是自由賦予的。小手放好,立身端坐,大人都難做到,別難為小孩子了。他就是一小蝌蚪,歡快活潑靈動,就得這樣,這樣才是他。
張濤覺得,我們就應該這樣養孩子,他的想法也得到了孩子母親的支持,更為幸運的是,他找到了和他有同樣想法的兩位朋友:一個跟他一樣初為人父的孩子家長,和醉心國學的“麥子老師”王亞南。四個人就在一個親子樂園中開辟出一方空間,種菜、養花、飼養動物、搭建教室、購置玩具,開辦了這樣一個“放養式”的兒童教育機構:耕讀園。首批入學的兒童,就是幾個合伙人家的適齡孩童。
對于自己孩子的教育,按照張濤他們的理念忠實地執行著,耕讀園里的課程雖多,卻沒有任何強制性的作業;在這里沒有老師催促你必須午睡;也沒有規定要求你必須站直坐好;關于興趣,隨孩子們高興就好,曾有小朋友私下向家長“打小報告”說不喜歡這里讀《中庸》的國學課程,當家長建議轉去每天有作業的普通幼兒園時,小朋友立即用高聲抗議表達了自己留下的意愿。在這里,你可以不喜歡國學,甚至可以不喜歡任何一個或者幾個課程,對此老師們從不強求,不喜歡的話就去做你最喜歡的事,只要別打擾別人。不要打擾別人,是這里最大的規則。
國學老師王亞南每天用30-60分鐘的國學課程帶著孩子們誦讀唐詩、讀《三字經》、讀《道德經》,沒有家庭作業,沒有強制要求,孩子們像誦兒歌一樣地興致勃勃。王亞南視它為播種子,此時像春天一樣播下一粒種子,等二十年、也許是三十年后的收成,而我們不都是以前種下的種子嗎?
除了國學,王亞南還希望帶領孩子探索更多的領域:在教室外面,有近6畝的有機菜園,孩子們可以自由地在里面游戲。每周都有農耕課,植秧、澆水、捉蟲、采摘。土地帶給孩子們的滋養,除了每日的有機蔬菜給孩子們健康的飲食,還有對孩子心靈的滋養和動手能力的培養。藝術工作室有木工、陶藝、布藝、綜合材料、繪畫等形式的每月主題課程;還原語言本質的英語教育;遠足郊游、篝火露營、野外探險等每個學期的游學;每月第一個星期天的擺攤活動……
王亞南將自己的教育理念歸結為“愛和自由”,她認為,愛孩子就應該給孩子充分的自由,應該用平等的方式與孩子對話,現在許多家長是以愛的名義傷害孩子,過度的保護和自己價值觀的強加,剝奪了孩子成長探索的權利。家長不是仆人,不要讓孩子失去照顧自己的能力,相比孩子,我們家長和老師更應該學習,學習如何有效地陪伴孩子,我們的角色是陪伴者。不要去做孩子的指路明燈,每個孩子都應該是自己的明燈;不要過多地用成人的思維去界定孩子的行為,懲罰和獎勵,都是一種變相的奴役。
反思教育 也是反思我們自己
因為差異,世界才有了繽紛色彩,孩子們的世界也是這樣,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性格,都有自己的成長節奏,無論作為老師,還是家長,我們都是陪伴者,我們必須尊重、聆聽和順應他的節奏,按他們的拍子,而不是我們的拍子,陪伴他們。某種意義上,是他們自己在成長,按自己的節奏成長。
正因為對孩子們各自成長節奏的尊重,才有了如今的耕讀園。而創辦園區的初衷,則是幾位創辦者自己在傳統教育中所受過的傷。張濤說:穿過教育的硝煙,我們傷痕累累。而耕讀園,則是不想讓這些傷痕,再出現在我們的孩子身上。回首過往,張濤希望在耕讀園的教育中,應該教會孩子幾個簡單的人生道理。
首先就是要勇敢地做自己,自從我們進了校門那天起,就沒有一個老師告訴過你:你要做自己,我們在努力地成為別人,卻沒有人告訴孩子,怎樣去做自己;然后要教會孩子們樸素自然地表達,從我們學習遣詞造句開始,老師表揚的,都是那些會用優美詞語的同學,張濤想要告訴孩子們:作文,就是內在感情的文字表達,不裝腔、不作勢、有則多說、沒有少說,沒有大話、沒有格式,真實,大過一切。
最后,耕讀園想要告訴孩子和家長的是,不要用過度的技能教育和簡單的書面成績打擊孩子幼小的自信。上帝造人時就有了區分心,腦袋結構就有不同。這些結構影響了人對數學、空間、音樂、繪畫、文字不同的敏感度。教育,就是發現每個孩子的不同,揚長避短,通過其擅長,找到通往生活、生命和宇宙的路。
“我們在追問如何教育孩子的時候,不妨想想我們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受過哪些傷負過哪些累,教育到底留給了我們什么?如此,在‘望子成龍’‘精英教育’大行其道之下,我們會留給自己一些思考:怎樣算是本質的教育?反思教育,也是反思我們自己。”
農場里的自然教育
2013年,在珠海從事對外貿易多年的施維在一次踏青旅游中被優美的田園風光所吸引,這喚起了她埋藏在內心深處的田園夢想。在城市之外的田園深處,施維承包了一片農田,辦起了青青農場。對童年生活的懷念、對當前教育模式的思考、還有滿足自己“夢想”的小小私心,出生在長江岸邊小城的施維,在都市的霓虹燈下徘徊半生后,又一次回到了自己記憶中的田園,也用實際行動踐行著自己對自然教育的思考。
一路走來,施維也想把自己從田園生活中收獲的人生感悟分享給身邊的朋友,也想把自己對兒童教育的思考踐行到自己的農場中,施維覺得:田園生活美好而舒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才是她心目中最美好的畫卷。在孩子們的成長道路上,田園的優美風光能讓孩子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而除草插秧的農耕生活也能帶給孩子們另一種人生體驗,讓孩子們明白生活最質樸的樂趣。
隨著農場的日漸成熟完善,一些開放性的互動空間也被用心拓展出來,你可以在農場里租用一塊土地,帶著自己的孩子親自耕種;或者參與農產品采摘、農家生活體驗、野外活動拓展等農家活動;也可以去茶園學堂上一堂戲曲課、參加一次英語沙龍、或者干脆在農家小院里教孩子辨認五谷雜糧。
施維想通過這樣的方式,把青青農場打造成一個進行親子互動、自然教育的綜合性資源平臺,各類資源在這個平臺上根據孩子和家長、老師的需要進行合理配置,搭建出最適合每一個孩子的成長道路。

對童年生活的懷念、對當前教育模式的思考、還有滿足自己“夢想”的小小私心,施維用行動踐行著自己對親近自然教育的思考。
在農場的經營過程中,施維也看到了許多家長在養育孩子方面迥然不同的態度和行為,也深深感受到不同孩子個體成長的差異和環境對他們成長的影響。施維發現,在村鎮學校和鄉村環境中長大的孩子,相對在城市中長大的孩子更樂于與人交流,他們或許沒有上過太多的興趣班,掌握太專業的業余技能,但他們很樂意與身邊的人分享他們的樂趣,表達和展示自己,而城市長大的孩子或許擁有比他們更好的條件,卻很少與人交流分享;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們的交流分享能力反而在逐漸喪失,年齡越小的孩子越容易與身邊的人打成一片,越大班級的孩子反而越沉默和孤立。
這或許就是自然教育、田園生活帶給人性格的改變,大自然用無聲的教材教會了孩子們樂觀開放的心態,小心保存了他們那份與生俱來的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心。而在這個過程中,家長的過分干預和過度保護反而對孩子接觸自然、認識世界起到了反作用。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是:家長不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到孩子身上,許多家長也認同這方面的觀點,但在實際生活中,依然有家長出于對孩子的保護心理,限制了孩子的自由,讓孩子從開始對任何事物都好奇的熱情逐漸降溫,最后逐漸喪失了對周圍世界的好奇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這無疑是成長的退步。


在自然中放飛孩子心靈
施維將自己的農場搭建成為了一個親子教育的平臺,而在珠海還有幾個年輕人,則把教室搬進了大自然中,在城市周邊的公園、小山中,用自然做舞臺,讓小動物們做主角,給孩子們上一堂生動的自然教育課。
Hello大自然教育工作室的創辦人“建鋒”,2013年伴隨著兒子的降生也對自己的人生開始有了新的規劃,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想給自己的兒子做一個榜樣,為自己的夢想做點事情。于是,他辭去了在金融公司朝九晚五的生活,自己組建了一個戶外教育公司,開始帶團進行戶外運動。2015年,在廣州鳥獸蟲木自然保育中心組織的大學生自然解說員培訓課程上,建鋒認識了另外三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曾從事教育工作,辭職后也曾自己開辦蝴蝶園的“狒狒仔”;剛剛走出校門的兩位90后美女領隊“蝸牛”和“綠野”。在湛江的特呈島上,互相搭隊配合而結識的四個人,就這樣因為對自然觀察和自然教育的熱愛,在緣分和偶然下相遇,因為共同的夢想而結伴同行。
在帶領孩子們進行野外觀察的過程中,建鋒和他的團隊也在思考,對于孩子們來說,野外觀察到底意味著什么,對于他們來說又有什么意義?帶著他們遠離城市去自然環境里穿梭,是不是在浪費他們的時間?關于為什么要做自然觀察,為什么要做自然教育,建鋒可以說出許多的理由:它能讓你更了解真相,更遠離嘈雜;更容易有自己基于事實的判斷;更能激發熱情和行動力;更愛自然,擁有自然的家鄉;更純粹,更容易獲得寧靜和快樂;更謙卑……更容易寫出一篇好文章。
但在這些切實可見的好處之外,建鋒的團隊帶給孩子們的則是一份相處在自然里的友誼,大自然寬廣無垠,當我們抬頭仰望的天空,和哈勃望遠鏡深空拍攝的,135億年前的宇宙是連在一起的。人類所有的情感,悲歡離合也罷,功成名就也罷,顛沛流離也罷,只要你回到自然里,統統都會被消弭,最后只留下真正純粹的自己,和自然對話,這時候你會感受到內心深處的真正的快樂。
而這個培養的過程,則需要時間的沉淀。許多家長在孩子的教育上喜歡看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可是,在自然觀察中沒有一幅漂亮的繪畫、一個精美的手工來表現孩子們的學習成果,孩子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歷來醞釀。走過許多山間小路、欣賞和觀察過眾多昆蟲的繁衍生息、安靜地等待天黑到天亮、一次又一次地走進同一片森林……經歷過后,發現最珍貴的記憶并不是那些昆蟲植物的名字,而是一路走來揮灑于林間的歡笑,一次與另一種生命的短暫相交,一份相處在自然里的友誼。
自由,是對父母壓制的找回,作為老師,他們正努力讓被壓迫的樹枝漸漸放直。自由,不影響紀律,孩子內在對秩序的遵守,超越父母,這也是許多家長始終不愿意接受和面對的一點。自由的孩子是幸福的,想要保證這份孩子的自由,就需要家長和老師在技能教育的功利和孩子的心靈成長之間做出一個選擇。
張濤、王亞南和他們的耕讀園選擇了舍功利,不討好孩子、不討好家長、也不討好社會,一切讓他按照自身的規律自然生長;施維選擇了給孩子們一個可以自由成長的平臺,用青青樂園里的資源自由搭建孩子們的成長之路;而Hello大自然的四位小伙伴,則用身邊的綠色的課堂,讓孩子們去體驗大自然的美好,讓孩子們在自然的懷抱里,自由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