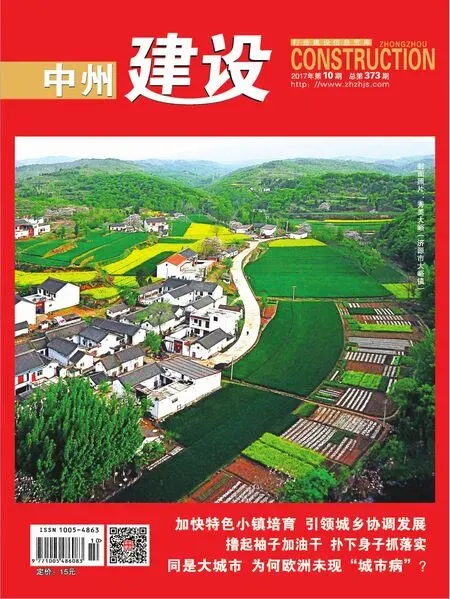左學金:城市發展不能只要核心功能
左學金:城市發展不能只要核心功能

左學金,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專家
城市的核心功能與非核心功能是相互支持的,不能只要核心功能而不要其他功能
我們的討論從北京疏解一部分功能開始。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北京并發表講話,對北京的核心功能作出明確的戰略定位,要求堅持和強化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功能。2016年中國出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再次明確了北京的上述定位。
但是由于核心功能與非核心功能是相互支持的,所以要把非核心功能疏解出去,做起來并不容易。如果核心功能與非核心功能協調得不好,也會出問題。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強調“先生產、后生活”,最后就帶來生產功能與生活功能不配套的問題。
我注意到,京津冀規劃并沒有說要疏解北京的非核心功能。北京疏解功能不是區別核心功能和非核心功能,而是區別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重點疏解非首都功能。京津冀規劃明確提出,北京的問題,如人口過度膨脹、交通擁堵、房價高漲,資源環境承載力不足,這些問題的產生,是因為北京集聚了過多的非首都功能,所以需要有序疏解這些非首都功能。
規劃明確北京疏解的非首都功能有四項:① 一般性產業特別是高消耗產業,這里主要還是制造業,比如首鋼遷到(河北唐山市)曹妃甸;② 區域性物流基地和區域性專業市場等部分第三產業;③ 部分教育、醫療、培訓機構等社會公共服務功能;④ 部分行政性、事業性服務機構和企業總部。所以我認為,首都功能是核心功能的一部分或是核心功能的一個子集,是中央黨政機關履行職能所派生的功能。這里強調中央黨政機關,不包括北京的地方機關,因為中央機關才體現首都功能。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區別首都功能與非首都功能還是有一定難度。
我們傾向于從政治、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等視角來談城市功能。但是國外一般從不同的視角來區分城市功能。比如在1933年有關城市規劃的《雅典憲章》中,把城市功能分為居住、工作、游息和交通四類主要功能,而且特別強調最基礎的功能是居住功能。從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來看,這樣分類也有其合理性。在這四類功能即居住、工作、游息和交通中,要區分哪一類是核心功能,哪一類是非核心功能,還是很困難的。因為從人的需要來說,這四類都是人所需要的功能,一個都不能少。
城市核心功能有個歷史演變的動態過程
城市的核心功能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一個動態的演變的過程。一個城市的核心功能在更大程度上是在特定經濟社會與技術條件下,由該城市的客觀因素或稟賦所決定的,如城市的區位、交通運輸的成本以及與經濟腹地的聯系等。
比如,前些年中國一些三線城市也建了民航機場,但是民航航班不愿意來。為什么不來?因為這個地方沒有規模經濟,沒有足夠的客流量,民航來了要虧本。所以如果要民航安排航班,地方政府就要每年補貼它。這是客觀規律在起作用。
當然,技術對核心功能的影響也很大。比如,我們知道揚州在中國歷史上,從漢唐到明清,曾經歷長期的經濟繁榮和文化興盛。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揚州位于大運河和長江的交匯處,有“中國運河第一城”之稱。我們讀唐詩是“煙花三月下揚州”,唐詩中沒有出現過今天的“大上海”,因為上海在19世紀中葉開埠以后才得到快速發展,成為遠東地區最開放最繁華的大都市。揚州的繁榮與當時的運輸技術有關,當時的運輸主要靠內河航運。隨著我們近現代運輸技術的發展,鐵路、公路運輸變得越來越重要,揚州的核心功能也就注定要發生變化。
我們再看看江蘇滬寧線沿線城市。中國最早的鐵路就是滬寧線。滬寧鐵路對沿線城市,從上海經蘇州、無錫、常州到南京的各城市的發展有重要影響。歷史上的國際貿易也影響過許多城市,如元末明初的福建泉州、鴉片戰爭以前的廣州等,都曾經是中國重要的貿易口岸。對外開放與貿易是促進上海在19世紀中葉以后快速發展成為遠東地區國際大城市的重要原因。這些都和技術及生產方式有關系。
從經濟學的視角來分析,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動城市核心功能的轉變?這里面主要的經濟邏輯是什么?就是用土地產出率更高的經濟活動來取代原有的經濟活動。比如,最早我們都是農業,沒有城市,后來有了交易的需要,就出現了集市。中國最早的城市只是政治中心,交易是在城外進行的。到宋代以后,城市才成為交易的地方。清明上河圖生動地描述了宋代首都汴京(開封)的繁華景象。交易帶來的土地產出率要比農業要高,所以交易用地就取代了農業用地。后來,農業手工業貿易市場又很快被大工業制造中心所代替了,因為大工業制造中心能夠產生更高的土地產出率。當然,后來制造業又被現代服務業所替代,因為中央商務區(CBD)比制造業用地能產生更大的效益。所以在城市功能演變的背后,是經濟規律在驅動。
但是目前中國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一些經濟規律難以發揮作用。比如根據京津冀規劃,北京集聚了過多的制造業功能。歷史上,其他國際大都市如紐約、倫敦,也有過很發達的制造業。為什么后來制造業外遷呢?關鍵是,土地所有者要追求更高的產出率和更高的地租回報,那么制造業就會被服務業所替代。在中國,這樣的市場機制發揮資源配置作用有難度,因為中國工業用地的價格不能充分反映土地的稀缺性。
國務院《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將城鎮用地分為居住用地、工業用地、商業用地等。其中商業用地的使用年限為40年,居住用地的使用年限為70年,工業用地的使用年限為50年。三類用地的土地價格(出讓金)也有很大差別。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來看,住宅用地和商業用地的價格要比工業用地的價格高得多。由于地方政府可以用非常低的價格征收農民集體土地,建設工業園區或其他工業用地,所以工業地價不能充分反映土地的稀缺性。這與中國部分城市的商業用地和住宅用地特別貴也有關系,因為大量的土地用于工業上,造成商業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供給相對不足。
這樣一來,國家土地的價格機制不能有效發揮資源配置作用,不能發揮向外疏解制造業的功能。所以,現在一個城市要轉型,在更大程度上需要政府去規劃與推動。這里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價格機制沒有起重要作用。從深化改革、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視角來看,政府可以采取的替代做法,就是讓價格機制發揮更大的作用。
不但土地資源如此,水資源也是如此。目前華北是中國鋼鐵工業的集聚區,但是華北也是嚴重缺水的地方。生產鋼鐵需要大量耗水,但是目前中國的水價是補貼的。南水北調,調水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果水價能充分反映水資源的稀缺性,那么耗水多的工業就很難在華北地區發展。現在因為水的價格機制被抑制了,所以鋼鐵工業在華北地區過度發展,帶來嚴重的水資源問題與大氣環境問題。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就要求我們在碰到問題的時候,應當先思考如何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出了問題就是政府來管。
在城市空間布局上,要重視規劃建設多中心城市與促進混合功能
我想對北京的城市規劃提一些看法。在我看來,北京的城市規劃有兩大缺陷:首先是單中心的城市形態,其次是居住與就業功能在空間上的日益分離。
北京作為一個特大城市,從空間形態上來看,只有一個中心,就是以天安門-紫禁城為中心,圍繞這個中心,在原北京城墻的地基上修了二環,修了三環、四環、五環、六環,六環已經是180多公里了。現在正在建設七環(亦稱北京大外環高速公路、首都地區環線高速,或G95),途徑河北省張家口、涿州、廊坊、承德,以及北京市大興區、通州區和平谷區等地,全長940公里,據說2019年可以完工。這些環線基本上都是圍繞一個中心的同心環,都在不斷強化北京作為單中心的城市形態。
這種單中心城市、“攤大餅”式的城市形態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北京人口的就業空間與居住空間的日益分離。城市的就業功能集中在中心城,而城市的居住功能則不斷外移。越來越多的城市常住人口,包括戶籍與非戶籍常住人口,向城市邊緣搬遷。結果居住地與就業地的空間距離不斷延長。2016年北京一半以上的常住人口居住在五環以外,上下班平均通勤距離達18.9公里,耗時50分鐘,均為全國之最。而長距離通勤人為增加了交通需求、大量的私人小汽車出行和嚴重的交通擁堵。
實際上,國際上城市規劃理念在歷史上也有所變化。如1933年的《雅典憲章》強調分區,強調將城市的三種功能,居住、工作和游息進行分區,通過交通功能將不同分區聯系起來。但是1977年在秘魯馬丘比丘古城遺址簽署通過的《馬丘比丘憲章》則強調城市的混合功能,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但是中國現在的城市建設總的來說都是劃大塊,這一塊是工業區,那塊是生活區,那塊是商務區,這還是單一功能分區。這種分區造成很多問題,各種功能難以相互支持,人為增加了不同功能之間的交通需求。
清華大學的建筑學家梁思成(1901—1972)教授半個多世紀前曾提出,老北京城不要動,另外建一個新城,完全不影響北京的發展。可惜他當時提的建議沒有被毛主席采納。但是現在,一定程度上在采納他的意見,因為北京要向外疏解一部分功能。新加坡著名城市規劃專家劉太格2016年建議把北京分成五六個城市,每個城市都有比較完整的混合功能,這樣可以盡量減少各城市之間的交通需要。實際上,五年前我在北京參加關于北京建設國際大都市的研討會,在會上也提出,北京的問題是單中心城市,需要通過發展多中心城市與加強各中心的混合功能來減少北京的通勤需要。
北京有一萬多平方公里,當然有一部分是山區,面積和東京都市圈差不多,但東京都市圈有3700萬人口,遠遠超過北京人口,而且東京沒有嚴重的擁堵問題。所以主要問題不是人口規模,而是城市規劃的好壞。
北京城市問題還有一個外部原因,就是中國的城市等級體系。中國的城市體系,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等級體系。處于金字塔頂部的是北京,然后是其他一線城市,然后是省會城市,然后依次是地級市、縣級市與鄉鎮政府的所在地城鎮。
中國將大量的投資集中于北京與其他金字塔頂部城市。北京等金字塔頂部城市,具有更好的就業機會與發展機會,具有全國最好的教育與醫療設施,具有最高的人均收入、最高的人均財政收入和最好的公共服務,北京還是全國央企總部最大的集聚地。
中國的一些資源,尤其是公共資源,是最優先配給了北京和其他一線城市。這等于是在長江上攔了一個大壩,大壩上下游的水位差非常大,目前的辦法就是把這個大壩攔死,盡量控制水的流動。但是上下游之間存在巨大的勢能,大壩受到的壓力也很大。所以要通過行政手段來控制人口流入城市,尤其是流入一線城市。實際上,更好的替代辦法是逐步降低大壩上下游的水位差,這樣即使自由流動也不會帶來災害,實際上就不需要通過大壩來控制了。降低上下游的水位差,就是要在中國的城市體系中逐步弱化一線城市的優先地位,提高社會保險與公共服務在各大小城鎮之間的均等化水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強調北京優先,又要防止北京城市過于擁堵,實在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要提高城鎮之間的均等化水平,就要加強有利于人口與勞動力流動的基礎設施,包括硬基礎設施與軟基礎設施。也許我們有理由為中國一些硬基礎設施已經超過美國而自豪。美國有許多公路陳舊不堪,美國還沒有高鐵。但是我們也有理由認為,中國促進勞動力流動的軟基礎設施還不行。我們的基礎養老金還沒有實現全國統籌,還是地方統籌的,所以勞動力跨地區遷移流動時,很可能在流動過程中造成養老金權益的損失。相比之下,美國的社會保障是聯邦政府統籌與運作的,美國勞動力在國內跨地區遷移流動,仍然在聯邦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之下,不會發生社會保障權益損失的問題。
我們的各類社會醫療保險也是地方統籌的,所以北京上海的退休職工,很難遷移到廣東或海南養老,因為他們會面臨醫療費用報銷的問題。相比之下,美國的老年人醫療保障(Medicare)是聯邦的,窮人醫療保障(Medicaid)、少年兒童醫療保障(CHIP)的資金籌措都由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分擔(一般是各出一半)。但是我們主要是地方籌資,所以地方之間的差距非常懸殊。所以,在這些軟基礎設施方面,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即使像美國這樣比較強調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國家,還有很大差距。
政策建議
第一條建議是,解決中國城市擁堵問題的關鍵是加強多中心城市的建設。尤其是像北京、上海這樣的超大城市,要加強城市的一級中心與二級中心的規劃與建設,在一級中心與各二級中心之間加強大容量快速軌道交通聯系,加強二級中心向周邊輻射的交通聯系。另外,在城市規劃與建設中要實行混合功能,避免目前就業大量集中在中心城,而居住卻越來越向外圍擴散的發展趨勢。因此,我們要加強中心城的居住功能,東京規定,中心城區的舊城更新必須至少有20%的建筑面積用于住宅。今后中心城區的舊區改造要避免簡單將相關居民都動遷到郊區,要適當增加住宅(尤其是小戶型住宅)面積。另外,各類工業園區也要適當建設一定比例的職工住宅或宿舍。郊區新城要增強就業功能,要發展各類就業機會,尤其是第三產業的就業機會。還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讓土地作為一個重要的生產要素的價格能更好地反映土地的稀缺性。
第二條建議是,完善有利于中國人口流動的軟基礎設施。要逐步淡化城鎮體系金字塔的等級結構,提高公共資源配置的均等化程度,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同時適當提高社會醫療保險、義務教育與其他公共服務的統籌層次,提高經費籌集與使用的均等化程度。這樣做了以后,我們就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讓市場來配置勞動力資源,形成全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戶籍制度所隱含的資源配給功能就自然而然地淡化了。到那個時候,偏遠山村的孩子就能與城里的孩子一樣,享受更加均等化的基礎社會保障與各類公共服務,就能獲得更加公平的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