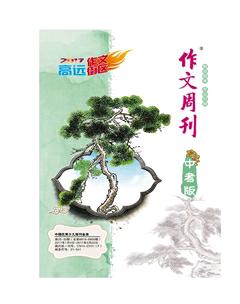遭遇書房
說中國人不喜歡讀書,那是偏激的;說中國人喜歡讀書,也有失偏頗,只不過書籍對有些人來說,是晉升的墊腳石。這種人讀書的目的是功利性的,甚至是狹隘的;讀的大部分書也只對晉升有利,于心靈無補。
我看過許多人的書房,有窮人的,也有富人的;有百姓的,也有官員的。面對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書房,我時常感慨良多。挑選三個例子一說,你就大概知道目前國人讀書的現狀了。
先說一個不能與時俱進的詩人的書房。他寫了一輩子,讀了一輩子;窮了一輩子,苦了一輩子。雖然只寫詩,但他讀書卻很廣泛,除了中外詩歌,還涉獵歷史、文學等許多領域。他的書籍都擺在那些早已斑駁的木架子上,黯然失色,像他的人一樣。他每天靜坐書房,勤奮閱讀,然后下樓逛街,手中不離一個20多年前的半導體收音機。看到他,我很辛酸,恨不得替他一把火燒了書房!
再說一個中學同學的書房。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他也是一個讀書人。遇到我或相知者,總是談一些讀書的體會,而且將他的讀后感一直滲透到你的思想里,才肯罷休。那時的我們雖然物質上不富裕,精神上卻很富有,前面總有亮光照耀著,心里總有那么一股子沖勁兒。他偶然得到一次升遷的機會——上司生病住院,他代理工作。代著理著,他便嘗到了做領導的甜頭,然后官越做越大,房子越換越大,書房越來越大,書也越來越多。置身于他的書房,仿佛進入小型圖書館,包羅萬象。那些偉大的理論書籍,擺得整整齊齊,令人望而生畏。有一次,我在報紙上讀到他給一位教授朋友寫的書評文章,感覺很好,便給他打了一個電話(絕無拍馬屁的意思)。接了電話,他也不躲閃,直截了當地說:“那是我秘書寫的。”我頓時啞口無言。
最后說一個小領導的書房。他理科出身,腦子活,讀得最多的書就是教科書,但擁有的書籍卻了不得,光他的辦公室里就有近千冊之多。同上面那位老兄一樣,他書櫥里的理論書籍和名人大典等,琳瑯滿目,永遠保持著光鮮。而不同之處是,他喜歡在書櫥前面擺造型,譬如拍照、攝像、上電視等,總能夠看到他身后滿堵墻的大書櫥和滿書櫥的書籍。最近他換了單位,打電話給我,讓我過去將他辦公室里的一些煙酒取回家。我一進門就聽一個年輕人問:“這些書還要不?”他說:“算了,那邊有。”看到躊躇滿志的他和遍地狼藉的書,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忽然想起豐子愷先生的一首題畫詩:“藏書如山積,讀書如水流。山形有限度,水流無時休。”曾經的讀書人,如今顯達了,藏書越來越多,讀書卻越來越少。弄那么多書籍做擺設,只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文化風景”罷了。他們心里還是自卑的,生怕人家說他沒文化——被人罵沒文化,那是最大的恥辱。所以,他們硬要裝出一副斯文、有文化的樣子。
我以為,讀書應該像每天吃飯睡覺一樣,保持良好的閱讀口味和品位,保持清醒的思維與思想,必然受益無窮。做人,為官,都一樣。
(作者包光潛,選自《渤海早報》2013年7月25日)
讀寫對接
本文采用了“總——分——總”的形式,先總括目前中國人讀書的現狀,再用三個書房的例子來展現現狀,最后提出“讀書應該像每天吃飯睡覺一樣,保持良好的閱讀口味和品位,保持清醒的思維與思想”的觀點。同學們在寫作時,對“總——分——總”結構的運用已經非常熟練了,但是如何去用好這個結構卻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他們時常在“總——分——總”的兩“總”上犯重復的毛病,后一個“總”與前一個“總”的內容相同,沒有思想的提升。而在本文中,作者首先概述現狀,再用三個例子呈現現狀,最后提出自己關于讀書的看法,這兩“總”在思想和內容上都呈一個階梯式的進升,給人一種逐層深入、有深度之感。并且三個例子的安排也是有講究的,第一個例子是在介紹不能與時俱進的讀書人現狀,第二個例子是在介紹一個原本癡迷讀書但后迷失官場的人的讀書現狀,第三個例子是領導的讀書現狀。這三個例子所呈現的是一個動態變換過程,第二個例子的人是從第一個人變成第三個人的,他在中間起著過渡的作用。這三個例子的位置決不能變動,否則,就會使得整篇文章的構架黯然失色。因此,同學們在運用“總——分——總”這種結構時,也可以采用這種遞進式的寫法,如此,寫作便不會有空洞、重復之嫌了。
(本版由苗文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