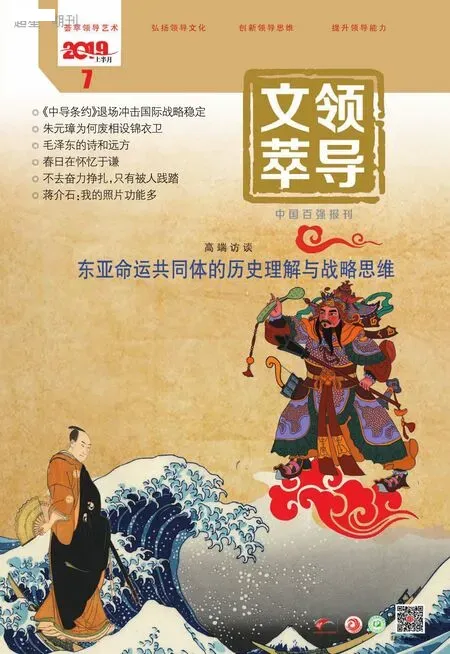供給側改革要緊盯“三大失衡”
張占斌
中國經濟社會平穩發展,有力回擊了對中國經濟的種種質疑。同時,下更大氣力破解中國經濟發展遇到的矛盾和問題,才能使中國經濟實現爬坡過坎、持續前行。
破解矛盾和問題,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要抓牛鼻子。當下中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的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剖開來看,主要表現為“三大失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緊緊盯住這“三大失衡”問題的解決。
一是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改革開放以來,經過近40年的持續高強度開發建設后,供給體系產能十分強大,傳統產業和房地產相對飽和,鋼鐵、水泥、玻璃等產業的產能已近峰值。
但實事求是來看,相當多的供給滿足的是中低端、低質量、低價格的需求,這同過去大規模投資和大規模出口的需求結構有關。隨著進入個性化、多樣化、定制化的新消費時代,以往那種模仿型排浪式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消費逐步退場,消費結構加快擴充升級,出口需求相對下降,既有的供給結構越來越不適應需求的新變化新趨勢。
從更深層看,伴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發生重大變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中等收入群體加速擴大,對消費不斷提出新要求。然而,供給體系未能及時調整跟進,結果一方面過剩甚至嚴重過剩,生產出來的東西賣不出去,供銷不對路;另一方面消費者對質量高、有信譽保障的消費品需求快速增長,國內供給無法滿足,境外購物熱度不減、“需求外溢”。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提高供給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有效性,提高供給的質量。這就要求企業形成自己獨有的比較優勢,發揚“工匠精神”,加強品牌建設,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強產品競爭力。如果我們的供給能夠體現高質量高水平,必然會大大提高國內消費市場的活躍度和消費規模。
二是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在實體經濟結構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的情況下,解決問題的思路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把結構性供需矛盾當作總需求不足,以增發貨幣來擴大需求。但因為缺乏足夠的回報,增加的貨幣資金很多沒有進入實體經濟領域,而在金融系統自我循環,形成游資尋求一夜暴富。這樣的背景下,金融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實體經濟嚴重缺血,導致工業特別是制造業比重逐步下降,一些企業難以維持,甚至選擇歇業和退出。
另一種是不把結構性供需矛盾看作是總需求不足,而是要看到真正需求的存在,關鍵是充分認識到有效需求得不到有效的供給。現實生活中,有大量中小微企業抱怨“融資難”“融資貴”“融資險”,這既有中小微企業自身的問題,也存在金融企業“嫌貧愛富”的問題。破解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就是要提高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
三是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伴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房地產業實現了約20年的“黃金增長”,為國民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衍生出的問題是,在實體經濟結構性失衡的過程中,由于缺乏投資機會,加上土地、財稅、金融政策不配套,城鎮化有關政策和規劃不到位,致使大量資金涌入本來屬于實體經濟的房地產市場,用加杠桿的辦法進行房地產投機,帶動了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房地產價格上漲。房地產高收益誘使資金脫實向虛,一些地方經濟增長、財政收入、銀行利潤依賴“房地產繁榮”,進一步推高了實體經濟成本。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定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要堅持分類因城因地施策調控,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
上述“三大失衡”有其內在因果關系,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如果只是簡單采取擴大需求的辦法,有可能會加劇產能過剩、抬高杠桿率和企業成本。正是基于此,中央強調要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定政策,通過去除沒有需求的無效供給、創造適應新需求的有效供給,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進而推動經濟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緊盯“三大失衡”,關鍵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短期與長期、減法與加法、供給與需求的關系。主攻方向應當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必然是深化改革,最終目的肯定是滿足需求。從我國在世界經濟的坐標系中看,這是一個艱巨但又必須回答好的世紀性大課題。
(摘自《瞭望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