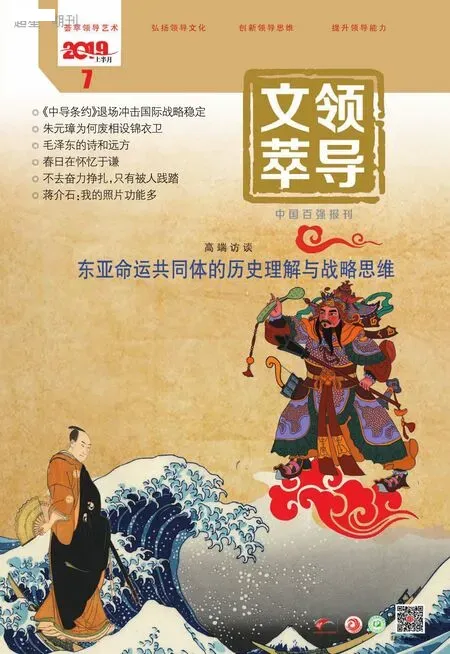諷刺聯中的清末官場
陳正賢
專制王朝每到末世,總是亂象叢生,官場尤其如此,清王朝也不例外。翻閱清末民初的筆記雜記,常常可以看到各種描述清末官場亂象的聯語。這類聯語,有抨擊官員貪瀆腐敗的,有諷刺官員好聲色之樂的,有嘲罵官員昏庸無能的,有譏笑官場頹風陋習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筆鋒所向,直指各種官場污穢弊竇。諷刺的對象則上至軍機大臣、封疆大吏,下至地方上的芝麻綠豆官,連九五之尊的皇帝也不能幸免。
這類聯語發泄對官員、官場的怨氣、怒氣,代表一種社會輿論,反映一種世情民意。就其譏刺的具體人事而言,雖有夸大或不實之處,但就整個官場而言,它的描述卻是真實的、可信的。由于這類聯語是一種解氣文字,因此詛咒、漫罵式的人格侮辱和人身攻擊時有出現,其直捷快當,不加隱諱,有一種將官場丑人丑事“游街示眾”的效果。一些聯語借用經書成語典故,對官員、官場不正之風進行調侃,寓譏諷嘲笑于幽默之中,給人以智慧的快意。
揭露官員的貪腐行為
揭露官員的貪腐行為,是官場諷刺聯的大類,聯語常常將重點放在揭露官員的貪腐手法上,因為這是百姓們經常聽到看到和感受到的。
滿人端方拍馬有術,為慈禧看好,迭加升遷,光緒三十年(1904年)出任兩江總督。此人貪墨成性,民間曾傳他鯨吞賑災款二百余萬兩白銀。他又有收藏之好,縉紳家有古籍書畫、金石彝器,總設法羅致之。有陸姓兄弟知道他的這一愛好,把價值二十余萬兩的藏書獻給他,兄弟兩人一人得軍械局總辦,一人得寶應厘局總辦。他還按“官之大小,油水之多少”賣缺,有一位姓許的知府,借他調任直隸總督之機,以“贐敬”之名送他白銀二萬兩,端方回報給他一個綜理財政局的美差。端方以贓款買書、買畫以附庸風雅,又在藩署旁開了一個古玩鋪,鋪中所列都是他家存物,各物價格,一一標明。有熱衷買官的,早上從鋪中不惜重金買來獻給他,晚上便掛牌得官。有人估計,端方在江南幾年,這樣的間接受贓不下百余萬。對此,有好事者撰一聯云:
賣差賣缺賣厘金,端人不若是也;買書買畫買古董,方子何其多乎?
這副對聯,將端方兩字巧妙地嵌于其中,諷刺端方的貪得無厭和厚顏無恥。
譏諷官員的聲色之好
光緒朝江西巡撫德曉峰,酷好聲劇,撫署中除朝廷規定的忌日外,幾乎無日不在演戲。德的女兒也有乃父之風,且特別喜歡看演男女放蕩淫媟的戲,如《翠屏山》《也是齋》之類。上之所好,往往為希圖攀援而上的屬下提供阿諛逢迎的機會。新建縣令汪以誠,以能員聞名官場,為上司所喜。德曉峰到江西上任后,汪以誠覺得又到了自己大顯身手之機,于是便派遣丁役,帶著錢鈔四處奔走,聘請負有盛名的名角,即使遠在京師,或者津滬,也不計錢財請來江西演出。汪自己則“日在撫署中”,管領調度各項演出事宜,儼然是巡撫衙門一名專職的“戲提調”。至于自己在新建縣中該管該做的事,則大小不論,全部托付同僚處理。汪縣令心里很明白,對于自己的升遷,縣令做得最好,也沒有做好“戲提調”讓巡撫大人高興來得重要。有人寫了一副對聯諷刺道:
以酒為緣,以色為緣,十二時買笑追歡,永夕永朝酣大夢;誠心看戲,誠意聽戲,四九旦登場奪錦,雙麟雙鳳共消魂。橫批:汪洋欲海。
聯中的四九旦、雙麟、雙鳳,都是當時名伶,能將這些人一一請來,可見汪以誠用力之勤,和對巡撫大人的誠心誠意。不過這兩位沉溺聲色之樂,終日“買笑追歡”,置國事民生于不顧的官員,最后還是栽了跟斗,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德曉峰有罪褫職,汪以誠也受牽連被糾,尋歡作樂的大夢由此告終。
嘲諷官員的昏聵無能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湖南巡撫吳大澂奏請從軍,獲清廷允準,任為幫辦東征軍務。1895年1月,吳大澂率新老湘軍二十余營出關,開往前線。但吳“不諳軍旅”,又有“言大而夸”“自負不凡”的毛病,既對戰爭全局缺乏了解和認真部署,又過高估計自己,以致弱點為日軍所乘,致使“湘軍力戰而敗,死傷過多。”吳大澂憤湘軍盡覆,欲拔劍自裁,被隨軍僚屬阻止。乃自嘆曰:“余實不能軍,當請嚴議”。清廷以吳大澂戰敗,革職留任,仍回湖南,不久恢復原職。湖南人寫了一副對聯來諷刺他:
一去本無奇,多少頭顱拋冀北;再來真不值,有何面目見江東。
“有何面目見江東”典出《史記·項羽本紀》,是項羽兵敗垓下后,在烏江邊與烏江亭長說的話,“江東”這里指的是湖南的父老鄉親。聯語諷刺吳大瀓自命不凡,好大喜功,白白送掉湖湘子弟性命,現在還要厚顏無恥回來任職。
暗諷官場中的頹風陋習
歷朝歷代,官場中難免有頹風陋習,它表現在官場的方方面面,體現在官員的待人處事中。這類現象自然也是諷刺聯的材料。
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自恃年長望重,視巡撫端方如無物,而端方遇到張,也不敢與他爭高下短長,凡事都謙讓于他。有人寫了一副對聯諷刺兩人:
端拱無為,遇事全推老世伯;張皇失措,大權旁落丫姑爺。
這是一副藏頭聯,上下聯分藏端、張兩人。“端拱”是正身拱手的樣子,指端方在張之洞面前恭敬有禮,莊重不茍。端方與張之洞之子張權以兄弟相稱,有金蘭之契,因此以世侄身份謹事總督,遇事罕有自己的主張,只說“待請示老世伯。”總督與巡撫職權上并無高下之分,端方這樣做,看上去是尊重張之洞,實際上是在推卸自己應負的責任,不過對喜歡攬權的張之洞來說,端的耍滑頭恰正合他的心意。下聯“丫姑爺”,指張彪,時張彪任提督,湖北人傳說,張之洞以其通房丫頭嫁張彪,故有人送給他這樣一個雅號。通房丫頭是指名義上是隨女主人陪嫁到男家的婢女,實際是男主人姬妾的人。張之洞攬得大權,又旁落于丫姑爺之手。張之洞憑資望攬權,端方因缺少主見拱手相讓,張彪又借妻子與張之洞的特殊關系代張之洞用權,稱得上是官場上不是奇事的奇事。
皇帝也成為譏笑對象
九五之尊的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歷史上很少見到有誰拿皇上來開玩笑的,更不要說諷刺,但在清末,這個禁區被打破。
大約從1845年起,受鴉片戰爭打擊,步入老年的道光帝就像眾多老年人一樣,貪圖政治平靜,耳根清靜,“惡聞洋務及災荒盜賊事”。于是善于體察皇上心情的大臣,尤其是軍機大臣也就報喜不報憂,對那些擾亂皇上心緒,破壞平和心境的事,就千方百計封殺言路,掩飾真相,而專揀那些喜慶的、好聽的事說給道光帝聽。于是有人寫了一副對聯來諷刺這一狀況:
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樂;是、是、是,皇上天恩臣無事。
這是一副諷刺道光朝君臣的對聯。“著”即“喳”,與下聯的“是”一樣,都是“臣明白”或者“臣遵旨”之類的應答聲。面對積重難返的朝政和風雨飄搖的江山,道光帝只求能夠安安靜靜樂享余生,而身邊那些擔負著輔佐皇上治理國家重任的大臣,也乖巧得很,既然皇上喜歡清靜,那就給你制造清靜,自己也正可借此樂享清靜。于是,這些大臣在皇上面前凡事一味點頭稱是,就成為他們應付皇上的最佳方式。殊不知,他們的所作所為恰是在合力為清王朝挖掘墳墓。
(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