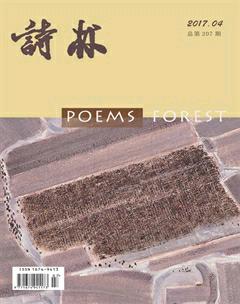文獻發明家與風景沉思者
馬小貴
縱觀張存己這幾年來的寫作,對歷史內容個人化的重寫是其寫作的主題之一,沿著這條線索,他極具公共性的個人制作也逐漸走向完善,寫于2014年的《草木深》就是一個例子。《草木深》回應歷史是通過改寫歷史的方式完成的,長久以來被傳頌的“伯牙叔齊”的故事,其中寄寓著延續了幾千年的“義利之辨”的精神傳統,然而對歷史人物的招魂,沒有帶來任何拯救和安慰,就連承載精神寄托的亡魂最終也敗給了唯利是圖的當代潮流:
伯夷和叔齊們便排起了好長一隊,他們
輕輕地
避開人家燒下的紙灰堆,淋著細雨,就跑
下了首陽山
——《草木深》
“伯夷和叔齊們便排起了好長一隊”有出奇的反諷效果:民族精神的亡魂代表和現世的勞作者們在此刻共享了一種當下常見的生命狀態——排隊。“排隊”的隊伍中擁擠、焦躁的形態,是典型的現代人病癥的表現,而排著長隊無限等待的原因大多數時候連排隊者自己都不明所以,物質利益的誘惑如魔咒般在無形中作祟。堅守道義還是隨勢而變?在詩的結尾令人措不及防的是,原本一度考量人心的兩難選擇在今天已經完全不再成為一個問題。與《上杜將軍二十大壽》一樣,張存己在《草木深》中依然表達了他對于歷史進程充沛而自信的把握能力,反諷式的招魂延續了他之前的寫作策略。在此后,《回憶莎菲女士》和《東方子道論》等詩,都顯示出張存己重新編排歷史、發明歷史,并從其中發現奧秘、呈現荒誕的出色能力。我們對這類詩歌仔細閱讀、揣摩之后,無法不注意到詩人的專業歷史研究者的身份。夯實的歷史知識為他的寫作打開了一個巨大的可抒寫空間。盡管他在詩中扮著鬼臉說所有都是“一場天人交感的大夢”,但在這一系列帶有杜撰性質的文獻后背,有一種對歷史把戲的警覺。這些以發明文獻為手段的詩中往往有動人的真誠,背后是一道道充滿懷疑和批判質地的聲音,它并不提供具體的生活觀點和價值尺度,而是傾向于在修辭與現實之間表現一種品質,一種毫不妥協的品質。
這種品質可以解釋為一種避免寫作被繁復花哨的修辭所吞噬的自我意識。因為真正的主體,無論面對被寫進教材的學科知識,還是身陷其中的切膚生活,都會保持一種疏離感以發覺更多真相。為了這種疏離感和反思性,詩歌對語言向外捕捉力的要求優先于語言的自足性,在此,張存己選擇了更加平實、清晰的語言風格,這也是他的詩歌在同齡人寫作中很特別的一點。就我目前有限的觀察來說,90后的寫作者,尤其是身處學院的年輕一代,大多以技藝的繁復、選詞的輕盈和詩意的跳躍為風尚,這形成了一片華麗的詩歌面貌,放逐詞語所指的寫作能量為豐富詩歌的形態帶來不少可能。然而同時,我們相信,詩歌總會是某種文化意義上的聲音,在它個人化的發聲背后仍然有強烈的交流和回饋愿望,寫作者必須重新領會“言之有物”這一最樸素的教導。語言不會僅僅滿足于詞語的組合、拼接、排列等無意義的游戲(當然這種無意義也被認為是一種意義),重要的是,如何在語言的肌理中把現實聯結在一起。雖然他早期的比如《安魂曲》等詩還帶有在詞語表面滑翔的快感,等到寫出《草木深》、《合歡》和《陰天去榆林路》時,張存己已擺脫了漂亮修辭的誘惑,轉而發展出一套以敘事為主的抒情風格。在那些整體上具有敘事特征的詩中,某些小說手法以保留其精華的方式納入了其中,沉思和詰問余音般在詩行結束之處繼續回響。這種不緊不慢的節奏屬于一個風景的觀察者和沉思者,而觀察和沉思也是知識者一種獨有的道德姿態。
張存己沉思的能力在重現記憶的詩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記憶常常面臨記憶的不忠,記憶因其美化效果而常常淪為普泛化的懷舊情緒。當里爾克說“詩是經驗”時,他是在強調一種對記憶冷靜、綜合的處理能力,也就是說,思考記憶而不是任記憶發揮,重現記憶而不是被記憶所吞沒。張存己寫成長經驗的那些作品,比如《合歡》《車過洛陽》和《歷史性》等詩,一顆顆閃光的孤獨的心靈擁有一種超越年紀的察覺能力,保留了成長中這種孤獨也就意味著保留了對記憶的忠誠。張存己不是以一種成熟理性的成年主體對往日經驗進行歸納式的總結(這是懷舊濫觴的一個常見原因),而是借用了他身上一直攜帶的可愛面具——即兒童和少年特有的懵懂、幼稚和不諳世事:
可是為什么,我真的想知道
為什么那時我依然
會覺得
不快樂
——《合歡》
媽媽,我已經聞見了楊樹的影子
今晚我第一次害怕到四川去
——《車過洛陽》
太陽很快就要落到高架后面去了
不是嗎?
——《歷史性》
為了重現記憶的原貌,張存己在這些詩中選擇了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講述,疑惑、好奇和敏感的天性在聲音上多表現為呢喃、疑問和自問。某種意義上,張存己讓記憶中的人說話而非記憶者說話。正是這種混合了神經質和疏離感的性格,反而使詩中未成年的抒情主人公具有了驚人的發現力。《合歡》寫了一個孩子幫他的父親去郵局寄信的故事,在去寄信路上他觀察到的人群和事物卻引起了他的憂郁。一切都看起來明亮而有活力,“為什么那時我依然/會覺得/不快樂”呢?既非戰亂年代的顛沛流離,也非離亂家庭的殘破不全,那些平常無奇的童年風景是在何種意義上為詩歌提供了有效的素材?實質上,孩子眼中的風景也正是他那顆孤獨心靈的具體內容。“我”即這個十二歲孩子也是柄谷行人意義上的風景發現者,而風景是和孤獨的內心狀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切如常的表面背后那些不可思議和神秘的東西,只有在孩子的目光中才得以顯現,日常生活的神秘性與孤獨心靈互相照亮。
成長時期對世界的疑問和沉思,主要表現為一種“童年性格”,即天真的性格。在后來的寫作中,張存己詩中的這種“童年性格”已經超越偏好而發展成為一種特征。比如《綠色校慶日》制作了一個短小的卡通片寓言,閃爍著頑皮和想象;《荒草中的一日》中那個老實木訥的大男孩說:“你知道,我從來都不是那種/ 很會交朋友的人”;《記夢》中發出的漂浮的聲音:“你在做夢嗎”“你在找我嗎”“我在做夢嗎”……像一個囈語的孩子仍然對恍惚世界的意義窮追不舍。“童年性格”的另一個表現,是張存己詩里那種擺脫重力、飛向天空的想象慣性。在《論童年》中,目光穿過窗外,“讓人可以輕易望見遠處的鐵塔/和樹頂上的云”,那是我們在發現神秘之后對天使的渴望。《論老年》則有這樣的句子,“此刻,若他伸出手,抓住壁櫥里/晃動的燈繩,像從金色的沙丘上摘下/一朵低懸的云”,衰老腐朽的身體依賴著想象完成了最后一次輕盈的采摘。即使是在《海上花》暗露情感的詩中,也有“你卻向我投下紅樹林的影子/幾乎高如天穹”這樣突然凌空的思緒。對風景的發現始于沉思而最終抵達想象。“童年性格”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完整的沉思者的形象,像宗教繪畫中的天使那樣,永葆童貞同時擁有對世事人心天賦般的洞察力:他既是內觀的,顯得憂郁寡言,在踽踽獨行和自我疑問中發起對世界的偵察;他又是向外開放的,常常憑窗瞭望,以天真的“特權”沖破生活的局限。張存己選擇面具化的方式,是因為許多他企圖揭示的東西都是成人所無法抵達的,“成熟心態”的盲點在這些詩中得到了克服,“兒童性格”為張存己沉思世界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路徑。
摘掉了天真的面具之后,作為風景沉思者的張存己正面表達了對現實境況的觀照。《陰天榆林路》這首詩透露出強烈的“中年氣質”,以一個旁觀者的形象,緩慢地行走在這種壓抑的生存景觀中。蘇珊·桑塔格在其討論攝影的一書《旁觀他人的痛苦》中討論了旁觀的倫理:如何在旁觀時避免一種自我的優越感?因為缺乏一種感同身受的理解,被觀察的對象常常在比較中淪為劣勢的存在,觀察者在這種比較中無形中獲取境遇的、道德的、心理的優勢。張存己的深刻性在于他一開始就抵擋住了居高臨下的誘惑,在耐心地描繪這幅后工業時代蕭條景象的同時,想要與本地人發生某種聯系,并不斷小心尋找突破的機會。沉思者不止于旁觀。張存己的姿態在這首詩中十分明確:“當我的頭頂堆滿豐潔而肥膩的積雨云時/我也多么像一個睡不醒的本地工人。”對本地工人的觀察、揣測,以至最后以睡眠的方式加入這個沉默的共同體,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張存己想要通過寫作而觸及的那個廣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