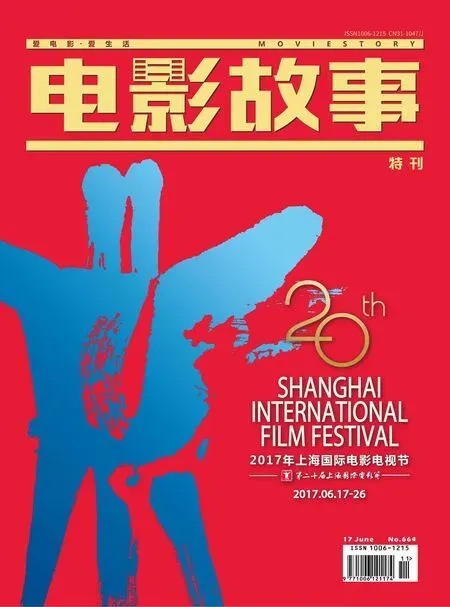王小帥
王小帥
亞新獎
主新席
中國導演

王小帥一直以來都被譽為中國第六代導演的領軍人物之一,在時代的變遷中,忍受著主流文化消費市場的折磨,因為他的電影夾雜著濃重的藝術氣息,有些沉悶,并不怎么好“看”。但是,他影像中的“邊緣人”,卻是對這個時代最好的記錄,似乎在宣揚“我的攝影機不撒謊”。因此王小帥被美國《商業周刊》這樣評價,“你的堅持對國家和民族生活產生了廣泛影響, 用電影的方式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態度, 并帶給未來以無窮的希望。”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他表現得有些“狡猾”,他說:“我覺得我不好解釋, 也不想做過多解釋。很感謝《商業周刊》對我的褒獎。”這一“殊榮”里,王小帥顯得尤為難得,況且他多次登上世界頂級電影節的舞臺,在電影上的成就早被大眾所知。如今,王小帥被邀請出任第20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評委會主席,他的專業,他的態度,或許會在這里留下又一個說不完的故事。文/何小威
都市與鄉村:漂泊的“電影夢”
王小帥近些年幾乎保持著同樣的造型:極短的黑發,一副黑框眼鏡,一件白色襯衣,一雙黑色皮鞋。內斂的神情、深邃的眼神和咧嘴的微笑使人覺得他不像一個奔波于片場的導演,倒更像是一位鄰家大叔,有一種熟悉的陌生感。因為豐富的人生經歷,王小帥的身上,有上海“小男人”的特點,也有貴州人簡樸的特質,還有北京人豪爽的個性。
1966年王小帥出生在上海,后隨父母遷往貴州,在武漢讀過兩年書,15歲考入中央美院附中,19歲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專業學習。從都市到鄉村再到都市,風華正茂的王小帥過早地感受到了漂泊之苦,也養成了關注身邊人的習慣。“我覺得我好像就找不著家鄉。因為我的父母等于說離開上海就一直飄著,我也一直跟著我父母漂泊,邊上都是認識一些新鄰居而已,沒有‘扎根’的感覺,所以我挺有點耿耿于懷的。”他這樣解釋自己漂泊的心態。
在電影學院四年,因為看到過很多法國新浪潮、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電影,尊崇費里尼為精神偶像的王小帥,逐漸將興趣轉向了藝術類電影。“這些電影對我們直觀的影響其實并不大,只是讓我們知道電影也可以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王小帥說,“這讓我們明白其實拍電影很簡單,不一定非要有戰爭和歷史,甚至不用燈光,扛起機器就可以上街拍。”于是,他在分到福建電影制片廠之前,就招呼了一幫朋友,拿著攝影機到街邊胡亂拍攝。拍攝完后,就聚在餐館喝酒、胡侃,仿佛過上了“快活”的日子。漫無目的的拍攝,注定要失敗。王小帥說:“到了第二天再用BP機呼人都呼不到了,拍攝也就流產了。”
1990年,王小帥被分配到福建電影制片廠,開始了籌拍電影,尋找投資,賣拷貝的“前”導演生活。也許是他太過年輕,年輕得有些輕狂,一心想著像“第五代”的張藝謀、陳凱歌一樣,在艱苦的環境下拍出一鳴驚人之作,從此真正地擠進電影圈。殊不知,拍電影的現實困難超乎了他的想象。不過話說回來,這種標榜也顯示了王小帥拍電影的野心,企圖走一條有別于“第五代”風格且標新立異的電影之路。但是,王小帥忘了,這并非簡單的“街拍”,也并非誰都能達到如安東尼奧尼《放大》那般的高度,“以至于自己追求目標定得太高,后來的路,果然走得很累。”王小帥的這種自我辯解,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宣告了他對于高品質藝術的追求。時隔多年,王小帥回憶起這段時光,感慨萬千,說:“現在想想那時候確實有點少年輕狂。”
挑戰與堅守:時代的記錄者

作為第六代導演群體中頗具思想氣質和作者氣質的王小帥,作品中總是流露出一種鋒芒,既“非常簡單”,又帶有時代文化語境變遷的精神之氣,“是當時那個年齡段絕大部分藝術家、相當多中國人的共同感受”。在數十年的創作生涯中,王小帥拍過不少電影,如《扁擔姑娘》《青紅》《日照重慶》《闖入者》等。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王小帥“不再單純追求影像的力度,而是人文的深度,其作品蘊含著一股嶄新的感染力,來源于厚重的中華人文本身的純凈之力”。或者說,王小帥對于人性的悲憫,對于人文厚度的不斷求索,被他移入了影像之中,并且透過時代的敏感點,關注到了這個時代的人群,諸如農村小孩到城市打工、想出國的偷渡客、個體創傷等。正因為這樣,王小帥的電影才顯得尤為重要。更何況,他用一個時代的故事,呈現出了社會的真實面貌——“細說平淡人生,靜觀社會大相”。
2005年,王小帥憑借《青紅》在戛納電影節“走紅”。在中國“第六代”導演群體紛紛遭遇票房和藝術雙重危機之時,王小帥的《青紅》問世,無疑有其獨到之處。作為一部文藝片,《青紅》的價值并不在于票房,而在于它順應了時代文化的精神氣氛,凸顯了“現代審美意識”,并且具有超前意識,把握住了現代化進程中人性異化、人格分裂的種種危機。此后,王小帥延續了這一風格。在電影《日照重慶》中,王小帥在文藝片的道路上顯然走得更為徹底。片中,反打鏡頭和晃鏡成為表現中年人群痛楚與無奈的重要手段,預示著人內心的不可捉摸。不得不說,王小帥掌握了“記錄時代”的技巧,能夠用相對樸實的拍攝手法直面人的內心,同時引導觀眾走進到角色的精神世界。
如果說《青紅》是通過“愛情與時代的錯位”表現人的壓抑,《日照重慶》是通過父子關系表現人物因無奈而心生的疏離感的話,那么《闖入者》則在歷史的追憶中,嘗試著“過來人”個體自責的懺悔與救贖。影片延續了王小帥一貫的“小人物承載大歷史”的敘事策略,個體記憶、家庭記憶、集體記憶和家國歷史相互融通,使個人化的敘述有了大歷史的蘊涵。但是,王小帥又在影片中進行了一些類型片的嘗試,加入了懸疑犯罪元素。對此,王小帥說:“一個導演,不需要觀眾為他個人的情懷或情結買單,也不需要和觀眾解釋他因為這部電影付出或獲得了什么,他需要提供給觀眾一部好看、有趣,能夠一直吸引他們并且有回味的電影。我自認為我做到了。”
“得獎和票房都不是衡量一部作品好壞的標準”,王小帥認為“要給電影留一些尊嚴,留下點社會變遷的影像”,實現“個人表達和記錄時代的文化作用”。如今,王小帥出任第20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評委會主席,他將以這一標準去衡量一部作品的好壞,發掘新人,甚至提攜新人。“我相信我們評委會會以公平、公正以及專業的態度完成這次的評審工作。”王小帥如是說。當然,我們也期待,此次王小帥攜手亞洲新人獎評委們一起助力新人導演,通過追溯電影的本質,為我們帶來更多的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