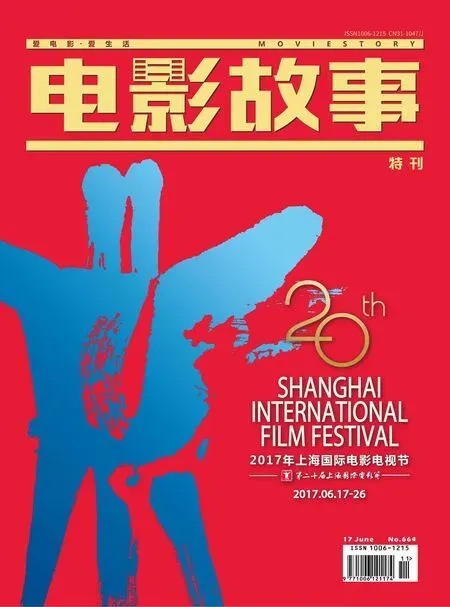李檣
李檣
金爵評委
中國編劇

永遠不為癖好而寫作
史航曾經(jīng)用“很清醒但很消極的天才”來評價編劇李檣。但李檣并不認為自己消極。“我是悲觀主義,但悲觀主義不等于消極,是不再奢望什么東西,不再自我麻醉,也不再自以為是。”在他看來“悲觀主義就是認清了人生的某種端底”。很早之前,李檣就已經(jīng)憑《孔雀》《立春》《姨媽的后現(xiàn)代生活》成為中國認知度最高的編劇之一。后來,《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黃金時代》再次將他推向各大電影獎項的領(lǐng)獎臺。但他始終沒有沉浸于寫作,甚至很少將自己完全代入角色的情感中,“永遠不為癖好而寫作”是他的底線。哪怕是早期有一定自傳色彩的《孔雀》和《立春》,也都刻意保持了冷靜的距離。
李檣創(chuàng)作時的狀態(tài)近乎冷酷,這或許與他的軍人身份有些關(guān)系。1987年李檣入伍在河南軍區(qū)當了文藝兵。他總是下基層演出,去縣城、礦山或者軍營,目睹人們的艱難生活,自己也顛沛流離。李檣說,當過兵的經(jīng)歷讓他比同齡人更清醒。中戲畢業(yè)之后,李檣先是被分配到北京戰(zhàn)友話劇團,兩年后轉(zhuǎn)業(yè)到家鄉(xiāng)河南安陽的文化局做編劇。始終苦苦尋找著寫作者可寄托之地,最終選擇了重回北京。后來,他在《立春》里寫王彩玲,一個生活在小縣城卻癡迷歌劇的格格不入者,數(shù)次折返于故鄉(xiāng)和北京之間,“如動物追逐水草”。
李檣創(chuàng)作的劇本《孔雀》描寫了安陽一個五口之家的遭遇。他曾在后記里寫,主人公們代表了三種人,姐姐是理想主義的;哥哥是實用主義的;弟弟是虛無主義的。劇本里的主人公們都想沖破命運,但卻都被命運馴服了。李檣身上也許有這三種人的影子,但他對于創(chuàng)作卻始終持一種近乎潔癖的理念—“我覺得人一生如果能夠從事自己喜歡的職業(yè)是最大的自由和幸運”。決絕純粹的李檣,在這一次的評委隊伍中成為特別的存在,編劇的身份也使其將肩負起為好故事加冕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