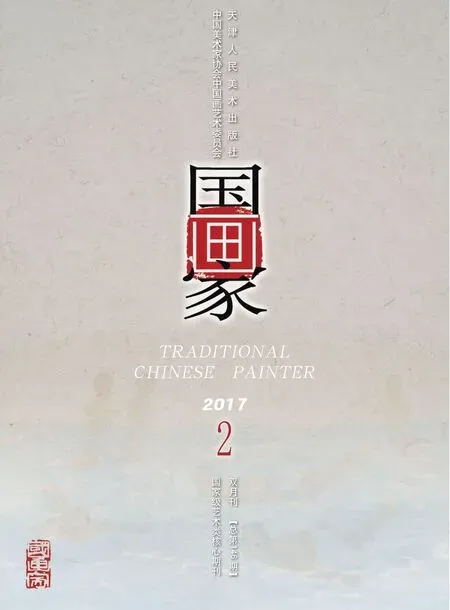“東方美學”與“水墨”的邂逅
——探尋“東方美學”如何在現代語境中發展“新工筆與新水墨”
姜向陽 孫國喜
“東方美學”與“水墨”的邂逅
——探尋“東方美學”如何在現代語境中發展“新工筆與新水墨”
姜向陽 孫國喜
中國傳統的水墨繪畫在歷史的長河中凸顯出獨特的藝術魅力與深刻的哲學內涵。近現代以來,在復雜多元的藝術思潮之中,藝術家們對于有關傳統國畫改良與發展問題的探討似乎從來都沒有停歇。因此在這種探討與爭辯的過程中,像“水墨畫”“實驗水墨”“新水墨”等相關詞語就跳進了人們的視界之中。
當然不可否認討論和研究傳統國畫的現代轉向問題是一件好事情,但我們的目光不能僅僅放在“轉”與“不轉”的問題上,而應將精力放在探尋水墨繪畫的內在情感與價值精神如何在現代藝術的語境中得到表達。實際上,藝術家們可以思考得簡單一點,不論是傳統的國畫、實驗水墨還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新工筆與新水墨,它們其實就是一種視覺表現形式而已。好比八大山人的繪畫作品,在明末清初就已具有強烈的個人情感和深刻的哲學感悟,而八大的作品較東晉顧愷之的繪畫則有了清晰明確的審美趣味和精神內涵。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八大的作品比顧愷之的畫更具“現代氣息”,而今,我們毫不猶豫地將八大的畫歸類在“傳統繪畫”的范疇里。那么,東晉時期的顧愷之又怎會預見經過漫長歷史的發展與演變而形成的“文人畫”藝術風格形式呢?可想而知再過千百年,當今所謂的“新工筆與新水墨”也會被我們的子孫后代看作一種傳統藝術風格的繪畫,因此“傳統”這個概念是在相對意義語境下產生的。
無論水墨創作風格如何發展與變革,其內在核心思想才是最能反映作品真正價值的。2016年11月,上海言午畫廊舉行的“言——東方美學的再發現”水墨展就充分地從水墨作品的美學意義上進行了一場精彩的“言說”,而這場“言說”是由藝術作品本身發起的,旨在通過展出的作品與展覽的形式來探索“東方美學”的現代意義。“言”展覽的策展人朱小鈞強調了此次展覽的主題是:中國傳統的再探尋,東方美學的再發現。為何在當今倡導對“東方美學”再發現,這是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的。“新工筆與新水墨”的出現的確提供給國內青年藝術家一個非常輕松、活潑的發展空間,他們可以自由地用水墨材料隨意地表現和傳達他們的精神思想。雖然自由的環境可以為我們帶來優秀的藝術作品,但也能帶來諸多“不良文化”。在層出不窮的青年水墨藝術家和堆積如山的水墨作品中,我們既看到了水墨作品的生命在現代社會文化中的發展與延續,也看到了一些帶有“消極色彩的藝術元素”在作品中體現,因而“思辨”的意義在現當代水墨創作環境中就顯得尤為重要,優秀的傳統水墨作品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和藝術震撼,更是引發了人們在哲學層面上關于精神與價值的思考。當代水墨不能因為擁有寬松自由的發展空間而失去了對于水墨核心價值的認知,所以當代水墨畫家在基于主體創作的過程中既要牢牢把握好藝術作品的價值觀念,也要將時代精神這條主線貫穿在作品當中。中國的傳統文化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閃爍著耀眼的光彩,尤其是東方的美學觀念在幾千年的沉淀過程中更是深刻地體現著傳統文化的價值與內涵。
這次“言”主題的水墨展覽中邀請了高茜、賈寬、李百鳴、李娜、李振、秦艾、魏久捷、徐華翎、徐累、謝天卓、楊東鷹、袁銘林、曾健勇、曾志欽、朱小坤、祝錚鳴等17位在新工筆,新水墨領域具有代表性的中青年當代藝術家參展,他們的作品一方面強調了“新工筆與新水墨”的當代性,另一方面將中國美學思想加以在作品中體現,其中包含了以“中國傳統典故”再創作的《史記·玄武門之變No.2陽謀》,還有以成語“龍馬精神”和“一葉障目”創作出的《龍馬圖》和《障目》,以及根據經典小說人物形象“孫悟空”創作的繪畫作品《大圣6》。這些作品在闡釋東方美學觀念的過程中與生活在中國現代社會的人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生活在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中的人們對于各種成語和歷史典故耳濡目染,他們長久地沉浸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東方美學中而不自知,這些文化和美學觀念就如同“空氣”一樣環繞在他們的身邊并不能使他們獲得清晰的感受,而看到“言”主題的水墨作品時,這些由大眾所熟知的“傳統和美學”通過采取現代的表現手法和水墨語言而被闡釋出來,使人們感到新奇又熟悉。從這個角度上來分析,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對于創作的主題選擇是至關重要的,如果選擇了不恰當的主題不但不能很好地傳達出藝術家的創作思想,而且還會錯失一次與大眾產生共鳴的機會,這樣來看,“新工筆和新水墨”除了要帶給人們視覺沖擊之外,還要提供一種深層內涵的現實意義的思考。
中國傳統水墨講究“文人精神”,而“文人精神”又是中國文人畫的核心價值,文人墨客通過筆墨抒發心中的情感思想,暢快淋漓地將所想表達的內容描繪在紙上。這種強烈的個人情感色彩在文人畫中的發展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我們欽佩古人高超的繪畫技法與思辨的哲學精神,古人作品中極簡的筆觸和落墨的瞬間是情感與形式的高度統一,是人格與藝術的高度結合,所以文人畫的文人情懷才顯得彌足珍貴。因而我們會思考當代水墨的精神何在,價值何在。太多的當代水墨作品只是在形式上來迎合當代藝術的大環境和大背景,將花哨的、前衛的元素附會在作品上,這里不是批評當代水墨不能擁有前衛的元素,而是想說明沒有精神內涵、價值導向的花哨作品最終會走向凋零。中國是一個講究文化、講究歷史傳承的國家,這是在長期的發展與演變過程中植根于人們意識形態里的,潛移默化形成的,東方美學觀念也會扎根在孕育我們成長的文化土壤之中。東方美學再發現的意義就在于將傳統的審美經驗加以整合為現當代所用,當代水墨的發展完全可以跳出“傳統”這個大的范疇去尋求新的“生命之撐”,但我們也沒有理由完全摒棄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文化財富。東方美學中最為核心的范疇就是“意象”,藝術家通過對“意象”表述使藝術作品獲得更高的精神追求。“意象”中的“意”可以理解為藝術家作品中的思想情懷,而“象”可以理解為傳達思想情感的載體。“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出自唐代詩人王維的《山居秋暝》,而這四句中出現的“意象”勾勒出一幅空靈幽美的自然景象,這種通過“意象”而展現在人們思想意識形態中的畫面更加具有一種靈動的空間美感。“言”主題的水墨畫作品展中的展出作品就是抓住了“意象概念”,通過畫面的構思、布局、表現主體、色彩搭配組合成了一幅幅生動的,具有鮮活生命力的“意象”性藝術作品。藝術家對于“東方美學”的把握主要體現于對所想表達物象的概括能力,他們通過對元素的提煉與加工形成具有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和符號,這不僅可以突出表達所想描繪的物象,也可以幫助藝術家總結尋找屬于自己的繪畫藝術風格,這對于一個藝術家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言”主題水墨畫展覽作品在突破繪畫主題、表現形式的情況下,對于展覽的布置上也做出了別出心裁的創新之舉。立足中國傳統美學基礎,將更多能夠體現“東方美學”觀念的元素加入到展覽的展示過程中。明清家具、高古石刻等中國傳統美術元素的加入使得展覽所處的環境擁有了一種“東方美學”的趣味性審美環境,置身于展覽現場的觀賞者除了能近距離地觀看繪畫作品,而且還能與這些老家具、老物件所形成的“情感環境”產生共鳴,此舉在營造古典美學的觀賞氛圍時,更將觀賞者帶到一種“東方美學”的虛擬環境之中。策展人的用意是在于通過這些不同的“美學元素”的組合來找尋一條由古代連貫現當代的“線索”,讓“東方美學”以更加真實、自然的面貌展現在觀眾面前。
無論是“新水墨”還是“新工筆”,都是新一代藝術家在漫長的藝術道路中對于藝術堅持不懈的探索。我們既要尊重藝術作品,更要尊重藝術精神。我們寄希望于水墨藝術家在當今寬松自由的藝術環境中能夠堅守本心,堅守對哲學精神的把握,創造出有價值,符合時代精神的優秀藝術作品。基于此,藝術家們應該不斷地夯實自己的文化內涵和精神思想而獲取更加富有價值的創作思路和靈感,我始終堅信不朽的藝術作品必定能傳達出高尚的內在精神價值和符合時代氣息的審美趣味。“東方美學的再發現”只是從美學觀念上來探索“新工筆與新水墨”的發展道路,而探索和發展“新工筆與新水墨”的思路和方法有很多,在多元文化的碰撞過程中,我們期待遇見更加青春而美好的水墨藝術作品。
1.陳剛.《究竟什么是“新水墨”》.美術[J].2014.
2.耿涵.《新水墨概念探討:從“新水墨”的語境與意指談起》.天津美術學院學報[J].2013.
3.賈方舟.《柳暗花明:走向當代的新水墨》.文化研究[J].2014.
4.彭修銀,李穎.《東方美學中的“意象”理論》.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2005.
5.彭修銀,齊靜.《東方美學原始意象的表現形態》.湖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2004.

魏久捷 史記·玄武門之變 No.2陽謀100cm×210cm 絹本設色 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