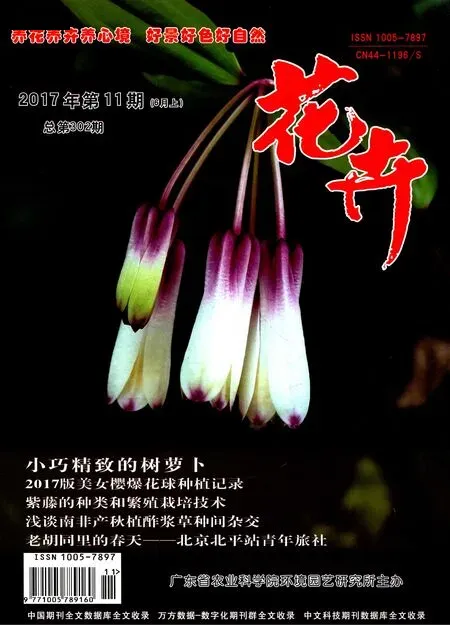鐘情于深秋的山胡椒
安徽/許青山
鐘情于深秋的山胡椒
安徽/許青山

一直認為,秋天才有落葉。可昨晚的一夜強勁的風雨,糾正了我對落葉的認識。晨起上班,在公交車站,看見環衛工人用掃把很吃力地打掃緊緊貼在地面上的落葉,我才知道春天也有落葉的。四季常青的樹木,自身也存在著新陳代謝的規律。其實,落葉屬于春夏秋冬的,每個季節都有。只是秋冬交替之際,明顯于春夏罷了。
提到落葉,突然想起皖南山區的一種名叫“山胡椒”的雜樹,每到深秋,它與其他灌木齊心協力,把綿延的山體,涂抹得色彩斑斕。看見野漆葉紅了,鹽膚木黃了,它也跟隨打扮,先是淡黃,后是深黃,而且,身影遍及山體,這里一叢,那里一叢,盡染山體,把山體打扮得紅紅黃黃,仿佛穿了件新制的花衣,鮮艷、華麗。每當這個時候,我都要吆喝一群喜歡行走的好友,去欣賞它的杰作。好友見之,無不歡呼雀躍,嘖嘖稱贊。深秋的皖南,驚艷的不僅是烏桕樹、銀杏樹、楓樹,而且也有山胡椒。面積之廣,規模之大,令人大開眼界。站在高山頂上,俯瞰眼底層林盡染的起伏山巒,你一定會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語:太美了!太漂亮了!你一定會對大自然的調色功能佩服得五體投地,豎指點贊。
然而,我仰慕的不止在于它的美麗,更在于它對深秋的鐘情。
秋風掃落葉。按理說,秋天的黃葉,經歷秋風,至冬天已經落盡。但山胡椒的葉子絲毫沒有想離開枝頭的跡象,介乎此,當地人稱它“假死柴”,意思是葉子看似“死”了,其實還是活著,即使在寒風凜冽的冬天,堅持留戀枝頭,一任寒風勁吹,消褪它的黃黃色彩,直至變暗,也矢志不移。一直挺到春天,待到新葉綻放,它才離開枝頭,悄然落地休憩,讓人們真真切切看到植物的有情,不僅是飄零枝頭的落花,而且還有忠實于樹干的落葉。
秋日山胡椒,人間更紅艷。宋代,始終把洗雪國恥、收復失地作為自己畢生事業的辛棄疾,是讓人景仰的;為了救國,把家產全部作為軍費,不顧個人安危,身陷囹圄,吟唱“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是可歌可泣的;“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抗金名將岳飛,是精忠報國的;為國雪恥、壯志不衰、僵臥孤村、尚思為國、夜聽風雨、馳騁疆場的陸游,是赤膽忠心的;白發征夫,濁酒念家,依然選擇在邊陲建立功勛的范仲淹,是令人敬佩的。明末清初的張岱,深感國破家亡的沉痛和悲憤,“披發入山”,布衣素食,游山玩水,用淺淡的筆觸,追憶成《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寄托對故國的懷念。方志敏、楊靖宇、劉胡蘭等革命志士寧為玉碎的獻身精神,體現的也是一種赤膽的忠誠。“心里裝著蘭考人民,唯獨沒有自己”的焦裕祿,給人們樹立的是敢于擔當,全心全意當好人民公仆的時代標桿。像這樣的人間“山胡椒”,不勝枚舉,正是有了這些“山胡椒”,人間才充滿了浩然正氣,時代正能量。
五一假期,戶外行走,在綠意盎然、生機勃勃、蜿蜒曲折的山道旁,我又看到了山胡椒,完成了新老葉子接力棒的傳遞,踏上了新一輪的征程。記得湯顯祖《牡丹亭》中的杜麗娘,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余秋雨也曾說:“健全的人生須不斷立美逐丑,然而,有時我們還不得不告別一些美,張羅一個個酸楚的祭奠。世間最讓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對美的祭奠。”但我從山胡椒的身上,卻看不到酸楚,它從舊葉中脫胎換骨,長出嫩綠葉片,從春綠中從容不迫地走向夏的繁茂,為的是在深秋,給人間深情送上一曲高歌的。同時,借助凜冽的寒風,考驗自己對深秋的堅貞。沒有想到,山胡椒是不喜歡凄美的,它永遠追求著美的釀造。
山胡椒的形象,極為平凡。在艱苦的年代里,人們常常砍來當柴火,干柴進灶堂,爐火燒旺旺。現在,有了煤爐、煤氣灶,很少用它燒火了,所以,這種雜樹的種族,迎來了繁榮的年代。如果在春夏,在滿山遍野的山體灌木叢里,想要一下識別,除非親近。可到了秋天,人們站在遠處,就可輕易識別,只因色彩的別致。冬天,只要見簇簇黃衣,便知它在癡情秋色。它,身影既不高大,也不以花色見長,只是擅長染色葉片,然后默默堅守,癡心不改,丹心于秋。于是,在滿山的植被中,我忽然悟到山胡椒這種植物的別具一格,心頭徒然升起一陣感動,蔓延著自己前方的路途,心想:即使平凡普通,但在自己的成長路途中,不必好高騖遠,而是立足本職工作,樂于進取,勤思好學,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極致,這樣的人生,也同樣精彩動人,讓人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