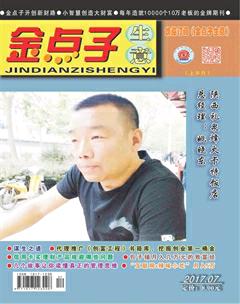在老胡同掘金的連鎖主題餐廳
邦邦
韓桐、袁寶和陳洋這三名北京80后小伙子將隨處可見的串串香生意做得風生水起,餐館的名字叫8號苑,在北京的80后人群中有著很高的知名度,僅僅兩年時間就開了三家店,擁有7000多名會員,一個月的流水達到五六十萬,還曾在央視的一家創業類節目中得到了雷氏照明創始人吳長江的300萬元投資。
餐廳像學校
2009年2月,在朋友那里得知西單后面的新建胡同有一個店面出租,小時候來回穿梭于那一片兒的韓桐就來了精神,覺得很親切,就租了下來,想開個餐館。他專門請來好幾撥父輩的有著多年老北京開餐館經驗的朋友幫忙設計,結果人家連門都不進,直接告訴他,“我不能幫你設計,這里太偏,開不起來,幫你就是害你。”
但這位“80后”沒被老輩兒的經驗嚇倒,盤算一下租金不算貴,自己努努力應該可以。
沒什么餐飲經驗的韓桐做起火鍋店,小店不過幾十平方米,只有16張桌子。連韓桐在內,店里的員工也不過寥寥幾人。
“當時我們沒做任何宣傳,唯一做的就是印了些傳單,發了不到兩個小時就被城管看到,800多份傳單沒收了;去大眾點評網投廣告很貴,索性就沒做。‘8號學苑大部分靠一傳十、十傳百的口碑宣傳。第一個月只是朋友來,但幸運的是第一個月沒賠錢,還盈余幾千元。到七八月就開始排隊了,來捧場的都是‘80后,所以我就覺得做‘80后懷舊主題這事可以做。”韓桐說。
由于自己也是“80后”,韓桐深深地喜愛小時候居住過的老北京胡同。為了讓很多年輕人重溫舊夢,在“8號苑”的第一家店的進門處韓桐貼了很多小時候的獎狀,餐桌前的白墻也弄成手繪墻,任憑顧客自己畫。
此后生意逐漸火爆,“8號苑”竟然顧客每天排隊。韓桐把一起租下的另一間門面也啟動了,開一家叫做“8號學苑”的新店,這次韓桐要做的是更純粹的“80后”校園主題,整體布局是學校課堂風格,進去吃飯叫服務員要叫老師;埋單的收銀臺那兒是一個大黑板,上面有校規、測驗題、課程安排(營業時間);餐桌是課桌的模樣,只不過中間挖空了放電磁鍋;椅子都是課桌椅那模樣的;餐廳整體布局也是課堂的風格,白墻綠漆;餐具是“80后”小時候的那些搪瓷缸、搪瓷盤。
“其實8號苑只是一個懷舊的雛形,我們計劃當時機成熟之后開一家主題餐廳,只是不知道要主打老北京的主題,還是80后的主題。”袁寶說。三人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長時間的思考,通過對市場進行分析,他們意識到做老北京主題飯館8號苑沒有任何優勢可言,因為老北京涮肉館太多了,更不乏像東來順、南門涮肉等老字號。而做80后懷舊餐館則不同,首先這個主題在北京還沒有人做,最主要的是三人本身就都是80后,了解這個群體的所思所想,他們知道愛玩愛鬧的80后在畢業以后面對社會壓力有著很深的懷舊情結。“我們當時就決定為所有的80后創造一個集體懷舊的地方,而這個最能凝聚回憶和人氣的地方非校園莫屬。”韓桐說。
只接待“80后”
韓桐的店之所以能在偏僻的胡同里讓顧客心甘情愿地等著排隊叫號,最吸引人的不只是裝修,而是上課式吃飯的方式。韓桐把新店的經營模式打造成上課形式,吃飯必須進行預訂。除此之外,韓桐還規定,“8號學苑”會員必須是“80后”,“70后”、“90后”都不能進。這個規定可不得了,一下得罪了經常光顧“8號苑”老店的顧客。
韓桐回憶,五月份新店開張時,老店門前排隊幾十人,新店這邊只坐了兩桌,但就是不讓老顧客進,氣得老顧客直罵他。盡管不停地跟人家解釋,但是韓桐就是不妥協,到了門的生意怎么就不做呢?韓桐認為,“當時我就是想做純粹的適合‘80后的店,如果放開兩不靠,‘70后覺得幼稚,‘90后不理解,就相當于一群喜歡鄧麗君的人中突然出現了嘻哈樂,會破壞氣氛,所以我覺得做就做純粹。”
來這吃飯的顧客都會參加一個考試,考試卷子正面是考生的信息和試題,反面就會有一個值日生的表格。如果愿意來店里兼職,填好這個表就有可能開始當“班干部”的體驗。“這家店里就沒有服務員,都是班干部,這些人全都是有工作的員工或學生,業余時間幫店里兼職。為什么不請服務員,因為服務員都是外地的,而且歲數也小,不理解‘80后,無法交流,所以我們這邊都是‘班干部制。他們有時間就跟‘班長協調排班,按時過來。別的餐館都怕過節,但我的不怕,一過節我的值日生們都來了。”和這些“班干部”在一起,韓桐絲毫沒老板的架勢,就像個大班的孩子一樣來來回回走動,看著同學們吃著火鍋,玩著游戲。
作為餐館的基本功能是就餐,菜品的質量才是一家餐廳存亡的關鍵,8號苑除了有秘制的串串香之外,還有招牌的“滅火器”和土豆泥等小菜,人均消費40元左右,現階段對大多數80后來說是一個聚會就餐的理想選擇,但是未來的路是越走越寬還是越走越窄還需要很多的摸索。
韓桐總是說自己的“80后”主題概念,感情多于商業。采訪當中,不停有顧客訂位,他直呼其名,貌似多年的哥們。掛了電話他得意地表示,這都是來這里吃飯吃出的朋友。時間長了,韓桐就成了“8號學苑”的頭兒,時不時地帶著大家出去玩。目前“8號苑”系列餐廳已經有7000名左右的會員。如果只在店里搞活動,一次才能容納幾十個人,但是一次“課外活動”就會影響幾百人甚至上千人,玩著玩著后來都成為好朋友了,也因此更加深了對“8號學苑”的感情,經常帶朋友來吃。
每次這樣的一個校外活動一個月就會花費四五千元,關鍵還得擔責任。為了安全,每次活動韓桐都得踩點2次,把一切安排好了。在“8號學苑”的墻上貼著很多他們夏天玩漂流的照片。除了校外活動,韓桐還組織了課外興趣小組,通過消費積分,積分抵錢,“學校”也拿出一部分來組織課外活動,比如足球、籃球、棋牌等。顧客中有很多文藝骨干,可以任意在手繪墻畫圖,上面有“80后”喜歡的藍精靈、一休哥,還有栩栩如生的變形金剛。“這些人太有才了,讓大家在這里展示才能,搭建一個平臺互相認識,資源互相共享,這就是‘80后的一個出口和平臺,也是一個線下的SNS社區。”韓桐說。
正是這股純粹的執著勁兒,讓這個純粹的“8號學苑”引起媒體關注,更吸引了大批來客,提升了其他兩家普通型火鍋店的業績,也使得這三家開在胡同里的小店,一個月的流水達到了50多萬元,毛利率保持在55%左右。
“8號苑”隨著韓桐的校園主題的逆向營銷,加之以餐廳為基礎的平臺化運作,人氣正越來越旺。
遭遇“60后”投資人
本來韓桐一邊和“80后”的一些朋友玩著,一邊慢慢擴大著自己的規模,已經很開心了,但是2010年“十一”參加了央視一檔創業類節目,遇到了雷氏照明的創始人吳長江,節目做完之后吳長江就以300萬元的投資與“8號學苑”初步達成了意向。
“吳長江的到來就像打了一針興奮劑,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的目標。”韓桐如此評價吳長江的加入。當天初步接觸時,他們都以為對方在做秀。沒想到第二天吳長江的助理就過來吃了一頓,感覺還不錯。
“過了十幾天,吳長江親自來了,我們一塊聊了兩個多小時。”這一聊盡管氣氛和諧,但是思路上還是產生了激烈的碰撞。
吳長江認為,“8號苑”是一個社交場所,他并不是在賣餐飲。如果再過10年,有些“80后”就40歲了,一個40歲的人是不會到你這個地方來交友的,因此這里不能只定義成“80后”。
這樣的說法讓一直沉浸在“80后”圈子中的韓桐一時有點無法理解,“我一直把這里當成不僅僅是賺錢的事業,還是給‘8()后搭建的交流平臺,因此我做的‘課外活動比‘課內的還多,比如每個月郊游、籃球賽、足球賽,這些都是餐廳掏錢。”畢竟是年輕的“80后”一代,走向現實但還有比較理想化的生存狀態。
但久經商場的吳長江卻有一個鮮明的認識,“反對這種交友方式的推廣,創業不是在做公益事業,創業是要賺錢的:”經過商量,兩人最后達成了共識,把目標人群定在20-30歲之間。在學苑發展壯大后,可以按照小學、初中、高中的方式把不同年齡層的消費者分類。變賣交友方式向賣衍生品方向發展,以后不光是賣餐飲,還賣這個年代的紀念品,或者做一些演唱會,搞旅游。發展不僅僅局限在北京,要走向全國。
資金有著落了,一個小飯館逐漸走向規范化的運營,韓桐感覺壓力還是很大,“本來想五六年之內扎扎實實在北京,但吳總投資之后還是提了一些要求,三年之后一線城市需要有幾家店。我們也有這種愿景,但文化定位還要商量一下。”
對于“80后”經營者與“60后”投資人的這次合作,目前來看是創意和經驗的結合,未來“8號苑”能否像“呷哺呷哺”一樣開遍全國,除了創意和資金外,還需要很多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