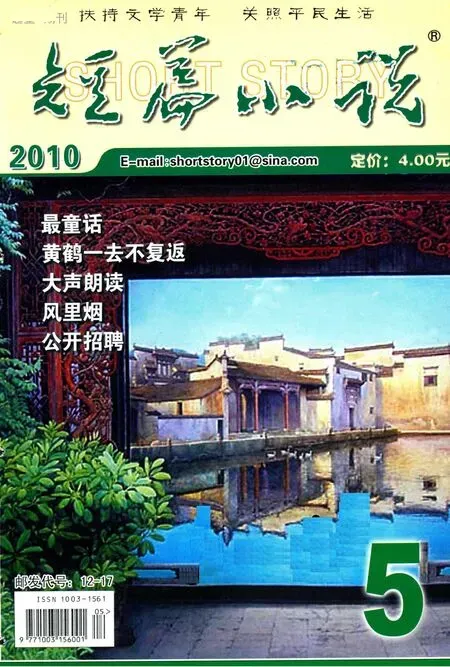艷婚記
◎高遠
艷婚記
◎高遠
一
我敢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相親更讓我激動的事了。我姐給我說這事的時候,我躺在城里醫院的病床上。我姐抽著臉,想哭,但沒哭出來。她說,小放,你回家不?我們今天就回家吧,你回家就能相親了。
我認為我姐這話一定是在騙我,至少也是在可憐我。我當初進城打工時曾立下雄心壯志,決心在城里苦干五年,為自己攢點錢回鄉下討個老婆。我快三十歲了,討老婆的事不能指望我姐,也不能指望我爹。但是,我才在城里干了兩年就把拼搏的本錢給丟掉了,現在只能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我對我姐說,姐,你不要騙我了,我成了這樣子誰肯和我相親?除非人家是傻子!
我眼下像一只落到地上的蘋果,轉眼就破敗不堪不成樣子。紗布纏滿了全身,腦袋上也是,我像一截硬邦邦的樹樁,鼻孔里枉然地喘著一絲生氣。如果不是我的眼睛老圓忽忽地睜著,眼皮怎么也合不上,旁人早以為我已經死掉了。不過我的確不想死,我走過的路那么短暫,還來不及在路邊摘顆桃子掐朵花什么的,就這么結束了,實在不甘心。還是我姐最了解我,最清楚我的心事。我看見我姐的嘴唇在哆嗦,她必須用兩根指頭同時把它們壓住,才能勉強和我說話。我姐說,傻弟弟,你不是有它了嗎?你有它了還怕沒有人和你相親?姐真不騙你,爹在鄉下正給你張羅呢,等你回家后就能相親了。
我姐說著話把一條胳膊抬起,給我看她手里一個紫色人造革提兜。她嗓子眼一哽一哽的,像突然有東西要從里面冒出來。她那原本干癟的提兜,在這一天變得異常飽滿。
這是你們老板賠給你的。姐說,有了這些錢你什么干不成?你什么都能干了!
姐說完這話,彎著腰蹲在地上放聲大哭起來了。
她以前不是這樣,以前她一進城就害羞,見了生人連話都說不了。但這次我躺到病床上以后,她整個人都變了。這些天來,她拎著她那只饑餓的提兜四處奔走,去我干活的建筑公司吵鬧,去政府門前喊冤,去信訪局、電視臺、報社,去所有能進入的機關和單位,差不多和整個城市吵翻了天。她總算沒有白忙活,她的提兜終于像一副酒足飯飽的肚子了。我過去以為我姐很愛錢,但其實不是。她蹲在地上手攥著提兜,像惡毒地掐著誰的脖子,她的指頭陷進皮革里,連關節都埋沒了。我說,姐,你不要掐那些錢了,再掐它們就會斷氣,然后也像人一樣死掉了。
姐哭得更厲害了,肩膀一抖一抖的,幾乎喘不過氣來。
衛衛在病房的窗戶前站著。衛衛和我是一個村兒的,我們在一個工地上干活,我躺到病床上以后,他被老板派來專門伺候我。他喜歡一動不動地站在窗前,像是要把自己鑲在窗框里。我叫了衛衛一聲。我希望他不要那樣傻乎乎站著了,他應該走過來勸勸我姐。我姐一哭我就難受,另外病房里還住著兩個病人,她不能攪擾了別人。
衛衛回過身,從窗前走過來。衛衛一看見我眼珠子就慌張地往地上滾,滾落到一個紅色塑料盆上。他把它拉到床邊,伸出手,從我腰間的紗布里抽出一根管子,膠皮的,把一頭放到塑料盆子里。做完這些,他又回到窗戶前,又那樣呆滯地站著。他的耳朵支棱著,他在聽。他想他很快能聽到一股綿軟的水聲了,最后他什么也沒有聽到。
我不想撒尿。我對他說,我想撒尿我就會告訴你,但是我現在不想。
衛衛沒有以前機敏了。他以前可聰明伶俐了,什么事都瞞不過他的腦子和眼睛,不然他也不會和張小紅談上對象。張小紅是個很艷麗的姑娘,走到哪兒都引人注目。如果不是張小紅自己告訴我,我一點也看不出她也是從鄉下來的。衛衛和她走在大街上,坐在熱氣騰騰的夜市上,偷偷摸摸地躲在街道旁邊的大樹背后。你只要一看見他們,就由不得心生嫉妒。我總是提醒自己,衛衛是我的好伙伴,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嫉妒他。但是我管不住自己,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象著我和張小紅待在一起的樣子。他們是多么驕傲的一對呀,那時候不但是我,工地上所有的年輕人都是又羨慕又嫉妒的。可惜張小紅后來卻出事了。
對面床上的一個老頭幾天前就要斷氣,眼下仍然在那里躺著。我姐一哭起來像給誰哭喪,搞得老頭心驚肉跳,一只雞爪似的手不停地按床頭的按鈴。幾個護士從門外跑進來,東張西望,又一路小跑著出去。接著她們又跑回來。她們手忙腳亂摘下床頭的氧氣罩子,打算給我戴上。
這時,我們的老板從門外走進來了。
老板身后跟著一個女人,他走到什么地方,身后都跟著那個女人,她是他的影子。老板很少到醫院來,他不喜歡醫院里的藥水味兒。工地上死過好幾個人了,我猜想他肯定是聞不慣死人的味道。
女人用一塊花手巾捂住了自己的嘴。剛捂了一下,馬上把手巾捂在老板的鼻子上。
老板說——老板拖著鼻音,聽起來像是感冒了,他對我姐說,這種事是誰都不想看到的。老板咳了一聲,走到門外去,在墻角里吐了口痰,然后又回來。他接著說,唉!不是我這個人不好,主意是你們拿的,丑話已經說在前頭了,給賠了錢病就不給看了,以后是死是活都和我沒有關系了。
我姐抹去眼淚從地上站起來。老板身材高大,她再那樣在地上蹲下去,看著就像是給人家跪著。我姐說,以后什么也不用你管了。他到城里來打工是為了掙點錢討個老婆,現在好了,我們回家去就把他的心愿給了了。
女人不斷拉扯老板的胳膊,老板掙脫她,向我走來。老板像大人物那樣伸出手,想在我腦袋上撫摩一下。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他說,這里的賬已經結清了,按照協議,你們今天就出院吧。
二
我那天從城里回來得很晚。我躺在一張木板床上,木板床放在面包車的車廂里,我姐和衛衛坐在兩側。我姐從小到大沒有過這種享受,她羞答答地坐著,胳膊都不知該放到哪里了。
車在路上顛簸了三個多小時,到我們村口時,天早就黑嚴實了。
村口圍聚了許多人。人們在車燈的指引下在村街上涌動,最后聚集到我家門口。
我爹在門口站著,手放在額頭上。他在用這種方法抵擋刺眼的燈光。他不習慣在夜晚看見亮光,我家的電費總是很少,我不在家的時候,他愛一個人坐在黑洞洞的土炕上,從來不需要電燈。
車還沒有停穩,我爹的手就過來了。他用勁在車門上摳,他不曉得怎樣打開車門,一個勁兒在摳。圍觀的人比他聰明,最先從門縫里擠進來的不是我爹,而是眾多好奇的腦袋。車燈熄了。街道上恢復了夜晚的黑暗。幾束手電筒的亮光穿過玻璃照進來,光線像游魂在車廂內浮動。
死了。有人說。活著還是死了?
人們都懷疑面包車內拉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尸體。我在城里從七層高的樓房上掉下來時就想到了,這種事是無論如何也隱瞞不住的。
滿和那家伙又有生意可做了。有人在黑影里說。
只要一死人,滿和就該發財了。又有人說。
滿和是個開花圈店的。滿和的生意是把紙做成花圈和高高的紙幡,然后賣給死了人的人家拿到墳地上去燒掉。他就是做這種生意的。
盡管我在黑暗中拼命向圍過來的人們眨巴著眼睛,但是,他們還是以為我已經死掉了。
圍觀的人群亂哄哄的。女人們在一邊唧唧喳喳,男人們嘴里叼著紙煙,擁擠著把腦袋朝我跟前伸過來。
我一被抬出車廂就看見了滿天繁茂的星星。四周圍很黑,星星在頭頂顯得異常明亮。我喜歡星星,一直都喜歡。在城里一看見星星我老想起鄉下,想起鄉下的家和我爹,但現在,我一看見它們就想起了城里,想城里路燈,街道,還有街道兩旁的大樹。我看見張小紅在樹底下站著,一雙大眼睛撲閃撲閃的,像有無數火花從里面蹦出來。我從來都不敢看張小紅的眼睛。她的眼睛像一個無底洞,我一看就會掉進去。我為這事沒少在衛衛跟前尷尬過。但是我現在一點也不害怕衛衛了,張小紅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看著我,我也盯著她。她還是把我的心思給眨亂了。不曉得我爹給我找的是哪家的姑娘,是不是和張小紅一樣俊俏、耐看?我總是把我喜歡的東西想象得離我很遠,其實,我后來才知道,張小紅是離我們村兒七八里路一個叫張氏堡的村子的。不過我知道我是在空想,張小紅出事了,連衛衛想娶她也沒有指望了。
我看見了我爹遲到的腦袋。我爹是好不容易才擠到我跟前的,他現在離我很近,鼻子幾乎碰到我的鼻子。一些清涼的東西從上面流下來,流到我臉上。我叫了我爹一聲,我爹粗重地喘著氣。我本來想問問他關于我相親的事,但是我發現他的喘息聲越來越重,像我家破爛的風箱,只得把到嘴邊的話又咽回去了。
街道上很冷,風無聲無息地從臉上掃過。我爹在黑暗中指揮我姐和衛衛把我往家里抬。我姐和衛衛累得滿頭大汗,卻始終把我抬不進家去。我家的門太窄了,而我躺的木板太寬,他們折騰了半天,仍然抬不進去。我爹在黑夜里開始罵人。我爹總是在自己無能為力的時候,就一反常態地胡亂罵人。他邊罵邊從我姐手里接過床板的一頭,他明知道自己在枉費心機,可仍然企圖把木板側著從門口擠進去。最后,他自己放棄了。他大概知道如果他一意孤行,到頭來抬進門的就不再是我,而只是一塊木板。我爹氣喘吁吁地把我放到地上,黑暗中在脖子上摸出煙鍋,給自己點了一鍋煙。
對面的三叔手里提了一把镢頭走過來。他揮起镢頭向我家門框上挖去,我爹沒有攔住,門嘩啦一聲倒在地上。
現在好了。三叔說,好賴回村兒了,總不能把尸體停放在大街上吧!
面包車在門外啟動了,街道上亮起一道白光。
我剛被從木板上挪到炕上,我姐突然大喊一聲向門外跑去。片刻之后,她又從門外回來了。我心里替她捏了一把汗,不過還好,她再次回來時,懷里緊緊抱著那只人造革提兜。老天爺!如果她把那只提兜拉到面包車上,我相信我爹立即會把她塞進深井里去。
三
我姑姑說,得二萬六。
我姑姑是站在院子里說這話的。院子的一面墻上搭建了一個廚房,廚房三面都是空的,我爹和我姐坐在廚房里。我姑姑進門后沒有多余的話,她只是說,得二萬六。
這是彩禮錢。
討老婆雖然不是買東西,但在鄉下和買東西差不多,得花彩禮錢。
我爹說,貴了。
我姑姑說,哥呀,你以為這是什么年代了!不要說小放掙了錢,有人從煤礦上回來,掙的錢能塞滿一棺材,也不一定能找到一門親。這家人是姑娘在城里待過,姑娘的意思要找個在城里待過的,這么著才輪到咱們小放了。
我姐坐在廚房里拉風箱。我姐說,二萬六就二萬六,姑,你早點給定了吧,再晚怕來不及了。
我姐又說,爹,不是賠了五萬嗎,我們要錢做啥,只要能把小放的親事撮合成了,花五萬都行。
我聽了這話,鼓足勁在屋子里向外喊,我說,姐,你就別窮大方了,一共才五萬塊錢,要給爹看病,給家里蓋房子,還得給我外甥留點學費——我外甥不是明年該上高中了嗎?不能為我的事把錢給折騰光了!
外面一時間靜下來。風箱聲也停下了。
我姐從門口走進來,站在土炕邊上。她的眼睛又紅又腫,像兩顆成熟的櫻桃。她說,小放,你好好在炕上躺著,別的事你不用管。姐說了給你相親就給你相親,你只管躺著就行了。
我說,你告訴姑姑,二萬六太多了,不能花那么多錢。
我姐說,我說過你不要管了,這些事你就不要再管了。
我姐用手抹著眼睛,轉過身向門外走了。
我姐回到廚房以后,外面說話的聲音就小了許多,我再怎么努力也聽不清楚了。
我姐從外面抱了一大堆柴火,要把土炕給我燒暖和一些。我說,姐,我一點也感覺不到冷,我是不是快要死了?你們不要給我忙活相親了吧,我大概活不久了。我姐說,別說傻話了,你沒有死。我仍然有點擔心,我怕萬一家里給我訂了親,我卻死了,浪費了錢不說,不是白白把人家姑娘也給耽擱了。我說,姐,要不相親的事再緩一緩吧。
我姐不再接我的話,貪心地把一堆柴火全塞進炕洞里,用一把扇子使勁地扇。
我姑姑是過了一天又來到我家的。她仍舊站在院子里,對我爹和我姐說,還是得二萬六。
我姑姑的話像一塊石頭掉到井里,很久沒有回音。
末了,我爹才說,滿和真是個狗日的!一點都不能少了?
我姑姑說,一分一文都不能少。滿和說了,再少這門親就不給小放說了,后邊很多人排著隊,都是從煤窯上回來的,錢多的是……
我姐忽然哭了。她說,都怪我,怪我在城里不會辦事,給小放要的賠償款太少了。
我爹嘆了口氣,邊咳嗽邊在地上磕煙鍋。他說,怪你啥?人家給賠了五萬不少了,我是罵滿和是個狗日的。
我姑姑說,滿和說了,今天再不給話,這事他就不管了。
他們在院子里說話,我躺在屋內的炕上,頭發一根一根在頭頂豎起來。我想我姑姑是不是老糊涂了,還有我爹,我姐。滿和是什么人他們不是不知道,他是個扎花圈的,是個一天到晚坐在公路邊上用破花圈伺候死人的。我又沒有死,怎么能輪到他來伺候。相親是多喜慶的事兒,他們找了滿和來說媒,還能喜慶起來嗎?一群糊涂蟲!不知道他們是怎么想的!
他們的做法搞得我情緒十分敗壞。我這天一整天都閉著眼躺在土炕上,和誰也不說話。我爹進來了幾次,我沒有搭理。后來我姐也進來了,我同樣沒搭理。我就那么氣鼓鼓地躺著。我姐在屋子里站了一會兒,走過來,用手摸我的臉。她越摸我臉上的眼淚越多,鼻子里也酸溜溜的,喉嚨那兒有東西開始竄動。我姐身子一軟伏在了炕邊上。
我睜開眼,對我姐說,姐,你們不要浪費錢了,叫滿和給我用紙糊個媳婦就好了。
我姐立時變得眼淚汪汪。她說,小放,你不要生氣,姐知道你為什么生氣,可滿和不是個壞人,再說他現在不做花圈了,改給人說媒了,你生什么氣呢。
我聽了這話,噗嗤一下笑了。我說,那你怎么不早說?我以為我已經死了,所以你們才找滿和要給我糊個紙媳婦呢!
我姐也破涕為笑,輕柔地摩挲著我的臉。她說,姐怎么會騙你,不會是紙糊的媳婦,一定是真媳婦。
我長長出了一口氣,相信我姐的話了。我心里一高興,就想和我姐說點什么。我說,難怪爹罵滿和,我小的時候,滿和做花圈買不起做花的彩紙,叫我們到野地上去給他采紅的黃的野花,野花采來了,他用一根鐵絲把它們串起來綁到花圈上。他答應采一個下午給發一顆糖的,可最后他欺騙我們,只發給半顆……
我姐抿著嘴,笑著笑著眼淚又出來了。她說,姑姑和滿和說妥了,明天就給你相親,等你的病徹底好了,你就可以結婚了。
四
滿和帶著一群人到我家的時候,衛衛正在我家炕邊上坐著。
衛衛陰沉著臉,好半天沒有說話。他一會兒把頭低下,一會兒又抬起來,半張著嘴巴,愣愣地看著窗外。窗外正在下雪,大片大片的雪花從門口撲進來,給進門的地方鋪了耀眼的一層白。
我對衛衛說,衛衛,我今天就要相親了。
我說完這話馬上就后悔了。我看見衛衛的腦袋擰了過來,眼睛通紅,鼻子一聳一聳的。我的話刺激了他,勾起了他連綿不絕的回憶。他的眼睛里空空蕩蕩的,像是等著把過去和張小紅在一起的日子給裝進去。我覺得挺對不起他。當初是衛衛帶著我進城的,我們的目的一樣,都是想在城里奮斗娶老婆,眼下我要相親了,他的老婆又在哪里呢?衛衛的頭深深地埋了下去,很長時間一句話也沒有,就那么在炕邊上坐著。我知道他又在思念張小紅了。
衛衛比我早一年到城里,我到城里后,他和張小紅已經搞上了對象。張小紅在一家發廊上班,衛衛平時在工地上干活,一到周末,就去發廊對面的柳樹底下等她。發廊的生意很好,總是要忙活到后半夜才下班。衛衛挺喜歡張小紅,他說,我們以后死也要一起死在城里。我當面問過他,我說大家的戶口都在鄉下,你死在城了,哪里有你的墳地?衛衛很倔強,他說,有,只要我們肯掙錢就會有。張小紅因此認為他是有雄心大志的,所以不管我后來怎么心懷鬼胎地捕捉她的目光,她對我一點感覺也沒有,一心愛著衛衛。我后來也不想喜歡她了,因為我聽別人說了,發廊里是不干凈的,什么亂七八糟的事都有。
果然,張小紅就是在發廊里出事的。一個男人拿著一把殺豬刀子沖進發廊,在里面見人就捅,一共捅死了兩個,張小紅算一個。她和那個男人一點關系都沒有,她被那個男人捅死,很多人都說是冤枉。但也有人說,男人為什么不捅別人,偏偏就捅她?男人后來逃走了,這些事誰也弄不清楚了。據說張小紅家里人為這事也在城里鬧得厲害,不安葬人,把她的尸體一直放在醫院的冰柜里。張小紅挺可憐的,她出事后我一點也不嫌棄她了,只是感覺她挺可憐的。
衛衛就是那時候開始變了的,變成現在這副呆頭呆腦的樣子。
我看著衛衛的樣子很為他擔心,他不是又要回工地上了嗎,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我那天本來在架板上站得好好的,都怪天空中的一只鳥,猛地飛過來撞到我眼睛上,我眼前一黑,從樓上摔了下來。我說,衛衛,你回城后得給老板建議,叫他給工地的四周圍上網子,那樣鳥就不會隨便亂飛了,要不然以后再撞到你的眼睛上怎么辦?衛衛回過頭看著我,眼圈一下子紅了。我說的話你一定要記住,我說,以前城建局的人就那樣給老板說過,可老板就是不聽,你回去再給老板說說。
衛衛剛給我點了點頭,滿和帶著一幫人從門外闖進來了。
滿和穿著一件大紅袍子,上面落了不少雪,手里拿著一個用花花綠綠的紙糊成的棍子,一進門就吹胡子瞪眼,在屋子里胡亂舞弄起來。
我聽見空氣里響起一陣虛假的沙沙聲,不久就發現滿和的紅袍子也是用紙糊的。雪花把紙袍子洇濕了,露出猩猩點點的紅,像涂抹了雞血。一群人圍著滿和看,我姐和我姑姑也在其中。滿和把紅袍子上的雞血甩到墻上,地上,還有我發燙的臉上。
這是一種很新穎的相親儀式的開始,我以前從沒見過。
滿和舞弄畢,我姐撲過來爬在炕邊,我姑姑也撲過來,拉著我姐的一條胳膊。我姑姑說,別哭了,別哭了,新人進門,相親要開始了。人群一閃,門口亮了一下,幾個人從外面擁進來,像一陣風,夾帶著屋外的寒氣,身上披著銀色的雪片。這些人把一個漆黑的柜子放到屋內的地上。我眼睛一花,末了才看明白是一口棺材。
屋外響起了怪誕的風聲,卷著雪花從窗縫里灌進來。
我覺得這一切簡直太荒唐了,我明明是要相親,他們抬棺材干什么?難道是我死了,這是來裝運我的尸體的?我看見衛衛和我一樣目瞪口呆。他一定嚇壞了,身體緊貼在一面墻上。幾個人把棺材在地上擺弄好,棺材就穩穩當當和我并成一排。
我爹站在屋檐下哭,哭聲攪著風聲,聽起來飄忽而蒼涼。滿和對著棺材又開始手舞足蹈,口里念念有詞。我爹邊哭邊在屋檐下擤鼻涕。我姐顯得比我姑姑還要衰老,在我姑姑的攙扶下,艱難地走過棺材和土炕之間的過道,又來到我跟前。我姐伸出手,冰涼的手放到我熱騰騰的臉上。
我姐說,小放,現在你可以安心地走了。你在醫院里就該走了,可就是閉不上眼睛。現在好了,給你找的媳婦叫張小紅,是張氏堡的姑娘,模樣又好又賢惠,有她陪著你,你到那邊再也不會孤單了。
衛衛猛地哭出了聲,從人群里往外擠,擠倒了兩三個人,瘋了似的向門外跑去了。
我姐把手放在我眼上,撫了一下,又撫了一下,想把我的眼皮給合上。
我本來有許多憤懣的話要說出來,但不知怎么搞的,我心里清清楚楚,卻什么也說不出口。我想把衛衛叫住,我得告訴他,雖然我有時候也夢見過張小紅,可從來沒想過要娶她。我再怎么說也不能搶了他的人。世界很安靜。我一個人叫了許多聲,衛衛仍然沒有回來。我看見張小紅委屈地躺在我身邊的棺材里,她一定很傷心。她從來都不認為我這輩子會有什么作為,她是看好衛衛的。可是衛衛逃跑了,她現在再怎么難受,也只好和我一起毫無生氣地躺著了。
外面仍在下雪,大片的雪花不時從門口拋進來。
我聽見了雪花從天上下墜的聲音,聽見了樹枝、圍墻還有冬天干硬的地面被雪壓迫的軋軋聲,也聽見了我自己微弱的呼吸聲。我在合上眼睛的那一刻,最后看了一眼張小紅。我忽然很擔心,她一點都不像鄉下的姑娘,我以后該怎么伺候她才好?還有,如果有一天衛衛來質問我,我又該怎么給他解釋這一切!
責任編輯/董曉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