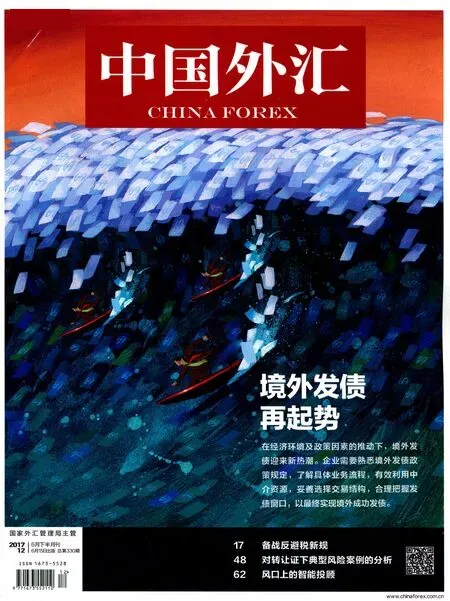“烏藍色”的人民幣?
文/程實 編輯/張美思
“烏藍色”的人民幣?
文/程實 編輯/張美思
現實的世界是多彩的,人民幣也是雙向波動的。沒有只是烏藍色的人間,更沒有只貶不升或只升不貶的貨幣。
霍小樹有一首民謠,名字叫《烏藍色》。慵懶的吉他、突然的鼓點,伴著充滿“烏藍色”的歌詞,把一種說不出道不明的魔性味道唱得格外醇厚。魔性的聲音,往往聽上去沒什么邏輯可言,但又隱隱會有種特別哲學的高深感。
“烏藍色的天空,飄著烏藍色的樹葉;烏藍色的衣服,掛在烏藍色的墻上;烏藍色的鞋子,踏在烏藍色的土地;烏藍色的心情,流入烏藍色的河。”“烏藍色的玻璃,嵌在烏藍色的窗;烏藍色的燈兒,發出的烏藍色的光;烏藍色的花朵,結出烏藍色的種子;烏藍色的火苗,燒著烏藍色的憂傷。”“烏藍色的雨傘下有烏藍色的背影;烏藍色的姑娘是否有烏藍色的愛情?烏藍色的書包藏著烏藍色的信,烏藍色的信紙上寫著烏藍色的詩。”這三組歌詞,每組四句,每句有兩個“烏藍色”,用無厘頭的排比,把一種抽象的寫實感唱得入耳入心。
其實我并不知道烏藍色代表怎樣的一種情感,但我覺著這并不重要。于霍小樹而言,是烏藍色;而于你于我則可能是藏青色、草綠色、鮮紅色: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魔性顏色。問題是,哪來那么多烏藍色?對此,霍小樹的回答是,“我喜歡用烏藍色的畫筆,涂滿一塵不染的白紙,在我悲傷難過的時候,給我烏藍色的快樂;我習慣用烏藍色的眼睛去看花花世界,在我腦海空白的時候給我烏藍色的幻想”。原來,用了這么多烏藍色,是因為要用烏藍色的眼睛看世界,從而看到一個烏藍色的世界。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就是這樣真實地生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
作為一個投行經濟學家,我無法真正在生活與市場間劃出清晰的界限。《烏藍色》的歌聲,使我不禁想到,對于很多人來說,人民幣也是烏藍色的。這種烏藍色在他們眼里、心里,就是人民幣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貶值。自2015年“8·11”匯改之后,很多人對人民幣抱有堅定的貶值預期。他們或不惜代價地將人民幣換成美元,或不計成本地建立沽空人民幣的頭寸。在這些人眼里,烏藍色的人民幣不僅是預期,還意味著利益。人民幣貶值會給他們帶來真金白銀的快樂,而且他們還真心期待有更多的人同樣擁有烏藍色的信仰。
夾雜著說不清、道不明的成見和利益,人民幣貶值預期很自然異化成心魔,以至于在最夸張的時段(如2016年年初和2016年第四季度),幾乎成為一種帶有魔性的聲音。在各種路演、論壇、采訪中,我對這種魔性聲音有著切身感受。記得在2016年年末一次年度經濟展望論壇的會議間歇,一大群記者圍上來問人民幣的匯率問題。當我說“不會破七”時,所有人都流露出一副不可思議的表情,甚至有個年輕記者驚訝得把話筒都掉到了地上。
然而,世界終究不總是烏藍色的。2017年以來,人民幣就走出了另一種顏色。先是年初,就在很多人迫不及待到銀行排隊購匯的時候,人民幣兌美元不僅沒有破七,反而走出一波強勢升值。這給了那些急于用滿購匯額度的人迎頭一擊。而在端午后,就在市場還在猜測6月美聯儲加息會不會帶來又一輪美元升值和人民幣貶值的時候,人民幣對美元卻突然大幅走強:離岸市場人民幣一馬當先,在岸市場人民幣緊跟不讓,而方向不是向上“破7.0”,而是向下“破6.8”。
然而,即便如此,還是有很多人不愿放棄烏藍色的信仰。他們陰陽怪氣地將升值歸因于某些短期外因,甚至連陰謀論都用在了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在我看來,烏藍色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面對現實”是每一個成熟的人應該具備的基本素養。
現實是,世界不會存在于幻想之中。決定人民幣價格波動中樞的,是其內在價值而非市場預期。這個世界是多彩的,人民幣也是雙向波動的。沒有只是烏藍色的人間,更沒有只貶不升或只升不貶的貨幣。根據我的研究,人民幣的內在價值構成了一道底線,且這道底線始終是穩固的。這不僅是央行努力的目標,更是市場長期運行的基準。
無論是《烏藍色》,還是人民幣大貶值的論調,魔性的聲音總會讓人念念不忘。但對于這些,娛樂一番尚可,當真則有失偏頗。
作者系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