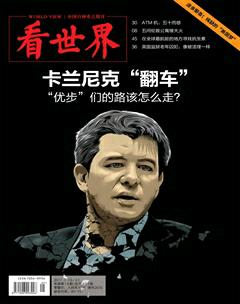她讓無數蒙古病患走好人生最后一程
桃寶
15年前的蒙古,人們從未聽說過“臨終關懷”這種說法。如今全球臨終關懷醫療國家的排名中,蒙古榜上有名。對此敖登托雅·達瓦蘇榮醫生功不可沒,正是她不懈的努力,才促進了蒙古醫療系統對于姑息治療的完善,大大地減少了病患去世前的痛苦。
當17歲的達瓦蘇榮醫生還遠在俄羅斯列寧格勒學習兒科醫學時,家里傳來了父親死于肝癌的噩耗。
“我沒有機會照顧我的父親,甚至連見他最后一面的機會也沒有,” 她回憶道,“當我回到蒙古, 我的妹妹告訴我,父親在去世前一直被病痛糾纏,苦不堪言。”
幾年后,達瓦蘇榮成為了一名執業醫生。當時,她與罹患肝癌的婆婆住在一起,但仍只能眼睜睜看著婆婆飽受折磨地離世。
“我照顧她,我喂她吃飯,我幫她洗澡,我幫她更衣,但我無法緩解她的痛苦,因為我不知道該怎么做。”她自責道。

達瓦蘇榮醫生(右)和她的患者
沒聽過臨終關懷
當時,在蒙古唯一可用于臨終病人的止痛藥只能緩解肌肉疼痛或頭痛,無法改善因腫瘤壓迫上腹部神經導致的持續性疼痛,也無法緩解持續的惡心和嘔吐等癥狀。
“對此我覺得萬分羞愧,我不是一名好醫生,因為我并不知道從何幫起。" 她說。
除了自身經歷,達瓦蘇榮在工作也目睹了患有白血病的孩子們因飽受病痛折磨而沉默寡言,神情失落。還有一位年輕的母親因不堪胃癌病痛而多次要求結束生命。
“還有許多病患痛苦地死在家里,飽受極大的身心之苦,”她回憶道,“許多時候病人親屬會買很多中藥或其他昂貴的藥物,希望能對緩解病痛有所幫助,但都希望落空。”
在其他國家,姑息治療或臨終關懷的醫療體系已相對完善。但在蒙古,游牧民族生活條件惡劣的這種生存狀態已持續千年,對姑息治療或臨終關懷的說法可謂一無所知。
肝癌致死率全球第一
2000年,一趟瑞典行讓達瓦蘇榮醫生找到了對癥下藥的方法,她參加了歐洲臨終關懷醫療照護協會舉辦的會議,受此啟發,她知道了該如何幫助蒙古的病人同胞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達瓦蘇榮醫生說,“在2000年去斯德哥爾摩前,我從來沒有聽過‘臨終關懷療護這個說法。”
回國后,達瓦蘇榮醫生積極地游說蒙古衛生部引進臨終關懷照護,但當局充耳不聞,甚至問她:“妳為什么想把錢花在瀕死的人身上?我們對活著的病人都沒有足夠的經費。”
蒙古的肝癌致死率全球第一,比全球平均肝癌致死率還高了六倍,而且死亡人數持續攀升。而這背后的罪魁禍首就是病毒感染,不是乙型肝炎就是丙型肝炎,通常經由血液或體液感染,目前有超過四分之一的蒙古人受到至少其中一種病毒的長期感染。
這是一種慢性疾病。病毒會使肝細胞基因突變,最終讓某些病患身上長出腫瘤,等癥狀出現時早就為時已晚。
達瓦蘇榮醫生認為,人們在臨終前有權利過得有尊嚴,“好好地死去”,這是有必要的。
當時,醫院一旦看病人救不活就會讓病人回家,借此降低醫院的致死率。于是,達瓦蘇榮醫生走訪瀕死病患的家,一一用攝影機拍下他們臨終時所經受的痛苦折磨。
許多返家后飽受病痛纏身的病人,最后是靠自殺獲得解脫。達瓦蘇榮醫生說:“許多人會要求:‘拜托殺了我吧。他們寧愿一死也不要再受苦。在拍完后,我晚上回家看到影片會邊看邊哭,太多人在生死邊緣掙扎了。”
根據肝癌統計數據,達瓦蘇榮醫生知道大多數蒙古家庭都有可能遭受這種痛苦。
在達瓦蘇榮醫生的不斷奔走和充滿感情的游說下,她終于在2002年獲準建立國家臨終關懷照護項目,旨在支持瀕死病患和親屬。

達瓦蘇榮醫生與一位病人家屬擁抱
15年后的進步
15年后的今天,蒙古每間省立醫院都有提供臨終關懷醫療照護,首都烏蘭巴托的九個區立醫院也有。
不只如此,達瓦蘇榮醫生另一個主要貢獻是讓國內的醫療系統取得嗎啡變得更容易。
在她幫助修改有關使用嗎啡緩解疼痛的法規前,許多官員認為, 使用嗎啡更容易助長病人成癮。
“但現在藥房可以根據每位癌癥病患的需要,免費提供他們嗎啡,直到他們過世”,她說道。
除了讓病人易于取得緩解疼痛的嗎啡,達瓦蘇榮醫生也訓練上千名提供臨終關懷醫療和心理支持的醫生,因為對于臨終病人來說,這這兩方面都是至關重要的。
“精神關懷有時比嗎啡更重要。” 她說道,“精神關懷可以緩解病痛,幫助病患減輕焦慮、恐懼、失眠等心理問題。心態平和地接受死亡后對病情會有很大的幫助。”
在蒙古國家癌癥醫院的姑息治療病房,達瓦蘇榮醫生正在與一名病患聊天,兩人的對話也從一開始的例行看診變得越來越親密。
達瓦蘇榮醫生解釋道,這名有著灰白頭發的病患是一名林業工人,有五個孩子。“他感到死亡要來了。不過在孩子的面前,他會故作堅強,要家人別擔心。”
“但我跟他說,現在是時候想想該跟孩子說什么,要怎么準備后事了,因為是時候了,知道真相總比懷抱虛假的希望要好。他微笑著同意了。”
接著,達瓦蘇榮醫生告知了病患女兒有關其父親的病情,在談話過程中,她漸漸收起微笑,隨后淚水奪眶而出,臉頰顫抖。
“我告訴她,她的父親正在死去,”達瓦蘇榮醫生說道,“她說,希望我能再救救他。我就跟她解釋說,這是癌癥末期,不是用藥猛轟的時候,而是需要用愛包圍他的時候。她回答說,謝謝你,我現在了解了。”
“這對我來說仍非常困難,有時候我會陪著我的病人一起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