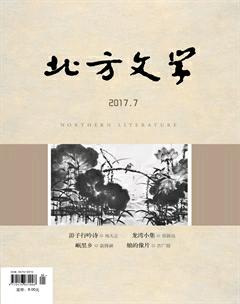《老人與海》張愛玲譯本中的“創造性叛逆”分析
張嬌
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要:由于語言和文化差異等原因,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不可避免。本文從這一角度出發,對《老人與海》張愛玲的譯本進行分析,發現其“創造性叛逆”主要體現在個性化翻譯、誤譯和增譯三個方面。這不僅為譯本增添了特色,也體現了張愛玲獨特的翻譯風格。
關鍵詞:創造性叛逆;《老人與海》;張愛玲
《老人與海》是海明威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該作圍繞一位古巴老漁夫與一條大馬林魚在海上斗智斗勇的故事而展開敘述,展現了老漁夫堅毅頑強的“硬漢”精神。1954年張愛玲將《老人與海》翻譯成中文,她的譯本被認為是該部小說的首個中文譯本。經過文本分析,筆者發現“創造性叛逆”是張愛玲譯本中一個鮮明的特點,體現了張愛玲對該作品的理解和其獨特的翻譯風格。
一、創造性叛逆
埃斯卡皮最早提出“創造性叛逆”這一術語,指出“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的叛逆”。在國內,真正開始系統地研究“創造性叛逆”的是謝天振。他在《譯介學導論》(2007)一書中,肯定了“創造性叛逆”存在的必然性,并將翻譯的“創造性叛逆”定義為譯介學研究的理論基礎。隨后董明在《翻譯:創造性叛逆》(2006)一書中表示支持并提倡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劉小剛在《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與跨文化交際》(2014)一書中指出文化差異是“創造性叛逆”在跨文化交際中形成的主要原因。
近年來,關于翻譯的“創造性叛逆”的期刊文章也層出不窮。孫建昌(2002)認為成功的“創造性叛逆”應當是一種增值翻譯,譯本要超越原文本;許鈞(2003)強調了譯者在翻譯的“創造性叛逆”中所處的中心地位;胡東平(2010)論證了“創造性叛逆”與忠實的關系,認為“創造性叛逆”其實是一種深度的忠實,它是表層上的偽叛逆,深層次的真忠實。然而,關于《老人與海》中譯本的“創造性叛逆”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本文將探究《老人與海》張愛玲譯本中的“創造性叛逆”是如何體
現的。
二、張愛玲譯本《老人與海》中的“創造性叛逆”
(一)個性化翻譯
個性化翻譯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遵循的自己的原則和策略。正如董明(2006)所說“不管譯者主觀上多么想忠實于原作,他的翻譯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他個人的色彩。”
例1: “He always thought of the sea as la mar......spoke of her as el mar which is masculine.”[8](25)
張譯:他腦海里的海永遠是“海娘子”……他們稱她為“海郎”,那是男性的。[9](18)
在例1中,“la mar”和“el mar”都是西班牙語。“海洋(mar)”既可作陰性名詞,也可作陽性名詞。其中“la”表示陰性,“el”表示陽性。張譯用“娘子”和“郎”這樣的中國古代男女稱謂來對應原文中的陰性和陽性,不僅符合漢語的習慣表達,而且使中國的讀者更加容易理解文中的外來詞匯的含義。
(二)誤譯
女性主義譯者有時會對原文中帶有性別歧視的語句進行有意識的誤譯,從而體現自己的女性主義思想。
例2: “Let him think I am more man than I am and I will be so.”[8](60)
張譯:“讓他想著我是個勝過我的人,我也就會超過我自己。”[9](40)
“man”的名詞詞性主要有兩個意思,一個是“男人,男子漢”,一個是泛指“人,人類”。這句話是要展示老人勇于戰勝困難的“硬漢”精神,所以譯成“男子漢”應該更貼切一些。而張愛玲將“man”譯為“人”而不是“男子漢”,意在消除翻譯語言中的性別歧視現象,提高女性的地位。
(三)增譯
增譯即通過增加和補充的方法,使譯文更加準確的表達出原文所包含的意義。
例3:“He rested sitting on the unstepped mast and sail......”[8](41)
張譯:“桅桿沒有豎起來,帆也沒有張掛起來,他就坐在那桅桿和帆上休息著……”[9](28)
這句話是老人與大魚經過一番搏斗之后精疲力竭的場景。張譯將原文中的“unstepped mast and sail”四個英文單詞譯成了15個中文漢字,這并不是張愛玲用詞不夠精煉,而是因為這句話不僅僅是在描寫“取下來的桅桿和帆”,而是通過這些景物來突出老人的疲憊。張譯用“…沒有…沒有”句式并不顯啰嗦,反而將老人的疲憊感在字里行間呈獻給讀者,因此這種增譯將原文要表達的含義更準確地表達了出來。
三、結論
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是由語言和文化間的巨大差異引起的。為了使譯本更容易被譯入語讀者所接受,“創造性叛逆”在文學作品中是不可避免的。本文從“創造性叛逆”這一視角分析了《老人與海》張愛玲的譯本,發現譯者運用了個性化翻譯、誤譯和增譯的方法對作品翻譯作出“創造性叛逆”,使作品為更多的中國讀者所接受。本文不僅為《老人與海》張愛玲的譯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視角,更是以張譯本為媒介肯定了“創造性叛逆”在文學翻
譯中產生的積極影響。
參考文獻:
[1]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M].王美華,于沛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
[2]謝天振.譯介學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3]董明.翻譯:創造性叛逆[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4]劉小剛.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與跨文化交際[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
[5]胡東平,魏娟.翻譯“創造性叛逆”:一種深度忠實[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2010,11(1).
[6]孫建昌.論翻譯的創造性叛逆[J].山東外語教學,2002(6).
[7]許鈞.“創造性叛逆”和翻譯主體性的確立[J].中國翻譯,2003,24(1).
[8]Ernest Hemingway.The Old Man and The Sea [M].Beijing:Knowledge Publishing House,2016.
[9]歐涅斯特·海明威.老人與海[M].張愛玲譯.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