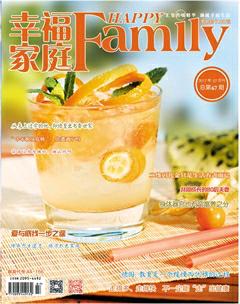究竟誰才是缺愛的一代
濱海時報編輯部
愛對于中國人來說一直不是件輕松的事情,羞于表達(dá)愛使得人們的情感難以得到有效的溝通。一些時候,恨反倒比愛更能交代清楚親情或愛情關(guān)系。在社交媒體上,“愛”已經(jīng)成為一種非常泛濫的符號,但在現(xiàn)實生活里,愛依然處于一個缺失或者空洞的狀態(tài),這讓人頗覺無奈。
想到這個話題,是因為國學(xué)大師季羨林遺產(chǎn)糾紛案最近再次開庭了。自2009年季羨林辭世后,與其遺產(chǎn)有關(guān)的糾紛一直沒有停歇。2016年5月,季羨林之子季承將存放了季羨林物品的北京大學(xué)告上法庭,要求北京大學(xué)返還其父親的遺物,一審判決駁回了季承的全部訴訟請求。從辭世到現(xiàn)在整整過去了8年,一次次被推到輿論風(fēng)口的季羨林,還在承受著世人復(fù)雜的眼光。
公眾心目中有兩個季羨林。一個是那位《懷念母親》《夾竹桃》《永久的悔》等諸多文章被收進(jìn)教科書、一生翻譯與創(chuàng)作出版了諸多煌煌大著的大師季羨林;一個是那位隨著遺產(chǎn)爭奪案一起不斷被曝光家庭生活的平凡老人季羨林。隱私一次次見諸于媒體,不會磨損季先生一生學(xué)術(shù)成就的輝煌,但卻一度讓這位真正走上大師殿堂的文化巨擘,暴露了家庭生活中脆弱的一面,這恐怕是所有尊重他、愛戴他的人們,所不愿意看到的。
季承曾出版名為《我和父親季羨林》的圖書,將父親形容為“一個人生失敗者,一個孤獨、寂寞、吝嗇、無情的文人”,書中還寫到諸多類似于這樣的細(xì)節(jié):“記得父親在摸了我的頭之后,立刻去水缸里淘了一瓢水去沖手,使我感到很新奇。但他從來沒有親過我或拉過我的手。”父親的冷漠讓一個兒子的積怨在成年之后爆發(fā),父子兩人曾13年沒有見面,這種人倫悲劇的發(fā)生,其實無外乎一個字——“愛”。
打官司很容易為季承贏得同情,一方面有“子承父業(yè)”這個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公眾的補(bǔ)償心理也會傾向于季承的利益。缺乏父愛的季承,表面上看是在索要父親的財物,但暫且放下法律條框、人倫情理,單從情感深處去分析,這何嘗不是一個兒子在向父親討要欠缺的父愛?在民間,類似的父子恩怨比比皆是。
這些年一直有一個熱門的詞叫“缺愛的一代”,60后、70后們紛紛自稱是“缺愛的一代”,甚至一直被認(rèn)為在溺愛中長大的80后、90后也認(rèn)為自己“缺愛”……其實向前追溯,生于1911年的10后季羨林那一代,才真正是“缺愛”的源頭。季羨林生于亂世,父親在他12歲時去世,給他所留下的印象是“荒唐離奇”。他與母親早早分開,青年時代顛簸流離,娶妻時娶了一個自己不愛的女子,現(xiàn)實生活缺乏真實情感的灌注,才是造就季羨林所謂“對親情冷漠”的真正原因。
對親情冷漠,是一個時代留給知識分子的集體烙印。作家老鬼在《母親楊沫》中還原了一個真實的楊沫,她會在父親打罵時添油加醋,說老鬼的《血色黃昏》是大毒草,給北大寫信檢舉自己的兒子。類似的事例,在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群體中并非個例,許多人忙于處理時代傷痕,無暇顧及親人感受,或者寄情于創(chuàng)作,把所有激情都用于學(xué)術(shù)鉆研,親情無形中變得如同炭火,觸碰一下也會被灼傷。
有一個細(xì)節(jié)值得關(guān)注,在女兒、嬸母、妻子去世之后,季羨林都沒有去參加葬禮,但卻分別寫了散文作為悼念,也許只有在文章里表達(dá)清感才是安全的,不用直接去揭開陳年傷疤,可以用文字去修飾殘破人生的裂痕。
作為局外人,關(guān)注季羨林先生家庭的私人生活,應(yīng)有悲憫之心,他們個人或者家庭的命運,在放大或縮小之后,都會投射到萬千家庭那里,只是普通家庭的隱傷,就算暴露后也會很快自我愈合于無聲當(dāng)中,而季先生作為極富知名度的公眾人物,不得不承受輿論的點評,卻是無法躲掉的命運。正是因為如此,大家才更應(yīng)該杜絕八卦之心,把季先生放在時代命運的大背景下去打量,理解、體諒這位文化老人的悲傷與無奈。
走出季先生的家庭故事,再跨越20世紀(jì)60后、70后、80后這3代人,在20世紀(jì)90后,21世紀(jì)00后、10后這3代年輕人當(dāng)中,應(yīng)當(dāng)是不缺愛的,這么說是因為,他們的父輩已經(jīng)逐漸懂得了如何教育孩子去愛,上面幾代人花了幾十年的時間,已經(jīng)逐漸學(xué)會了如何科學(xué)地面對以及解決愛的難題,況且,當(dāng)下的青少年群體,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了解了更多的事物,擁有更開闊的視野,遠(yuǎn)比我們想象要獨立得多——而獨立,恰恰是懂得愛的前提。
有句話這樣說,“培養(yǎng)一個貴族需要3代人時間”,從不懂愛、缺愛到擁有愛、給予愛,何嘗不需要花費3代人的時間?值得欣慰的是,缺愛的年代一去不回,愛也剝離掉了附加在它身上的諸多條件,在這個時代處處綻放。
(摘自《濱海時報》2017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