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曉亮:東窗
納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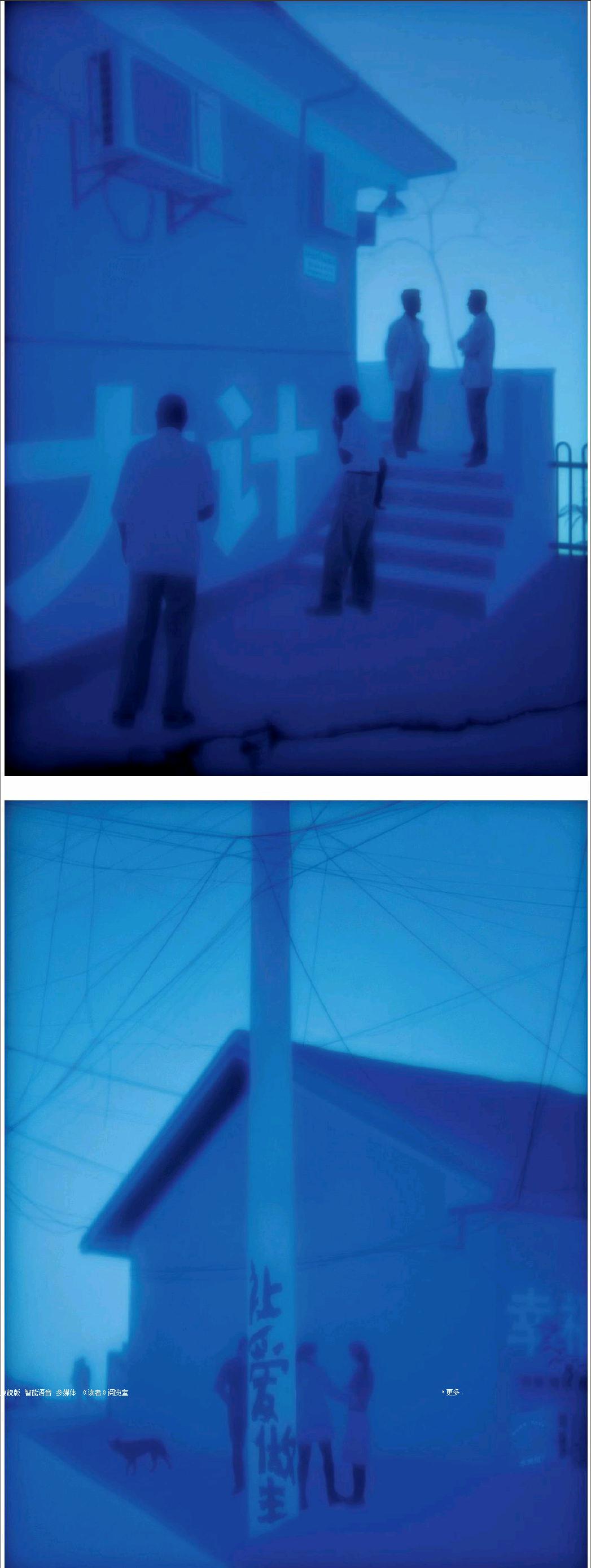
在創(chuàng)作完以故鄉(xiāng)、童年為靈感的《春,人間景》《夏,委婉》后,1985年出生于湖南湘西吉首的攝影師黃曉亮用了一兩年時(shí)間畫畫、拍照片,“不停積累心里的某種感覺”。
“積累到一定程度,那種感覺就爆發(fā)出來。”今年黃曉亮推出了一組新作,并在上海、北京舉辦了展覽“東窗”。新創(chuàng)作是關(guān)于不斷變遷、擴(kuò)張的城市環(huán)境景觀。他拍攝了城鎮(zhèn)中各種有意思的空間構(gòu)造,比如拆遷中的環(huán)境、正在建設(shè)的樓群、老街密集的房子、街道上空布滿的電線……這些錯(cuò)亂的結(jié)構(gòu)除了形式上的美感外,更讓黃曉亮心動(dòng)的,則是其中關(guān)于人的生活痕跡。
照片大多在黃曉亮毫不刻意的“潛意識”控制下完成。而這種漫不經(jīng)心的狀態(tài)也是他很喜歡的,“所謂不尋常往往就是在平常之中。人情世故和生活瑣事都是生活最真實(shí)的一面,藝術(shù)更是需要接地氣,營養(yǎng)就來自人間世界,而非想象。煙云俗世,常常讓我感到驚喜,甚至有點(diǎn)沉迷在這當(dāng)中。”
作品自述:
這是一個(gè)關(guān)于日常的創(chuàng)作,“日常”既不是很有激情也不是很消極的事。
仿佛我游離在生活的里外,以一個(gè)旁觀者的身份在觀看生活的世界,同時(shí)我又生活在這個(gè)世界當(dāng)中。最奇妙的是,我作為一個(gè)觀眾在看這個(gè)如同戲劇的世界,隨著時(shí)間的推演,故事情節(jié)在不斷延伸的同時(shí),我也是故事參演者。
所謂人生如戲,這個(gè)世界每天都在創(chuàng)造歷史,盡管我們很渺小,但也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關(guān)于歷史,我們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但歷史文化卻是日常生活的積累和沉淀。在信息爆炸的時(shí)代中,我們常常會感到生活的重復(fù)和乏味,因此我們都在期待驚喜的不斷出現(xiàn),重復(fù)的力量致使我們從麻木到產(chǎn)生期待,從而救贖自己。
以旁觀者和參與者的雙重身份去理解日常生活,“驚喜”就在其中,人們只是因?yàn)樘^于期待更新的可能出現(xiàn),而忽視了它的存在,然而它卻一直在那。
從“春”“夏”系列結(jié)束到拍這組作品,這期間你在做些什么?
黃曉亮:新舊作品間隔差不多有三年的時(shí)間。第一年我?guī)缀跬V沽藙?chuàng)作,事實(shí)上是有點(diǎn)沒勁兒,不想創(chuàng)作。大部分時(shí)間在忙一些生活瑣事,這期間我的第一個(gè)孩子出生了,所以大部分時(shí)間用在家庭生活中。不過這種狀態(tài)讓我更貼近生活,心態(tài)更穩(wěn)定。時(shí)間稍長便能夠發(fā)現(xiàn)日常的不尋常之趣。
你拍攝這組作品用了多久?創(chuàng)作的初衷是什么?
黃曉亮:不能用“拍攝”來談?wù)搫?chuàng)作。如果只是拍,我覺得一天之內(nèi)可能完成很多。如果從創(chuàng)作角度講,得花上兩三年的時(shí)間吧。創(chuàng)作是一個(gè)漫長且繁復(fù)的過程,“拍攝”這個(gè)行為對我來說只是一瞬間,算是最后一道“制作工序”。我們可以來討論攝影,但和怎么拍沒有具體而直接的聯(lián)系。
攝影只是一個(gè)媒介,而每一次創(chuàng)作或多或少都有一個(gè)觸發(fā)點(diǎn),致使自己開始新的創(chuàng)作過程。因?yàn)槊恳淮蝿?chuàng)作都不是為了完成某一個(gè)具體項(xiàng)目,所以初衷并不會有那么清晰且單一。這次新作的觸發(fā)點(diǎn)來自于我長久沉浸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我作為旁觀者的視角所看到的日常是什么樣子,特別之處在哪里,有趣部分又是什么。再反過來想,自己不僅僅是旁觀生活的人,也是生活的參與者,這又是很有趣的一面。
你之前的作品仿佛有著很濃的鄉(xiāng)土情緒,這組作品是這一情緒的延伸嗎?
黃曉亮:我覺得新作品沒有這種延伸,更多是日常之中的東西,來自于我所生活和工作過的不同地方。我并不會沉迷在自己的回憶之中,那將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似乎未來也就不了了之。
這組作品中的拍攝對象是在哪里捕捉到的?你在那些環(huán)境中發(fā)現(xiàn)了什么?
黃曉亮:很久以來,我已經(jīng)習(xí)慣了用手機(jī)拍照片,它成了我很重要而且很方便的拍攝工具。因?yàn)樗谋銛y和使用率高,可以更方便快捷地把當(dāng)時(shí)在某個(gè)地方所看到的第一感受記錄下來,在這方面我覺得手機(jī)超過了所有的相機(jī)。在創(chuàng)作這些作品的時(shí)候,我拍過大量的手機(jī)照片,正是因?yàn)檫@樣的高效,讓手機(jī)攝影者很多情況下處于無意識狀態(tài)拍攝。不過,無意識狀態(tài)實(shí)際上是在潛意識的掌控之下進(jìn)行的。
當(dāng)拍下大量的手機(jī)照片后,我發(fā)覺所拍過的照片都有一種不確定性,似乎有什么事情在發(fā)生,或者已經(jīng)發(fā)生了,或者是即將要發(fā)生。拍攝對象在我的生活中隨機(jī)出現(xiàn),隨機(jī)拍下。選擇標(biāo)準(zhǔn)往往是符合自己當(dāng)時(shí)生活狀態(tài)里的情緒,或者處事態(tài)度。
這種無意識的狀態(tài),我覺得特別像是一種觀看的方式,也會讓人引起反思——自己所看到的世界為什么偏偏是這些局部?別人看到的可能又是別的東西。因此,不同的關(guān)注點(diǎn)致使照片成為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也體現(xiàn)個(gè)人在某個(gè)時(shí)期的思考和態(tài)度。
圖片統(tǒng)一附著上濃郁的深藍(lán)色,為什么這么處理?
黃曉亮:拍攝的目的不是某張照片,只是為了記錄當(dāng)時(shí)的場景。為了讓我在以后的觀看中能喚起當(dāng)時(shí)的感受,我需要把當(dāng)時(shí)的第一感受呈現(xiàn)出來,所以你會看到畫面做了一些特殊處理。比較巧的是,新展覽呈現(xiàn)的一些作品都用到了大量的藍(lán)色,因?yàn)樗鼈兊呐臄z時(shí)間可能是傍晚,夜幕降臨,又或者是黎明時(shí)分……
畫面中有很多帶有意味的文字,你選擇的原因是什么?
黃曉亮:文字能夠喚起一種時(shí)代感。過去的某種標(biāo)語,又在當(dāng)下的情景中出現(xiàn),我覺得挺有意思,能產(chǎn)生一些細(xì)微的戲劇性。對于攝影這種單一的媒介來說,它的藝術(shù)生命力來自于豐富的戲劇性。
標(biāo)題“東窗”有什么意味?
黃曉亮:原本想用“東窗事發(fā)”來作為展覽的名字,后來覺得這個(gè)成語的指向太明確,而我要的是一種不確定的感覺。所以后來選擇用“東窗”,它更有詩意和想象力,也貼近生活。
有人說你的作品有朦朧的畫意,你同意這種評價(jià)嗎?
黃曉亮:也許從視覺上大家可能這樣看,但我從不認(rèn)為“朦朧的畫意”是我所追求的東西。影像帶給人的藝術(shù)力量不是近似繪畫,而是它自身的光影造就了魅力,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媒介,繪畫不可能替代攝影,更不會超越。攝影也不可能達(dá)到繪畫的力量,哪怕企圖達(dá)到都是妄想。兩種平行的媒介,帶給人的感受是不一樣的。攝影一直被誤解成是繪畫的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但實(shí)際上它們的創(chuàng)作過程和呈現(xiàn)方式都很不同。
你對自己之后的創(chuàng)作有什么計(jì)劃或設(shè)計(jì)?
黃曉亮:設(shè)計(jì)會存在于展覽之中,做展覽需要設(shè)計(jì)一個(gè)呈現(xiàn)的方式,展示自己創(chuàng)作的想法和藝術(shù)感受。通常來講,不是特定的藝術(shù)項(xiàng)目合作,我不大可能去設(shè)計(jì)或者是規(guī)劃一系列的創(chuàng)作,因?yàn)檫@也許不符合我的內(nèi)在需要。創(chuàng)作的最好狀態(tài)就是每天都有所思、所做。至于是否勤奮,做多少量,和藝術(shù)的好壞沒有關(guān)系。
我相信藝術(shù)家不是靠勤奮和量的積累就一定會成功。所以我還是會盡量維持我的生活節(jié)奏、我需要的狀態(tài),繼續(xù)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往往是未知的,創(chuàng)作者內(nèi)在生發(fā)出某種想要?jiǎng)?chuàng)作的動(dòng)力,進(jìn)而展開一系列的行動(dòng)。在這個(gè)過程中,創(chuàng)作者會產(chǎn)生很多新的想法和新認(rèn)識,創(chuàng)作的結(jié)果往往會偏離起初的想法。我覺得這是好事,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這種未知感才讓人有強(qiáng)烈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