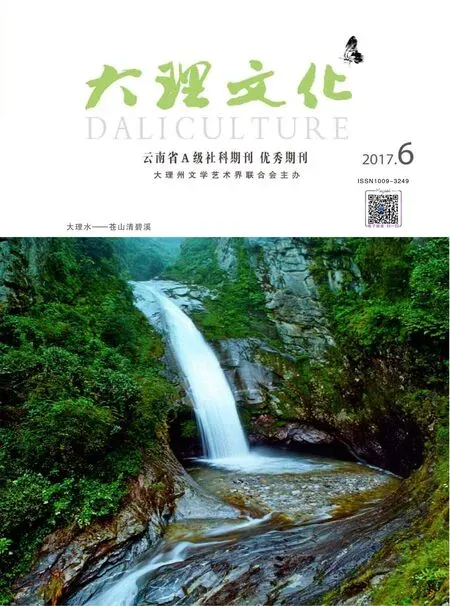心靈的歌者張樹先
●李樹華文圖
心靈的歌者張樹先
●李樹華文圖
2017年3月,在鶴慶奇峰村“梨花節”期間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采訪了年近70歲的鶴慶縣白族省級民間音樂傳承人張樹先,而讓我想不到的是,張樹先竟然還是一個盲人。
與我近幾年采訪的許多傳承人不同的是,張樹先從未上過學,但對音樂卻無師自通,不僅對三弦、二胡、笛子、木葉的演奏技藝得心應手,還會制作好多種民間樂器,不能不說是一個奇人,一位用心靈在歌唱的歌者。
鶴慶“田埂調”的傳遞者
“我最初走上民間音樂這一條路是從彈唱我們地方的‘田埂調’開始的。”一見面,張樹先便開門見山地告訴我。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種民俗孕育一種文化。自古以來,大理鶴慶人在田間勞作之余,會在田埂上一邊彈著三弦一邊唱著調子釋放心中的歡樂,久而久之,這種活動被人們形象地稱之為“田埂調”。在大理州的鶴慶縣,彈唱“田埂調”的風俗十分盛行。除了田間彈唱,節日、廟會、甚至在趕集的時候,人們也喜歡彈唱。甚至當地青年男女談情說愛時,也通過即興對歌彈唱來展現自己的才能和智慧,達到互相了解,互相試探,表達愛慕的目的。
“李老師,說起來有些好笑,我在門口削一段竹子,鑿上幾個眼就做成了‘笛子’,用蛇皮梨花木馬尾,搗騰幾天就做成了‘二胡’。”張樹先對我說。
“哦,你真是一個就地取材的民間音樂家……”我感嘆地回答。
“呵呵呵……”聽了我的稱贊,張樹先謙虛地笑了起來。
張樹先告訴我,他父親也是一個民間音樂高手,二胡拉得遠近聞名。
“有一次,我父親竟用十斗大米去換了一把鄰村人制作的三弦,現在,那個制作三弦的師傅早已作古,但那把三弦還一直在我家里收藏著,說起來已經有80多年的歷史了,那把換來的三弦也是我家里收藏的三弦中‘年紀’最大的一把。”張樹先和我說這話時,滿臉自豪。
“在那個年代,用十斗大米去換一把三弦,真是太不可思議了,不過,這也說明你父親是一個把音樂當作生命的人……”我感嘆地回答。
“把音樂當作生命,這一點我承認。不要說我父親,其實,李老師,我現在也可以說是一個把音樂當作生命的人。”張樹先坦然地對我說。
“是的。一個把自己喜歡的事情當作生命的人,一定會成為一個有作為的人的。”這是我的真心話。
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和同齡人相比,張樹先的人生可謂更加坎坷。張樹先4歲那年冬天,染上了天花,為了躲避地震,半夜和家人搬到院子里露天而睡,結果一場高燒使他不幸雙目失明,這讓他的生活一瞬間墜入了無底的深淵,但生活能力極強的張樹先并沒有向命運低頭,在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之后,張樹先竟然學會了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技能,從洗衣做飯、洗菜切菜,到使用家用電器……這些都難不倒他。
張樹先若有所思地對我說:“我有一個好的條件,就是我父親張金照是村里的洞經‘班主’,所以在我失明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就是在洞經音樂和民歌的對唱聲中長大的。經過我父親手把手的指點,再加上我的刻苦,幾年下來,我很快就掌握了三弦、笛子、胡琴、嗩吶、樹葉等一些民間樂器的演奏技巧,還能將我們鶴慶一帶廣為流傳的經典對歌、民歌曲調、洞經樂譜熟記在心……”
“哦,你剛才說的這些,對于一個樂手和歌手來說實在太重要了。”我打斷張樹先的話,深有感觸地說。
說來有趣,張樹先和他的妻子楊薇花,就是在彈唱田埂調的過程中認識后才結為夫婦的,可見田埂調在當地人們的社會生活中顯得多么重要。
田埂調的彈唱方式有自彈自唱,也有自彈自唱者與別人對歌,或一人專彈三弦,他人歌唱等多種形式,既可以采用坐姿彈唱,也可將三弦掛在胸前,站立在人群中彈唱。在眾多的鶴慶田埂調彈唱藝人中,雙目失明的盲藝人張樹先最終成為一位杰出的田埂調彈唱代表人物,并把鶴慶一帶流傳的經典對歌、民歌曲調、洞經樂譜等民間傳統曲調,加以創造性地發展,終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彈奏方法。
“我在前人彈奏的基礎上,對龍頭小三弦的彈撥方式和揉弦技法進行了改進,并注入了自己對音樂的獨特理解。”張樹先一邊說,一邊隨手拿起身邊心愛的龍頭小三弦,一瞬間,一股音樂就隨著他彈奏的手指流淌出來,婉轉動聽的樂聲跌宕起伏,如泣如訴,讓人無可躲閃。
在張樹先彈奏的美妙的音樂聲中,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話,“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的時候必然為你開了另一扇窗。”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失去了一些,就一定會在另一個地方找回一些。人生,往往不會一帆風順,會遇到許多坎坷。但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用積極的態度面對,不放棄,就有希望走出陰霾。與其在關著的門前流連忘返,不如去開著的窗外尋找屬于自己的天空。
我聽說張樹先對音樂的記憶力很強,從小就跟隨村子里的長輩擺弄各種樂器,剛成年時,他就基本掌握了竹笛、嗩吶、小三弦,還有樹葉的吹奏,作為一個盲人樂手,張樹先眼前的世界雖然一片漆黑,可是他心中的音樂天地卻是五彩繽紛的。
眾所周知,作為一種少數民族地區廣為流傳的曲藝形式,大本曲在大理地區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而在大理地區流傳的彎頭三弦則是大本曲傳唱時唯一的伴奏樂器。這種特制的彎頭三弦與漢族地區的三弦相比,形狀相似卻又不盡相同。它的弦鼓比漢族地區流行的三弦略小,但其鼓腔卻更空,鼓壁較薄。另外,蟒皮也蒙得比較適中,沒有北方三弦的硬,因此發音就更為寬厚濃郁,余音也比較長,還略帶一種“嗡嗡”的聲響,這樣一來,在獨唱伴奏時,這種三弦對人聲就更具有粘合力,能夠使人聲和三弦聲渾然融為一體,音場也顯得更為寬敞,所以非常適合在露天和空曠的場院里進行表演,受到人們的喜愛。可以說,三弦已經成為大理州內各個縣市白族群眾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伙伴。

張樹先在彈奏白族龍頭三弦
張樹先對我說:“李老師,我們鶴慶的龍頭三弦在制作材料、方法、音響效果和演奏技巧等方面不僅和大理洱海一帶的不盡相同,就是和劍川、賓川,還有祥云禾甸白族聚居地區的白族龍頭三弦相比也不盡相同……”
“哦,這是什么原因呢?”我不解地問他。
“這個原因么,是因為我們鶴慶的三弦,要選用那種硬度適中、具有良好音響性能的紅木作為制作材料,還要在琴頭上雕上龍頭作裝飾,琴桿有效弦長度要有60公分左右長,要用細銅條作山口,采用3厘米厚的黃銅箔作琴桿的指板面,琴鼓為八角鼓形,用整料鑿空而成,鼓厚為7公分,一面蒙蟒皮,背面開音窗,張金屬弦線,選用子彈殼作琴碼,用竹片彈奏,這也是我們本地人對三弦音色和音量特殊追求的一種體現。”
“哦,原來是這樣啊。我現在才知道大理州內的白族三弦還會有這些區別。說實話,我過去一種以為三弦雖然有大小之分,但都是一樣的。”
張樹先繼續對我說:“我承認自己是從學唱我們鶴慶的‘田埂調’開始走上藝術道路的。記得有一次到一所音樂學院表演,我從后臺一走出來,臺下黑壓壓的觀眾一看到我的甸北小三弦,又是個農民殘疾人,能夠來到這么高檔的音樂學院表演,都熱情地給我鼓掌,現在想起來,那種掌聲好像還在耳邊回響著,真是讓人回味無窮。我當時就在心里想,如果我不是一個盲人,能夠看得見那些鼓掌的人,那真是太幸福了。不過,李老師,我雖然看不見那些熱情的觀眾,但是我能夠感受得到觀眾那種對我發自內心的熱情,那是對我的一種尊重,也是對我們殘疾人的一種尊重,為此,我感到自己非常的自豪。”
“我能夠理解你當時的心情。其實,許多殘疾人需要的只是一種尊重,尊重就是對殘疾人最大的關愛。老張先生,你那次表演了什么曲調,你現在還記得嗎?”
“我當然記得,而且我這輩子都忘記不了。我那次在舞臺上表演了 《鶴慶田埂調》《梅花調》《山鄉情歌》,最后的一個曲目還是我媳婦楊薇花和我合作表演的。”說這話時,張樹先顯得有些興奮。
“哦,是這樣……”
通過交流,我了解到,在前人彈奏藝術的基礎上,張樹先根據自己對音樂的獨特理解,對鶴慶的白族龍頭小三弦彈撥方式和揉弦技法進行了鉆研和改進,因此他演奏的三弦音樂能夠跌宕起伏而又婉轉細膩,樂聲似斷非斷而如泣如訴,具有很強的感染力。
以洱海為中心的大理白族自治州,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區,自古以來,當地就流行對調子,彈三弦,吹嗩吶,表演吹吹腔戲,彈演洞經,演唱大本曲等活動。大凡生產勞動,節日慶典,婚嫁宴請,宗教祭祀,娛樂歌舞,年輕人談情說愛等民俗活動都少不了彈弦唱曲,可以說,通過歲月的變遷,彈弦唱曲已經與大理地區白族群眾的社會生活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成為他們社會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清以來,在大理一帶就盛傳著古老的白族曲藝“大本曲”,而在鶴慶一帶則流傳著另一種古老的白族曲藝“田埂調”,這兩種說唱在民間廣泛地流傳,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三弦作為這兩種說唱藝術唯一的伴奏樂器,對于曲種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傳承聯系作用,因此,也可以說,如果沒有三弦就不可能形成“大本曲”和“田埂調”的音樂體系。正因為如此,白族的三弦音樂藝術也顯現出了極大的豐富性和多元性,與我國內地的三弦藝術和其他民族的三弦藝術相比,有其特殊性及其鮮明的風格,也有濃郁的民族特點。無論從民族音樂學,音樂文化學,音樂形態學,音樂美學等相關學科的角度去審視,白族三弦藝術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科研價值。
白族龍頭小三弦音樂師
大理州鶴慶縣的白族人口主要集中在辛屯鎮、草海鎮、金墩鄉、六合鄉、松桂鎮等幾個鄉鎮。辛屯鎮位于鶴慶縣最北端,是鶴慶的北大門,也是大理州的北大門。交通便利,大麗公路橫貫境內,距鶴慶縣城12公里,漾弓江由北至南順流而下。地形地貌獨特,大小龍潭星羅棋布素有 “龍潭之鄉”的美稱。1639年,徐霞客到鶴慶時,曾到過香米龍潭(小龍潭)和仕莊龍潭,并對兩個龍潭進行了描述。辛屯是一個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的地方,以張樹先為代表的甸北田埂調,以洪子勝洞為代表的洞經古樂在民間一直傳唱不衰。
張樹先之所以能夠成為具有一定影響和知名度的民間藝人,就在于他在年復一年的彈唱生涯中,不斷繼承大理鶴慶甸北等地三弦藝術的傳統,從而練就了一手自彈自唱的好功夫。2002年,他被云南省文化廳授予 “云南省民族民間音樂師”,成為大理鶴慶白族地區唯一的白族小三弦音樂師。更為可喜的是,在2005年云南省第五屆殘疾人文藝匯演和大理州賽區文藝匯演中,張樹先還代表鶴慶縣分別獲得了第2名和第1名的好成績,被選送到云南省殘疾人文藝匯演代表團參加全國殘疾人文藝匯演。
“為什么鶴慶,還有大理、劍川、祥云禾甸等地的白族三弦幾乎都用龍頭來作為裝飾呢?”我向張樹先提出了這個在我心中一直存在的疑問。
“這個嘛,呵呵呵……”張樹先笑了起來,接著說道:“相傳古時候,我們白族把龍作為圖騰來崇拜,把龍看作一種吉祥尊貴的象征,視龍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所以龍的故事和傳說很多,這樣,以龍頭作為三弦的裝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龍頭三弦也就因此而得名了。”
“哦,原來是這樣。”
我隨手拿起一把鶴慶白族龍頭三弦,仔細觀看,只見手里的龍頭三弦由共鳴箱、琴頭、琴桿、弦軸、琴馬和三條琴弦等部分組成,而琴體尺寸竟然有1米多長,共鳴箱為扁六角形,琴框用六塊核桃木拼接膠粘而成,上下開有插入琴桿的方孔,琴框前面的振動膜面用一張厚棉紙蒙著,網絡用絲線編織,我知道這是用清糯米湯,將網絡裱糊在近10層的薄棉紙之間,制成的有筋絡的紙膜,一般要經過自然陰干后,才能將它膠于琴箱前口,這樣的振動膜不會受氣候影響而變得松軟塌陷,動起來既有革面的柔韌,又有板面的硬實效果。琴鼓的后背面是音窗,琴箱角面寬20厘米左右,厚近10厘米,琴頭用質地細膩的桃木制成,自弦槽處向后呈半圓形彎曲。龍頭上飾著彩繪,琴框上雕刻著花紋圖案,既是一件可供彈奏的民間樂器,又是一件可供觀賞、收藏的精美工藝品。
張樹先告訴我,因形制、制作材料、弦線、琴碼、演奏方法、演奏場合及流行區域的不同,白族龍頭三弦也有幾個種類,比如共鳴箱,就有扁六角形、扁八角形、扁圓形。琴箱也有大有小,有的由六塊木板拼接膠粘而成、有的有八塊。材料也有紅木、梨木,還有核桃木。
至于表演形式,龍頭三弦多為一人自彈自唱,或者對唱,也可采用坐姿或立姿表演。在表演時,用右手食指套一個錐形的牛角尖來彈奏。龍頭三弦的定弦,里弦、中弦、外弦為四度至五度,外弦、里弦為八度關系,有時也定為五度,不過,還要根據樂曲的需要酌情而定,而具體的音高則要由歌者自己來定。
“老張先生,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就是大三弦、中音三弦和小三弦在音量上到底有什么區別?”我問張樹先。
他想了想,回答:“這個嘛,當然有區別了。大三弦音量較大,音色渾厚而深沉,中音三弦音量適中,音色柔和而圓潤,小三弦音量纖細而明亮,清脆而甜美,富有穿透力。”
“那么在演奏方法上又有什么技巧呢?”我繼續問他。
“演奏方法么,一般分左右手。也就是說,左手多用食指和中指觸弦,有滑音、揉音、打音、和音等奏法,常使用大幅度‘滑揉’技巧。右手有彈,挑、滾輪和掃弦等技法。”張樹先詳細向我介紹道。
龍頭三弦在大理各地流傳很廣泛,在鶴慶,它還是白族青年男女唱山歌、對調子不可缺少的伴奏樂器,尤其是青年男女交往,談情說愛,通過即興對歌彈唱,能夠充分地展現自己的才能和智慧,達到互相了解的目的。每逢歌會,人們穿著節日盛裝,紛紛前往赴會。屆時,滿山滿嶺三弦聲,到處可見彈三弦的人們,男女老少,高手云集,賽歌打擂,場面恢宏壯觀。
通過幾十年的努力,張樹先的演奏技藝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終于成為眾多三弦手中的佼佼者。他不僅熟練掌握了許多自彈自唱的“田埂調”,還擅長即興演唱,具有獨到的演唱風格,他能夠演唱大量的傳統“田埂調”和當地的白族民歌小調,在國家級比賽和其他賽事中曾經榮獲多種獎項,成為大理州具有一定影響和知名度的藝人。
多年來,習慣于走南闖北的張樹先,不僅走出甸北,走出鶴慶,走出大理,還走到了北京音樂學院,還曾被日本三弦大師相邀到日本切磋技藝,盡管因種種原因未能成行,但精湛的三弦彈奏技藝已然征服了日本三弦高手。
在我眼里,張樹先儼然就是一個身懷絕技的奇人。他雖然雙目失明,但卻能彈奏多種樂器,即便是一片樹葉,一小塊塑料布,一張糖紙,到他嘴邊,隨手一吹,就能吹出來扣人心弦的調子。更為神奇的是,他能自制笛子和三弦,一段小小的竹管,隨手掏幾個小孔,放嘴邊一吹,就能音發七律。生活中,張樹先能生火燒水,切菜做飯,甚至還能接燈泡,利索熟練的動作讓人覺得他手上仿佛長著眼睛。
2008年11月,首屆國際三弦音樂周在北京舉行,來自中國、日本等世界各地的三弦音樂大師齊聚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大廳,向數萬名中外觀眾表演自己的拿手絕活。在那些大腕級的三弦音樂大師中,唯一的農民盲人張樹先一上臺就引來了全場觀眾如潮般的掌聲。很難想象,作為一個盲人的張樹先,竟然能夠憑著精湛的三弦彈唱技藝,把鶴慶甸北的田埂調唱到首屆國際三弦音樂周上,讓世人領略到了鶴慶田埂調的無窮魅力。
上世紀70年代以來,張樹先就經常活躍在各種文藝演出和比賽中,他在民族民間音樂方面的突出成就得到了省內外音樂專家較高的評價。1984年,他獲得云南省盲人音樂錄音評比器樂一等獎;1989年獲云南省首屆民歌獨唱、少數民族樂器獨奏電視大獎賽民間業余組二等獎;1997年,他的三弦獨奏《香港回歸頌》和《鶴慶田埂調》獲云南省第三屆殘疾人文藝匯演三等獎,三弦彈唱《鶴慶田埂調》獲得大理州殘疾人藝術匯演二等獎。2002年,他被評為“云南省民族民間音樂師”,成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和白族小三弦的民間音樂師。2005年,他在云南省第五屆殘疾人文藝匯演和大理州賽區文藝匯演中分別獲得第一名和第二名,獲得第六屆全國殘疾人藝術匯演廣東賽區器樂類節目優秀獎;2006年被評為“大理州民間藝術大師”。
2012年11月29日,當紅搖滾歌手汪峰到龍泉廟拜訪張樹先,新搖滾和田埂調在鶴慶碰撞時,“中國音樂在大理”欄目以“當田埂調邂逅新搖滾”為題,詳細報道了這一次專訪。這一天,張樹先招來了汪峰,汪峰又招來了活躍在大理古城復興路和人民路的那些音樂愛好者。確切地說,是旅游衛視“我是探路者欄目”的4集專題片《探尋大理音樂的十字路口》,讓張樹先的甸北田埂調邂逅了汪峰的傷痕搖滾。于是,在人們眼前很快就出現了這樣的場面:一頭鶴發的民間老藝人張樹先,用一片樹葉吹響了當紅搖滾歌手汪峰的 《怒放的生命》,本是充滿生命韌性的一片普通老葉,卻在很多葉子相繼凋零的冬天,任由張樹先熟稔地吹出一個個原本激蕩的音符,那些音符經過樹葉的傳遞,竟然充滿了憂傷……而來自波蘭的吉他手,在英國琴師的伴奏下,唱起了家鄉的民歌,大理南詔古樂協會的大本曲傳承人楊老師用笛聲相和,吹的則是《金花花喲遍地開》,悠揚的笛聲與來自波蘭的民歌融為了一體。
“我雖然看不見,但是我聽說,那天龍泉寺頭頂藍天如洗,我能夠想象得出來,在我們的音樂聲中,一望無際的桑葉正在暖洋洋的冬陽照曬下使勁生長。”張樹先若有所思地對我說。
“是的。這就是音樂的魅力,也是生命的魅力。”我對張樹先獨特的想象力充滿敬意。
“那天下午,結束了龍泉寺的交流后,汪峰挽著我的手,經過細窄的村間黃土小路,到了我的家里。就在我家堂屋前,我們兩個音樂人,一老一少,進行著難得的交流。我再次吹起了田埂調,彈起了龍頭小三弦,讓我的心聲飛揚起來。”直到現在,張樹先還對那天的情景記憶猶新。
張樹先告訴我,有一年,上海音樂學院幾位教授到張樹先家,準確無誤地記下《田埂調》的譜子,但彈出來的卻不是張樹先的那種味道,無奈只得遺憾返滬。也許除了張樹先本人,其他人雖然能夠記錄下一個個音符,卻無法記錄張樹先彈奏時那種瞬息萬變的情感,還有張樹先音符之外的那種坎坷人生,這便是情感的力量使然。
我由此想到,如果一定要說汪峰和張樹先兩個人之間有什么相同之處的話,那就是蒼涼的聲音,只有聲音里面才可能有這種相同的東西。盡管兩個人的兩種蒼涼一個來自城市,一個來自鄉村,一個來自自由自在的云端,一個來自面朝黃土的云貴高原,一個更多的是城市和現代人生活的迷惘,另一個更多的是生活的最底層和命運的灰色,然而卻可以殊途同歸,這也許就是音樂天生的“無國界力量”吧?
張樹先突然對我說:“李老師,外地人不知道,其實我們鶴慶分為甸南和甸北,人們常說‘甸南人斯文,甸北人會做生意’。只要走進甸南人家的小院,再清貧的人家,都會收拾得井井有條,三五盆花、一兩塊鐵畫銀鉤的扁額,隱透著一股文氣書香。而甸北院子就有點財大氣粗的感覺,電腦冰箱一應俱全。甸北人還有一大特色,很會過日子,一句話,浪漫。我記得在 20年前的月亮街的晚上,到處都是一束束的手電筒光,人們紛紛從家里出來唱田埂調,可以說,田埂調成了甸北姑娘小伙傳遞愛情的東西。那時,人們男男女女、三五成群地圍住,在龍頭三弦的聲音中且歌且舞……”
“哦,我能夠想象到那種場景,真的會很浪漫的。”我說的是真心話。
“是啊,我們義朋村是一個典型的甸北村子,在辛屯鎮,龍泉廟是村里的本主廟,我就是甸北義朋村的歌手,我們村子里的洞經古樂隊逢年過節就在那個廟子里演奏,因此,也可以說,我的音樂人生就是從義朋村開始,向甸北、鶴慶、大理、云南和北京一步一步蔓延的。”張樹先似乎有感而發。
“我聽說你的三弦和調子,被你們鶴慶那些不太識字的婦女形容成‘割心割肝’的調子,有這回事情嗎?”我接著問道。
“有這回事……呵呵。這很可能是因為我的田埂調有一種蒼涼、悲傷的緣故吧。”張樹先肯定地回答我。
“那為什么你能夠彈奏出那種蒼涼、悲傷的曲調來呢?”我問道。
“這個嘛,除了感情的投入以外,主要是我用來彈奏的龍頭小三弦與眾不同。就是它的弦板和弦線都用金屬制作,這讓它和大理蒼洱地區以及劍川的大三弦、尼龍弦線相比,細膩中更顯堅韌而富于質感,能夠緊貼人心。”張樹先向我解釋說。
別具一格的木葉吹奏
在鶴慶這個大理州的高原水鄉,人們總能聽到一曲曲扣人心弦的甸北田埂調,作為鶴慶甸北一帶知名度很高的盲人樂手和歌手的張樹先,在龍頭三弦的陪伴下面,且行且歌,從一個普通農民盲人,成長為省級民族民間音樂師,他的人生充滿了傳奇色彩。
1948年12月,張樹先出生于鶴慶縣辛屯鎮連義村委會義朋自然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張樹先至今還清楚地記得,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最后印象,就是縣城鐘鼓樓上面毛主席高高舉起手臂的那一幅大大的宣傳畫。此后,他的世界就陷入了無邊的黑夜……
2008年11月11日,這是一個讓張樹先永生難忘的日子。這天,他有幸受到中央音樂學院的邀請,趕赴北京參加“首屆國際三弦音樂周”活動。活動期間,張樹先在中央音樂學院演奏廳分4個部分用如泣如訴的龍頭三弦和歷盡滄桑的歌聲展示了鶴慶甸北田埂調的風韻,其中,《山鄉情歌》《鎮康小姑娘》以及鶴慶甸北田埂調聯奏贏得了滿堂喝彩;他和愛人的情歌對唱,更是把鶴慶甸北田埂調的韻味體現得淋漓盡致,贏得了眾多三弦專家及聽眾的高度贊譽。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三弦專業委員會會長談龍建先生高興地把張樹先的龍頭小三弦稱為云南鶴慶的“國寶”。
張樹先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除了龍頭小三弦,他的木葉吹奏技藝也是別具一格,遠近聞名。
木葉是大自然賦予人類的天然樂器,深受我國許多少數民族人民的喜愛。樹葉雖小,音色優美,音樂動人,獨具風采。吹木葉在白族中流傳極為普遍,聚居于云南大理的白族人民,常用竹葉、柳葉、栗葉和梨葉吹奏。在云貴高原的山間小路上,人們經常可以聽到一陣陣高亢、悠揚的樂聲,這是聰穎的少數民族,利用一種葉面光滑、具有韌性的橢圓形樹葉,通過各種吹奏技巧而發出的清脆、明亮的樂音,就像是多才多藝的山歌手在歡樂地歌唱。
許多民間藝人吹奏木葉的技藝都高超,吹奏方法也多種多樣,而張樹先卻能夠做到一個人同時操梆笛和木葉兩件樂器吹奏,忽而笛聲嘹亮,忽而葉聲悠揚,他經常吹奏的《梅花調》,恰到好處地表現了那種青年男女歡樂對歌的情景,受到人們的廣泛喜愛。近年來,大理州白劇團的趙懷禮,通過反復實踐,將軟硬適中的塑料薄膜剪成適當大小的葉片形狀用于吹奏,發音靈敏,強弱層次分明,音域達三個八度,演奏技巧有單吐、雙吐、花舌、滑音、顫音等,可吹奏出難度較高的樂曲,收到了十分理想的效果,他的大膽嘗試,使木葉音樂藝術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李老師,我現在就給你來上一段我經常吹奏的《梅花調》吧。”話音一落,張樹先便把一片葉子放到了嘴邊,很快,一股悠揚的木葉樂聲就從他的嘴邊飄灑開來。想不到小小的一片樹葉,竟能夠與人聲媲美,發出別樣的山鄉風味。
“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在張樹先的木葉聲中,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九歌》中這一句膾炙人口的詩句。自從屈原吟唱出這句動人的詩句后,木葉鮮明的形象,就影響了歷代的詩人們,許多為人傳誦的詩篇正是從屈原的詩句得到了啟發,“木葉”也成了詩人們筆下讓人鐘愛的形象。
“李老師,你知道木葉吹奏藝術的起源嗎?”張樹先突然問我。
“我也是最近才了解。”我回答。
“那你可以說一說么。”張樹先似乎想試探我。
我接著說道:“當然可以。木葉來自于大自然,是一種最簡單、最古老的樂器。在原始社會的狩獵時代,人們用木葉模擬聲音來捕獵禽鳥,后來就逐漸轉化為以聲代樂、以音伴唱的樂器了。幾千年來,吹木葉盛傳不衰,但見于史籍卻較晚。到了唐代,吹木葉更為盛行,木葉在皇室宮廷樂隊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被正式用于‘十部樂’的‘清樂’中。值得一提的是,樂隊在演奏《景云河清歌》和《霓裳羽衣曲》等重要樂曲時,也一定要有吹葉。這時的木葉,已身價倍增,受到隆重禮遇。”我接著對張樹先說:“至于木葉的樹種選擇,我可就要請教你了。”
張樹先爽快地說道:“我們互相交流吧。吹木葉,一定要選擇優良的樹種,一般要采用桔樹、柚樹、楊樹、楓樹、冬青樹等沒有毒性的樹葉,葉片的結構要勻稱,正、背兩面都要平整光滑,以柔韌適度、不老不嫩的葉子為最好。太嫩的葉子軟,不易發音,而老的葉子又硬,音色不柔美。另外,葉子的大小對吹奏也有很大關系,過大或太小的葉子既不便吹奏,發音也不集中。一般使用的葉片,以葉長 5厘米、中間葉寬2厘米左右的比較適宜。因為葉子不耐吹用,一片葉子一般吹幾次就會發軟破爛,不能再用了,所以吹奏時,吹奏者肯定需有多片樹葉備用。”

張樹先夫婦合作表演《鶴慶田埂調》
“張老先生,你還記得有一次我打電話問你‘為什么要把吹樹葉叫做吹木葉呢’的事情么?”
“當然記得。”
“我在電話中告訴你說‘木’就是‘樹’,‘木葉’也就是‘樹葉’。
“是啊。這個我知道。不過,我還是覺得奇怪,問題在于我們在古代的詩歌中為什么很少看見用‘樹葉’呢? ”。
“是啊,為什么?”
“我想可能是因為‘木’不但讓我們容易想起樹干,而且還會帶來了‘木’所暗示的顏色性。樹的顏色,就樹干而論,一般是褐綠色,與葉是比較相近的。至于‘木’呢,我就說不定,可能是透著黃色,而且在觸覺上也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濕潤的,比如我們平常所見的門栓、棍子、桅桿,盡管‘木’是作為‘樹’這樣一個特殊概念出現的,而‘木’潛在的暗示,卻依然左右著這個形象,于是‘木葉’就自然而然有了落葉的微黃與干燥之感,它帶來了整個疏朗的清秋的氣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落下的絕不是碧綠柔軟的葉子,而是窸窣飄零透些微黃的葉子,我們仿佛從詩中聽見了離人的嘆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這就是‘木葉’的形象之所以如此生動的緣故。‘木葉’之與‘樹葉’,不過是一字之差,‘木’與‘樹’在概念上原是相去無幾的,然而到了藝術形象的領域,這里的差別就幾乎是一字千里了。”
“哦,李老師,想不到你還知道這么多的東西。”
“沒什么,就像你說的,我們互相交流么。不過,對于木葉吹奏的技巧我就一竅不通了,還要向你多請教。”
“不客氣。根據我的經驗,在演奏時,要先把葉片上粘附的灰塵輕拭干凈,將葉片正面橫貼于嘴唇,用右手或左手食指、中指稍微岔開,輕輕貼住葉片背面,拇指反向托住葉片下緣,使食指、中指按住的葉片上緣稍稍高于下唇。運用適當氣流吹動葉邊,使葉片振動發音。木葉就是簧片,口腔猶如共鳴箱,雙手也可幫助起共鳴作用,通過嘴勁、口形、舌尖的控制,手指繃緊或放松葉片等各種技巧,改變葉片的振動頻率,可吹奏出高低、強弱不同的音響,音域達十一、二度。若要使它發出不同的音色,就需要運用不同的吹奏方式,通常是按住葉子的下半片,用氣吹其上半片,還有一手按住葉片,另一手輕輕拍打,像吹口琴那樣,發出來的音響既有共鳴,又能產生波浪音。而技巧比較高的是將葉片夾于唇間,不用手扶就能吹奏,像吹竹笛那樣,隨著曲調的高低,送出急緩有別的氣流,吹奏出優美動聽的旋律。李老師,那些技巧特別高超的演奏者更使人嘆服,能夠一口同時吹響兩片木葉,他們即使不用手指幫助,同樣也可以奏出動人的曲調。另外,木葉吹奏高低音時,需要運用不同的氣量,唇部也隨之忽松忽緊,控制氣流的送出。吹木葉是不能隨意斷氣、斷音的,特別講究曲調圓滑流暢、婉轉悠揚。”張樹先十分不厭其煩地給我詳細介紹了他的吹奏技巧,讓我耳目一新。
木葉的音色和小嗩吶相似,清脆明亮、悅耳動聽、近似人聲。它可以獨奏、合奏,也可以為歌唱、舞蹈作伴奏,在白族地區,木葉還被用于白劇音樂中,演奏的樂曲大都選自人們所喜聞樂唱的民歌曲調,有著十分豐富的表現力。
“老張先生,今天我們從你的音樂人生,說到龍頭三弦,又說到木葉,真是收獲不小,今后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還要來和你多交流。”在采訪即將結束的時候,我欣慰地對張樹先說。
“李老師,我們互相學習,今后一定還會有機會交流的。”張樹先謙虛地回答。
我接著問道:“你這幾十年來帶出來了幾個徒弟?”這是我對每一個采訪對象都要問到的一個職業性的問題。
“徒弟么?多了,至少也有30多個了吧。”張樹先想了想,回答我。
“老張先生,在你的影響下,你們一家人都應該是吹拉彈唱的高手吧?”在不知不覺間,我把對張樹先的稱呼改成了“先生”,這是我對一個傳承人起碼的尊重。
張樹先聽到我稱他為“先生”,愣了一下,隨即高興地說道:“是啊是啊,李老師,就說我吧,龍頭小三弦和木葉是我的拿手好戲,另外,嗩吶、笛子對我來說也是小菜一碟。至于我媳婦嘛,就不消說了,我和她就是在打歌場上唱田埂調時認識的。除了我媳婦,我大兒子張勝偉也是在16歲時就會吹拉彈唱了,他唱的地方民歌在我們地方還是小有名氣的。另外,兒子媳婦也會拉二胡……”
“呵呵呵,你們一家人成了名副其實的音樂世家了。”我打斷張樹先的話,說道。
“可以這樣說吧。”張樹先回答我。
張樹先告訴我,他在32年前就開始帶徒弟,幾十年來,前前后后已經帶出來了30多個徒弟,年紀大的有72歲,小的才有7歲,現在還在和他學的徒弟還有18個。
“茶壺有嘴不說話,三弦無嘴話又多;板凳有腳不走路,三弦無腳闖四方……”在采訪結束時,張樹先情不自禁地又一次彈起龍頭三弦,即興為我唱起了鶴慶甸北的田埂調,歌聲蒼涼悲愴,有一種大理高原水鄉的味道,我心里一驚,這不正是鶴慶民間形容的“把人的心都割走了”的那種腔調么……
“音樂不是用眼睛訴說的,而是用內心歌唱,我希望用歌聲給朋友們帶去更多快樂和美好的感受。”張樹先最后說道。
編輯手記:
非物質文化遺產,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聲音、形象和技藝為表現手段,并以身口相傳作為文化鏈而得以延續,是“活”的文化及其傳統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過程來說,人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大理人民孕育了絢麗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鶴慶縣省級非物質文化傳承人張樹先,上天帶走了他雙眼的光明,卻賜予了他優異的文藝天賦,作為最基層的技藝傳承者,雖然他的眼睛看不見,卻憑借對文藝的熱愛始終不言放棄,一直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繼續著他的文藝夢想。
關愛鄉土藝人 關注民間藝術 關心技藝傳承
責任編輯:彭瓊瑤
投稿郵箱:qyao72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