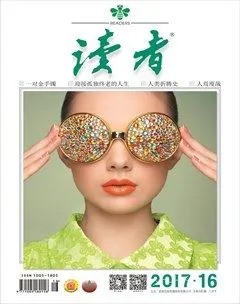文化哺育欲望
格非
最近返鄉(xiāng),我發(fā)現(xiàn)“污染”這個詞竟然已經(jīng)頻繁地出現(xiàn)在那些質樸的農民口中。常聽到村里的老人說,原先每天都會出現(xiàn)在視野中的圌山,現(xiàn)在已經(jīng)看不見了。污染物像一條灰黃的毯子,將山脈與村莊隔開了。
在所謂“沿江開發(fā)區(qū)”的規(guī)劃中,我的老家不幸被資本看中,成了鎮(zhèn)江地區(qū)的化工新區(qū)之一。談到污染問題,村民們也面有憂戚。但他們更愿意自豪地向我提及另一類“新事物”,比如,鎮(zhèn)上五星級的賓館、六車道的馬路、亞洲最大的造紙廠、雨后春筍般冒出來的化工企業(yè)、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專家”……當被問及他們是愿意生活在過去那個風光秀麗的山村中,還是愿意生活在如今灰蒙蒙的“現(xiàn)代化”城鎮(zhèn)中時,他們不假思索的回答異常堅定:“當然是現(xiàn)在啦,今天的生活是過去做夢也不曾夢到過的啊。”
盡管環(huán)保人士說,抽水馬桶的發(fā)明,是人類文明史的災難之一,可事實上我們一天也離不開它。我們對它的依賴是雙重的:身體對一種便利的生活設施的依賴,以及心靈對一種文明象征物的依賴。而作為風景的圌山在我們的視線中消失,本身也就成了一個隱喻:因欲望而做出選擇,以及因選擇而付出代價。將圌山與我們隔開的骯臟空氣,歸根到底是文化的分泌物——它作為多出來的東西、人為的東西、附加的東西、奢侈的東西,與文化本身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
小時候,我曾經(jīng)對資本家將牛奶倒入大海這一行徑所蘊含的“經(jīng)濟學常識”百思不得其解。不過,我對時下很時髦的想盡一切辦法來擴大和刺激內需,并將它作為拯救經(jīng)濟首選方案的做法,仍然覺得不可思議。需求為什么需要刺激呢?難道我們餓了,手中又有錢,還不知道吃飯,冷了還不知道買衣服,需要有什么外界的刺激嗎?如果我已經(jīng)吃飽了,又受到強烈的刺激,繼續(xù)吃下去,那么除了消化不良和糖尿病,還會有其他的結果嗎?有人說,當代經(jīng)濟學或資本主義文化邏輯所關心的并不是你得不得糖尿病,它關心的是你的消費和購買欲。另外,你得了糖尿病也不是什么壞事,因為醫(yī)療方面的消費順便也被刺激起來了。在一定意義上,所謂的刺激需求,所刺激的并不是簡單的日常生活所需的消費需求,而是通過一種特殊的文化觀念所灌輸并建立起來的超級需求,也就是卡爾·馬克思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中所發(fā)現(xiàn)的那種過剩性需求。它所刺激的是一種過剩性欲望,而無休止的欲望本身正得益于文化的哺育。
記得小時候讀巴爾扎克的《歐也妮·葛朗臺》,總覺得這個吝嗇鬼的形象,與吳敬梓筆下的嚴監(jiān)生有幾分相似。但仔細想想,又覺得這兩個守財奴不太一樣。嚴監(jiān)生守財?shù)男袨椋砻嫔峡词菫榱斯?jié)約燈油,實際上,是在占有的慣性下被欲望反制。而葛朗臺的目標自始至終都非常清晰——為死后在天國占據(jù)一個好位置而拼命積累世俗的財富,其邏輯與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文化精神完全一致。因此我們可以說,嚴監(jiān)生這樣的人是屬于“前現(xiàn)代的”,他的可笑源于欲望的偶發(fā)性迷失,而葛朗臺則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文化的實踐者和犧牲品。
眾所周知,除利潤之外,資本沒有其他目的。資本家既然可以將牛奶倒入大海,他們當然也可以劫持政府,干預國家機器。比如,像美國資本家曾經(jīng)做過的那樣,通過故意延后或取消公共交通設施的建設,迫使消費者購買汽車。當然,他們也可以控制言論、媒體和話語,培育并塑造他們認為理想的消費者。這就造成了目前社會中司空見慣的滑稽局面:富人大多以慈善者的面目出現(xiàn),進而被包裝成“救世主”一類的角色,而作為污染禍首的跨國資本和企業(yè),反而成了“環(huán)保英雄”。
(林 瑯摘自譯林出版社《博爾赫斯的面孔》一書,黎 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