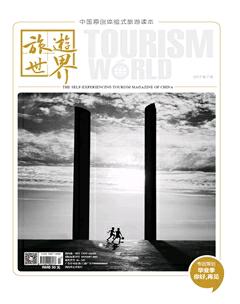到運河濕地去尋詩
董雨晨
臺兒莊城郊的運河濕地是離喧囂生活最近的“終南山”,它以水為骨,以詩為魂,以蓬勃的綠意為血肉,成了一個有詩有夢的地方。
說到詩與濕地,總繞不開中國最古老的詩歌總集《詩經》,這是一部與水纏繞的浪漫的典籍。開篇的《關雎》寫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寫的便是有愛情的濕地,《蒹葭》里寫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寫的是有思念的濕地。《柏舟》里寫道“泛彼柏舟,在彼河中……”寫的是求而不得的悲傷的濕地……
于是,五月的某一天,陽光格外慈悲,暖而不燥,我們登上了古香古色的畫舫,去臺兒莊運河濕地做一回尋詩的人。
河的兩岸綠樹環擁,莽莽蒼蒼,長長的水道是鋪開的紙箋,田田荷葉在舒展的水面上靜謐而茂盛地堆積排列。她們在五月是沒心沒肺的頑童,只顧著調皮地躍出水面,擁擠著,歡笑著,趕赴青春的約會。遠望,也是層層的綠意蔓延,在水上,在天地之間,這里的荷花姍姍來遲,還不曾到“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時節。坐在畫舫里,任意前行,悠悠的音樂隨風而來,柔柔地敲打著心扉,突然地想起周邦彥,想著“葉上初陽干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的雅致清淡,不由得感嘆古人詩心清明,我們卻只有歲月荏苒,活得堅硬、粗糙、涼薄。

彼時,那些浮在水面上的睡蓮卻開的正熱鬧,像無數雙亮晶晶的眼睛,在波光下蕩漾,好奇而熱烈地望向天空。白的,粉的,金的,黃的,像是在盛裝演出;又像傾其所有的燦爛去點染畫卷:點染著碧綠的水面,碧綠的荷葉,碧綠的蘆葦,碧綠的水菖蒲以及碧綠的北方喬木。菱角與芡實的葉子也剛剛浮出水面,與柔軟的青荇一起緩緩地招搖,它們在水里恣意地享受著綠的擁抱與寵愛,與岸上的抱莖苦荬菜花、淡黃的五月菊花、淺紫的水鳶尾、零星的彩苞鼠尾草、以及人工種植的波斯菊,遙遙相望。
我想起古運河上轟鳴的馬達與船娘的漁歌,九水通衢,商賈云集的盛況似乎并未走遠,很多年前,這里一定比現在還要質樸寧靜祥和。商隊踏浪而行,赤膊的跑船漢子用各種方言行起酒令,隨行的女人便露出潔白的牙齒,瞇著眼睛看向他們,手里可能正忙著洗衣或者淘米。而今,這里成了一個紀念,“活著的古運河”張開臂膀擁抱它的子民,看他們在二戰的炮火后如何用現代的方式行走。看著人們在廢墟中站起,看他們沿著先輩的足跡,把鄉愁從郁家碼頭送到海峽對岸,看著人們把一個綠洲里建起的古城一步步推向世界,并成為一個可以尋夢的地方。
鳥兒是濕地的精靈,它們從南方帶回游子的鄉愁,復歸此處。她們在蘆葦叢里啾啾地歌著,尤以“蘆葦迷宮”里的鳥兒叫的最響亮。鳥兒也是詩歌里恒久的意象,“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裝點了滕王閣的美;“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突出了破山寺后禪院的美;“雁聲蘆葉老,鷺影蓼花寒”是張可久詩里的意境美……當我們在木棧道上向著十里荷花廊慢慢前行的時候,清脆的鳥啼便這樣在耳畔提醒著愛與詩的存在。但總是無跡可尋,綠色是如此豐饒,像另一個世界,她們便隱身在自己的天堂自得其樂,將人類的紅塵紛紛屏蔽。
正因為這樣,人與自然應該離得很近很近才可以,否則,那些飄渺的夢和美麗的詩將無處尋找,人的靈魂將在日漸行遠的水上被無情曝曬,饑渴,干癟,而終于毀滅靈性。濕地雖然有人為的痕跡,與真正的自然尚有距離,但誰又能否認它已經用濕漉漉的晨霧,葳蕤的碧綠,盎然的生機將人們緊緊擁抱了呢?那水、魚、鳥、樹木、花草,就是人們接近自然的引領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