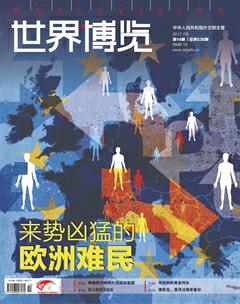美國人會做壁上觀嗎?
捷夫

當地時間2015年9月9日,丹麥Kliplev,一批難民沿著公路行走,這些難民不希望在丹麥等級,試圖步行前往瑞典。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為了比較深入地了解美國公眾對難民問題的態度,我們有必要先對所謂“地中海難民問題”的歷史作一個簡單的回顧,以此看美國是如何從歐洲對待難民問題的困境中吸取教訓的。
二戰之后,世界局勢進一步分化,局部政治、宗教的沖突加劇,導致地中海和中東某些地區種族和教派關系更趨緊張和惡劣。歷次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沖突、阿爾及利亞戰爭、兩伊戰爭、阿富汗戰爭、波黑戰爭、科索沃內戰、阿爾巴尼亞動亂、阿富汗亂局等,都曾制造了成千上萬的“地中海難民”。近年來,“阿拉伯之春”和伊斯蘭國(ISIS)的興起導致敘利亞國內戰亂,政府軍與反政府軍之間的軍事沖突愈演愈烈。而位于紅海西岸的厄立特里亞(Eritrea)因為自獨立以來一直飽受內戰、原教旨主義和與鄰國埃塞俄比亞的沖突之苦,且伴隨多次嚴重的自然災害,所以也成為難民淵藪。因而自2014年以來,“地中海難民”問題變得比以前更加嚴重,也越來越引人關注。
這些難民,有些是自己單獨行動,有些借助“蛇頭”,拖家帶口,甚至成群結隊,通過海、陸、空各種渠道全方位地偷渡進入歐盟境內。如果未被發現或阻攔,他們就非法居留下來,否則便以各種理由尋求難民庇護。
據歐盟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已超過50萬難民為了進入歐洲而“沖入地中海”,不幸死亡的人數已達數千人。這些難民中,有40%來自敘利亞和厄立特里亞兩個國家。此外,科索沃人,阿富汗人,伊拉克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也是這支“難民大軍”的主要成分。而來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船民比例雖暫時下降,卻也是困擾歐洲幾十年的“老大難”難民源,并沒有終止。
難民首先涌入的是希臘和意大利等南歐國家,再逐步向其他歐洲國家蔓延。
無比敏感的“政治正確”
正當“地中海難民問題”令歐洲國家深深處于兩難境地的時候,一個悲劇又把全世界的同情和關注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2015年9月2日,年僅3歲的敘利亞小難民艾蘭·庫爾迪在偷渡途中因溺水而不幸喪生,其遺體俯臥在土耳其伯頓海灘上的照片頃刻間被傳遍全世界,引發了山呼海嘯般的反應和同情。一時間,“救救難民”成了席卷歐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正確”。
9月9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宣布了一項“歐盟內難民強制性配額”計劃,對23個成員國進行強制性攤派,由各成員國分攤接受共計16萬“地中海難民”,甚至要求人口很少的盧森堡也要接受配額。只有事先就宣布不參加并獲得布魯塞爾方面認可的英國、丹麥和愛爾蘭三國未獲配額,但也被要求“自愿接收”。
與此同時,在民間,小庫爾迪之死帶來的“催淚效應”讓許多歐美國家民眾的同情心一下爆棚,指責政府缺乏人道精神,呼吁向敘利亞難民伸出援手。在德國、法國和英國,“9·2”后支持接納更多敘利亞難民的民調比率一度飆升,德國和奧地利甚至出現捐贈物資塞滿道路的盛況,而加拿大的民調也顯示,高達70%的民眾認為加拿大在敘利亞難民問題上應做得更多,54%民眾認為政府應接納更多難民。
在這樣的輿情、民意和“政治正確”導向的影響下,歐盟各國領導人早些時候對接納難民的謹慎態度開始逆轉。最具戲劇性的就是,事件發生的幾個月前,曾當眾告訴巴勒斯坦難民小女孩“德國接納不了你們這么多人”而將之惹哭的德國總理默克爾,“9·2”后卻一下成了對“地中海難民”最慷慨的世界領袖,被稱為“默克爾媽媽”。曾公開宣稱“法國絕不認同配額”的法國總理瓦爾斯改口,在社交平臺上稱“對難民的不幸忍不住熱淚盈眶”。原本對接受難民問題一直不松口的英國,也由首相卡梅倫出面表示“愿意根據情感和能力的綜合考量自愿接納一些難民”。其它一些國家或政要也紛紛作出象征性姿態,美國于2015年9月8日宣布,將在本財年接納至少5000敘利亞等國難民,兩天后又增加到1萬。
“默克爾媽媽”為歐洲帶來負面效應
歐洲之所以在“9·2”的催淚彈效應后競相秀“慷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地緣政治的原因,不得不有所作為。
歐洲離中東戰亂地區太近,歷史上又有接納這些地區的難民的傳統,50萬以上“地中海難民”早已源源涌入歐盟各國,其中大多數擠在靠近戰亂地區、經濟狀況又較差的意大利、希臘等國,令這些國家叫苦連天。他們不斷呼吁“歐盟一盤棋”,要求所有成員國分攤負擔。而率先“秀慷慨”的德國其實也不愿獨立背負如此沉重的包袱,因此成為實行“配額”的最大“推銷者”。面對歐盟內部步調的不一致,德國內政部長德梅齊埃甚至威脅,對反對“配額”的部分東歐國家施加停止支付歐盟基金補貼的經濟制裁,其目的是讓整個歐盟為德國的“慷慨”多少背點書,分攤一點壓力。
歐洲國家既然有苦難言,心照不宣,“9.2 事件”后那種“一邊倒”的“政治正確”就迅速地出現了微妙的變化,而歐盟的強制性“配額”也很快引發內部的強烈爭議。許多不久前才表示對難民“有條件接納、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接納”的歐洲國家,在10幾天后就迫不及待地“關門大吉”了。
這是因為,龐大的難民潮其實已經讓讓歐洲吃不消了。被德國的慷慨吸引而來的洶涌難民潮,很快讓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各國感受到其帶來的負面效應。歐元區國家邊境署Frontex于2015年9月15日公布的報告稱,全年估計有50萬以上非法移民和難民進入歐盟,德國僅慕尼黑一地,自15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抵達的難民就多達6.3萬,成千上萬的難民還在不斷涌向德國,平均每天萬人以上!一些城市的交通系統已無法正常運轉。德國民意因此在短短幾天內迅速逆轉,三分之二的德國人認為政府在難民危機處理方面的工作“相當糟糕”或“非常糟糕”。甚至連默克爾的一些重要盟友也開始發出不同聲音。迫于近乎失控的形勢,9月13日德國不得不大面積停開德奧鐵路客運,并恢復了德奧間的邊控,14日下午,全年已向德國運送45萬難民的奧地利至巴伐利亞鐵路停開,并規定只有歐盟公民或持有效證件者才能通過邊境,德國宣布“這種措施或許會在德捷、德波邊界推廣”。
德國的措施迅速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不少國家紛紛關閉邊界。在這種情況下,9月14日,歐盟內政部長會議最終也否決了9月9日提出的“強制配額”,這個配額因此而流產。
這些事實表明,出于人道對難民伸出援手固然很好,也符合歐洲的文化傳統,但一旦難民潮導致本國公眾的生活受影響,觸及自身的利益,民眾和政府就要從現實出發,對事件作深度的評估了。
糾結之后的冷靜思考
其實,歐美許多國家最初對敘利亞難民的態度是曖昧的,并不表現出超格的熱情。2015年5月雖迫于屢屢發生的難民船悲劇而推出了第一個“強制性難民配額”,但落實起來困難重重。
然而,如上所敘,“9·2”事件的轟動效應讓歐盟各國政府遭受到難民同情者的強大壓力,迫使它們顧及輿情民意,不得不表現得更“慷慨”。但是,這樣一時的痛快淋漓很快就顯現了明顯的后遺癥。成千上萬的難民已“不請自來”,對本來經濟狀況已經不甚樂觀的歐洲國家帶來難以承受的壓力,成為一個不可忽略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于是,隨著新聞熱點的冷卻,擔憂的聲音也開始多起來,政府和民眾不得不回到現實,考慮如下的一系列問題。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討論如何應對歐洲難民危機計劃。不過,這一場面對被媒體戲稱為“壁咚”。
首先,歷史上大規模、幾乎失控的難民潮 (如越南船民、巴勒斯坦難民、非洲難民等)都曾給輸入國帶來嚴重的“消化不良”,而中東難民的移民成分和情況甚至更為復雜,已在許多國家催生和加劇了一系列突發性事件,如英國倫敦托特納姆騷亂、法國《查理周刊》事件,以及澳大利亞悉尼人質事件等,早已讓西方國家心有余悸。
二是,難民一下子難以適應接納國的文化環境,短時間內不能對社會生產力有所貢獻。例如,在德國,一些分析家指出“難民從素質和意愿上都不可能馬上填補德國勞動力缺口”。
三是,缺乏對難民有效的甄別,不能排除在難民中混入懷有制造恐怖襲擊目標的極端宗教分子的可能。在英國和法國,許多人已開始擔心ISIS等極端原教旨分子混雜在難民中涌入,報端上開始出現“只對‘真難民慷慨”的提法。2015年11月的巴黎連環爆炸案,更是震驚了民眾。
四是,即使歐美國家能以仁慈之懷接受如潮水般涌來的難民,其實也只能起到杯水車薪的作用。因為“地中海難民”的根源是戰亂和貧窮,這個狀況沒有改善,就沒法根源難民潮的問題。正是因為戰亂和貧困,即便“阿拉伯之春”結束,“地中海難民”問題也未必就此一了百了。非洲船民問題就是一個例子,長期困擾歐洲。當小庫爾迪不幸喪生的“照片效應”慢慢被淡忘,那些令歐洲國家領導人頭疼的現實問題,包括就業壓力、社會福利競爭、文化差異、治安問題、社會矛盾、族際沖突、暴恐隱患等,就隨時可能重新喚起各國針對難民、非法移民的排斥乃至仇視。
最后,難民涌入導致的歐洲國家各自閉關,是對歐盟體制的直接挑戰。“地中海難民潮”引發了歐盟各國內部重新設立邊境檢查的連鎖反應,這是對《都柏林協定》和歐盟境內人、貨自由流通的申根協定這一“歐盟最偉大成果”的嚴重動搖。如果任由這種連鎖反應蔓延,或放任德國和東歐諸國間因難民問題相互拿歐盟義務“做劫”,很可能最終危及歐盟團結統一的基礎。正因如此,默克爾才不得不緊急“滅火”,呼吁“需要重鑄歐洲精神”,稱“我不認為威脅是達成協議的正確方式”。因此,因民調和“政治正確”而匆匆開放的“歐洲之門”,很快又因新的民調和對“政治正確”的無形糾正而重新收窄。

歐洲難民愈演愈烈,數千名難民通過塞爾維亞邊境涌入匈牙利。這些難民試圖自行離開臨時安置點與警方發生沖突。
從地中海難民由來已久的歷史看,不管歐美等發達國家如何從人道的角度伸出援手,哪怕是把接納難民的程度提高到不惜影響和犧牲自身社會穩定、交通安全等等的地步,也難以解決發生在戰亂地區的局勢,緩和源源不斷的難民潮。相反,加大接受難民的步伐,直接的結果是進一步鼓勵了戰亂地區民眾踏上離鄉背井的移民之路。
因此,真正的治本之策,在于治理難民源,包括幫助中東動亂地區平息戰亂、政治及種族清洗和宗教迫害,協助難民重返家園和恢復經濟,構建有利于長治久安的地緣政治秩序,并為當地的和平、發展提供國際保證等。這些措施,需要目前四分五裂的國際社會各重要成員國迅速達成共識并訴諸實質性行動。但是,目前美國和英國對解決敘利亞問題持有自己固有的看法,它們雖放低聲調表示“一切好商量”,卻始終把“巴沙爾下臺”當作解決敘利亞問題的關鍵,而俄羅斯公開向敘利亞派兵則讓問題變得更加復雜。美國對敘利亞軍方目標的打擊使美俄關系更加微妙,而軍事打擊一旦開始也就會有理由繼續,從而可能加劇該地區的不穩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