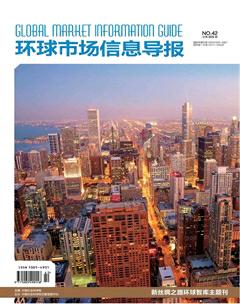農村失獨家庭社會支持現狀研究
郁斐
本文作者研究的問題是:農村失獨家庭社會支持現狀研究,主要以上海市奉賢區x鎮為例。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分為以下三類:文獻法、訪談法和調查法。其過程有文獻研究:通過大量閱讀各類期刊學術論文,以及相關碩博論文、查閱相關法律文獻、法律法規等;確定研究對象和收集資料,通過走訪奉賢區民政部門、x村等收集相關資料,了解奉賢區失獨家庭大致現狀(人數,生活狀況等),以及中央、市政府、區政府、街道地方社區的各項失獨政策和關懷措施,尋求失獨家庭信息;實地調查與訪談:深入失獨老人群體,通過訪談以及介入失獨老人參與的各項社會活動,整理分析失獨老人生活的現實情況和主要困境,以更加深入地分析失獨老人的社會支持問題;充實信息,分析數據;評估與論文撰寫。走訪中發現,不少農村失獨家庭的經濟狀況不容樂觀,相當一部分人幾乎沒有經濟來源,僅僅依靠政府的救濟或親朋好友的幫助來維持基本生活。尤其是由于疾病而造成失獨的家庭,經濟狀況更加貧困。再加上失去唯一孩子后,相當一部分失獨者無心工作,不少人還患上心里和生理疾病,這樣每月還要產生一筆不小的醫藥費開支,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課題源起
初次了解到失獨家庭,是在網上瀏覽時,看到一則新聞報道《上海失獨家庭約3.9萬戶。養老問題日益突出》。
中新網上海8月22日電(記者陳靜)上海市婦聯今日披露,根據人口學人口預測辦法估算,上海失獨家庭(即,失去獨生子女的家庭)總量約為3.9萬戶,養老問題正成為失獨家庭最突出的生活需求和社會問題。
看到上面新聞后,我們感到很震驚,能想象得到失獨將會給家庭帶來多大痛苦。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起,我國實施了“單獨”政策,因此,城市中絕大多數家庭都是獨生子女,我自己就是獨生子女。作為中國率先開展計劃生育的城市,上海獨生子女家庭比重更高,伴隨而來的失獨家庭問題也更加嚴重。此前相關部門公布上海失獨家庭總量為7000戶,很大程度低估了申城失獨家庭規模。最初七八十年代首批實施“單獨”政策家庭的夫妻如今都已經進入老年階段,他們的生活保障等問題日益突顯,也給政府和社會管理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
近年來,由于獨生子女死亡而產生的失獨現象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有關專家根據人口普查等相關統計資料,對我國失獨群體的數量、增長速度、發展趨勢進行了推斷,普遍認為我國至少有100萬個失獨家庭,每年新增失獨家庭7.6萬個。其中廣大農村地區家庭又占有很大的比例。
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和衛生部發布的《2010中國衛生統計年鑒》也顯示,中國現有獨生子女2.18億,15-30歲年齡段的死亡率至少為40人/10萬人,每年的獨生子女死亡人數至少有7.6萬人。由此帶來的是每年增加7.6萬個失獨家庭。
而相對于城市,農村失獨家庭就更顯得困難,更需盡快展開失獨家庭支持計劃和相關社會政策設計,通過社會工作者的介入來給予這一群體必要的關懷和支持。
研究問題
了解農村失獨家庭現狀。以上海市奉賢區某個鎮x村為對象,了解奉賢區失獨家庭(家庭成員平均年齡50-80歲)目前的生活狀態。
了解目前政府和社會對農村失獨家庭的支持與幫助現狀。
通過調查和研究,提出對失獨家庭社會支持的一些改進措施和政策建議。
研究方法
本課題運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為:
文獻法。文獻閱讀和分析,文獻主要源自學術期刊網上近十年來各類期刊文章、會議文集、報刊報導及博碩士論文等相關文獻,同時結合現有各類相關學術、著作出版物等紙質文獻,并對相關研究成果進行細致梳理、分析,為課題研究打下堅實理論基礎。
訪談法。通過面對面交流的方式對失獨家庭進行深度訪談,從而獲得課題研究所需數據,以及了解目前失獨家庭面臨的現狀,分析原因和提出解決方法。
調查法。對失獨家庭、街道、居委、社會團體組織、慈善基金會等進行實地調查,參與相關社會實踐活動,深入了解失獨家庭生活現狀,以及社會對失獨家庭的支持方式。
研究過程
第一階段:文獻研究
大量閱讀各類期刊學術論文,以及相關碩博論文。
查閱相關法律文獻、法律法規等。
第二階段:確定研究對象和收集資料
本課題以上海市奉賢區x村的失獨老人為主要研究對象。
通過走訪奉賢區民政部門、x村等收集相關資料,了解奉賢區失獨家庭大致現狀(人數,生活狀況等),以及中央、市政府、區政府、街道地方社區的各項失獨政策和關懷措施,尋求失獨家庭信息。
第三階段:實地調查與訪談
深入失獨老人群體,通過訪談以及介入失獨老人參與的各項社會活動,整理分析失獨老人生活的現實情況和主要困境,以更加深入地分析失獨老人的社會支持問題。
到奉賢區x村進行實地調研,采訪社會相關人士,從而了解全中國和上海市對失獨家庭的社會支持的基本情況,以及社會各界對“失獨”現象的觀點和看法。
第四階段:充實信息,分析數據
根據調研及訪談所得出的信息,完善調研和訪談提綱,對研究對象進行進一步的調查,對失獨家庭生活現狀進行更深層次的挖掘,對失獨老人社會支持的現狀及原因進行分析,同時尋求社會和政府力量來幫扶農村的失獨老人,提出使失獨老人擺脫生活困境,融入社會的方案。此外還要進行反思,以達到政策倡導的目的。
第五階段:評估與論文撰寫
本階段主要工作是通過匯集各種資料、總結工作方法來檢查介入的結果和目標,總結工作經驗,發展本地社會工作在此領域的研究,為研究失獨老人群體提供案例分析。
現有研究綜述
近年來,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和人口的老齡化,失獨老人問題逐漸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一些理論工作者和社會實踐工作者對此進行了研究和探討,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endprint
一是失獨老人面臨心理創傷,缺乏救助。趙仲杰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獨生子女的意外死亡(特別是大齡獨生子女的死亡)使父母精神受到沉重打擊,長期處于痛苦之中。張瑞凱研究發現,71.9%的家庭選擇他們而臨的最主要困難是“如何解決因子女死亡導致的家庭成員情緒長期低落”的問題。陳雯等采用仲氏抑郁癥量表,發現有76.9%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癥。
二是失獨老人的養老保障亟待完善。張瑞凱對北京市Y區調查顯示,
“失獨”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養老金和特別扶助金,其中選擇養老金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失獨”家庭比例高居首位占入,5.5%的家庭選擇了低保金,這一方面反映“失獨”家庭主要成員多處于離退休狀態,也折射出農村“失獨”家庭在沒有退休金收入的情況下,養老經濟困境更為嚴重,城鄉差別對“失獨”家庭養老問題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
三是失獨老人的生活醫療缺乏照護。袁偉霞調查統計,“失獨”父母中50%的人患有慢性疾病;患重大疾病的有60%-70%。張瑞凱調查顯示,“失獨”家庭被訪者及其配偶身體健康情況不佳,55%的被訪者表示患有某種疾病,還有6%的被訪者身體嚴重疾病。可見,隨著“失獨”父母年齡的增長,生活照料以及醫療陪護的需要就越來越迫切,然而,我國老年服務市場化水平較低,養老的專業人才資源缺乏,在居家養老仍是主要的養老模式的情況下,失獨老人的生活、醫療照護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
針對以上問題,很多學者提出了相應的對策與建議,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是將失獨老人納入救助制度。社會救助應是解決“失獨”家庭問題的主要依托,而心理救助是難點。謝勇才等提出:在對“失獨”群體進行社會救助的過程中。應該重點關注心理救助和醫療救助。此外,李赫一提出針對法律訴訟及賠償問題,需建立獨生子女亡故家庭的法律救助制度。查波等以上海市郊區為例,洪娜以蘇州市吳中區為例對獨生子女傷殘、死亡家庭進行了入戶調查,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扶助機制的建立。
二是提高失獨老人養老保障。袁偉霞提出應啟動“倒按揭”為獨生子女死亡老人提供生活保障。楊中強對我國發展逆向年金住房抵押貸款[]分析的結論是,建議推行逆年金住房抵押貸款。而劉佳等通過對“倒按揭”進行概念解析,構建了個體“倒按揭”精算模型和家庭“倒按揭”精算模型。
三是創新失獨老人救助相關社會工作。解決“失獨”家庭問題,需要創新社會工作,突出社會工作者的重要性,整合政府、社區、社會企業、義工團體、志愿者等社會資源,使社會力量的參與常態化,并積極引導“失獨”家庭自助組織的健康發展。彭善民認為針對“失獨”人群的服務目標或任務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危機應對期、封閉孤獨期、反社會期(部分“失獨”人群因得不到適當疏導,可能會產生反社會的情緒和行為)、增能發展期,并對不同階段社會工作者的工作重點提出建議。梅志罡從宏觀社會政策介入、中觀社區社會工作介入、微觀小組和個案工作介入三個層面,提出社會工作在幫助“失獨”家庭走出困境的具體建議。
綜合以上研究成果,目前我國學術界對于“失獨”問題具有著多元化的視角。但也較零散,缺乏系統性研究,并且農村的失獨老人在研究中也往往被人忽略。且有些也只是基于口頭推想,停留在關懷,溫暖,援助方面,而沒有深入進行微觀的社會調查與分析,缺乏實踐性、操作性的研究。所以,有必要嘗試,在系統調查和實踐的基礎上,將社會支持網絡系統介入失獨老人的生活環境中來進行一些研究。
對有關“失獨”問題的政策審視
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確立了20世紀末將中國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的奮斗目標,而這樣的奮斗目標又是同人均一千美元的追求相聯系的。中國當時認為:人口每增加一點,都是對“四個現代化”的沖擊,以致于得出結論:“唯一的出路就是少生”。定下了這樣一個“宏偉目標”之后,中國的人口政策在1980年驟然收緊。即從“晚、稀、少”迅速轉變為“一胎化”。其標志是1980年9月發表的《中共中央關于控制中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其主要內容就是“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公開信》是“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但后來全部成了強制。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第二十五條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第四十九條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由此,計劃生育政策正式開啟。
根據1990年全國生命表(兩性合計)權威數據:每1000個出生嬰兒大約有5.4%的人在25歲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歲之前死亡。男性和農村孩子25歲以前和55歲以前死亡的概率比前面的平均數字還要高一些。這也意味著,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因為總有一個風險比例,讓他們中的一部分將來成為失獨家庭。“失獨現象”的大規模產生,表面上看,可能是各種偶然事故造成的,深層次看,則是獨生子女家庭龐大基數與一定風險概率下的必然結果。關于這個問題,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教授穆光宗有一個觀點:失獨風險雖然說起來林林種種,但最核心的卻是“唯一性風險”或者“無替代風險”。我們國家目前的獨生子女家庭,絕大多數屬于“政策性獨生”的范疇,而非“選擇性獨生”的序列。所謂“政策性獨生”,即按計生政策規定只生一個,相對應的也就有了“政策性失獨”風險,這個風險需要國家兜底承擔。所謂“選擇性獨生”,即在有選擇的前提下只愿意生一個,相對應的也存在“選擇性失獨”的風險,這種情況,應當由自己負責。顯然。對于絕大部分失獨家庭來說,
“只要一個孩子”是政策的共性選擇而不是他們的個性選擇,因此,一旦遭遇“政策性失獨”的人生災變,國家理應立法保障其權益。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國自2008年全面實施計劃生育家庭特別扶助制度,獨生子女傷殘或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養子女的夫妻,自女方年滿49周歲后,夫妻雙方分別領取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傷殘)或100元(死亡)的特別扶助金。2012年,特別扶助金標準分別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110元(傷殘)、135元(死亡)。2013年,全中國領取特別扶助金的特扶對象共67.1萬人,其中獨生子女死亡的特扶對象40.7萬人。2014年起,中國加大對計劃生育困難家庭的經濟扶助力度,城鎮特扶標準分別提高到每人每月270元(傷殘)、340元(死亡),農村每人每月150元(傷殘)、170元(死亡),建立動態增長機制。中央財政按照不同比例對東、中、西部地區予以補助。同時,對符合條件的特扶對象,參保給補貼,醫療享救助;有再生育意愿的,醫療費用納入醫療救助支付范圍:申請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優先安排。至于立法層面,《計劃生育法》中也專門設立了“失獨家庭扶助條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