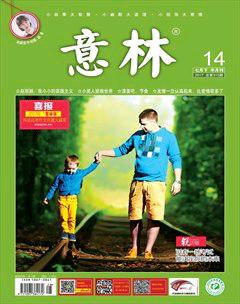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大家一起“喪”
鶴本
“你在哪一刻覺得自己老了?”——最近,在廣州老城區江南西街道一面墻上出現了一句這樣的涂鴉。
在青年亞文化當中,涂鴉既是藝術本身,又是一種秘而不宣的交流互動邀請信號。果不其然,一群年輕人迅速以涂鴉跟帖,發出自己的聲音。
在某些特殊時刻,他們感覺到“老”的來臨:“1988年中年女子刺殺金正男”“不用我媽提醒就自覺穿上了秋褲”“發現當紅男團一個都不認識的時候”“逛漫展勾搭coser,對方說自己是00后”“喝無糖可樂、跑馬拉松”……
“老”得猝不及防,激發了他們的各種小情緒,并引發了同代人的共鳴。陪著你長大的科比都退役了,你的青春也跟著落幕。你沒等到村上春樹拿諾貝爾文學獎,但等到了鮑勃·迪倫。張國榮去世原來已經14年,而陳奕迅的《十年》已經不止十年。連《哈利·波特》系列都早已完結……
90后熟得太快,早熟仿佛導致了早衰,青春期沒有留戀他們的肉體,他們迅速“被”進入中年危機。
說實話,在被聯合國“宣危”之前,你早就發現記憶力大不如前,恍惚中把牙膏當成洗面奶。你在臉上抹了一層遮瑕兩層粉底,還是擋不住眼袋的烏青;即使有十幾年的打機經驗,玩“陰陽師”還是打不過小學生;每逢佳節都會被逼婚,女友的影兒還沒見,買房生娃已經提上日程。
你的時代已經出現階層分化,90后里出現“新銳中產”,混得好的已經成了霸道總裁,早成家的已經二婚,或者準備生二胎。更多的人漂在北上廣,長期駐扎在辦公室,長出了肚腩和拜拜肉。用“蟻族”來形容已經不夠“喪”,“空巢青年”是二代升級。
北上廣的“愛情故事”里,多的是“中年危機”。某婚戀交友平臺的數據顯示,用戶中,北京單身汪最多,其次是廣州和上海。中國的空巢青年已經有2000萬,他們是20歲到39歲之間,與父母及親人分居、單身且獨自租房的年輕人。
在人生的前三十年,已經體驗了六十年的孤獨。悄悄地,初老癥提前駕到。
大家都是年輕人,有人調侃自己中年危機,有人表示不服,說這分明是矯情。
然而,矯情不是90后的特性,他們其實是聰明的“喪”一代:還沒到達中年,就是已經預見了中年危機。
90后和前幾代人一樣,登場之時扛著反叛的標簽,成為中堅之后又被后輩緊追慢趕。連對變老、優勢喪失、一事無成、未來一眼到頭的恐懼,在理想生活與眼前茍且之中的掙扎,大體都與前幾代人相同。
但他們對“老”的態度不同。以前流行講述少年式的憂愁,現在則以“喪”來應付一切。他們善于在自黑當中完成自我救贖,而且必須帶有娛樂性。有什么是表情包不能解決的?樂呵以后,又可以更好地加班了。
街頭涂鴉和網絡跟帖,都是符合年輕人特性的表達方式,各有態度,口無遮攔,仿佛一場話語狂歡。
“中年危機”是一個假命題,初老癥不屬于年輕人。他們還活在漫長的后青春期里,癱著曬太陽,耍伶俐的嘴皮,抖漂亮的機靈。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化解自己的危機。
既然青春留不住,那就做個歡快的自己。
舉鐵、長跑、吃沙拉,用人魚線偽裝中產,或者干脆和啤酒肚做伴,反正只要你不動,它永遠都不會拋棄你。
把所有新長的白發全部拔掉,或者帥氣一把,染一頭銀發,做中年女性界的fashion icon。
歲月面前,人人都有自我的危機。而“青年”的職責只有一個:找自己,并成為自己。
李宗盛都說了,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做個大叔好。不需要迷信成功學,適度生活有何不可?每個人都有正好適合自己的位置,你所要做的,只是不辜負自己。
最好的青年,是各有態度。據說,十萬青年態度已經攻占北上廣,這是網易新聞和新周刊一起搞事情的結果。
在廣州,江南西老城區的那面墻,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涂鴉跟帖。在這座充滿煙火氣的城市,你可以逗比,可以傲嬌,可以嚴肅,可以憤慨,可以沮喪,可以走心甚至走腎。每天清晨,學生、上班族匆忙而過,旁邊城市公園里的老人在悠閑地鍛煉,這幅城市圖像的背景,是自我思考、自我表達閃爍的光輝。
而在上海莫干山路、老碼頭,北京后廠村、網易北京研發中心大樓前和北京郊區一條安寧的路旁,都有這樣的涂鴉。年輕人的態度,刻在了他們生存的地方。
與現實搏擊,與自我和解,墻上的青年態度,就是當代的城市經驗。在中國,每日都有成千上萬的青年披荊斬棘,盡管有時需要“喪”一會兒,大多數人第二天還是會努力上班,一點一點地實現自己的理想。
(聶勇摘自微信公眾號“新周刊”圖/孫小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