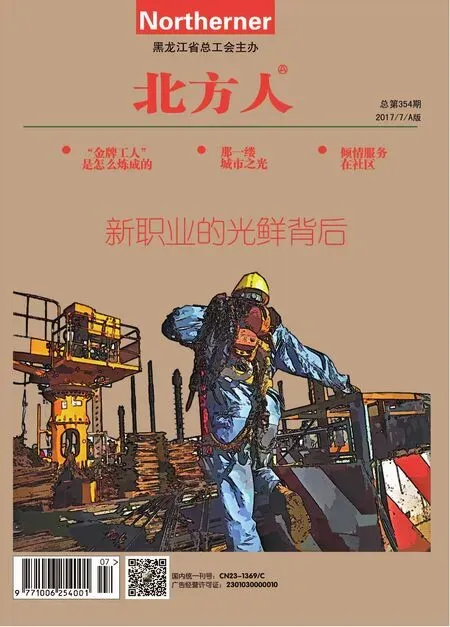活著的滋味
文/司躍雙
活著的滋味
文/司躍雙

近日,在一個黎明時分,我終于認真地讀完了英國資深劇作家蕾秋·喬伊斯的小說《一個人的朝圣》,這部小說是她的處女作,2012年曾入圍“布克獎”。
小說的主人公哈羅德·弗萊,60歲,一個在釀酒廠干了40年的普通銷售員,兒子自殺早亡,夫妻疏離,生活變得枯寂、冷硬、無味,有些荒漠了。
一天,當哈羅德·弗萊收到20年沒見的老友奎妮患癌癥的告別信后,在寄信的路上,從一個郵筒到下一個郵筒,不斷地行走和思考,最后,他決定用徒步行走的方式去看奎妮,希望用信念的力量激勵奎妮和癌癥抗爭,而去延長、挽救她的生命。他橫跨整個英格蘭,歷時87天,行走627英里,一個人的跋涉,一個人的行旅,一個人的朝圣,遇見了各種各樣的人和事兒,看到了不同景色和風光,飽嘗了孤獨、艱辛、痛苦、歡樂,種種活著的滋味,細膩的生命感悟,充盈的人生哲思,呈現(xiàn)在生存中,發(fā)生在真實里,一個生命行旅的“現(xiàn)場”,鮮活生動。
這般的“現(xiàn)場”,很引人思忖:一個關(guān)乎活著的“現(xiàn)場”,其間的多種滋味,到底如何?肉體、思慮、愛恨、生死,因何得以安頓?
最先說起的——“信念”,一個極有意味的詞。
就像哈羅德·弗萊的思考:“他發(fā)現(xiàn)當一個人與熟悉的生活疏離,成為一個過客,陌生的事物都會被賦予新的意義。明白這一點,保持真我,誠實地做一個哈羅德而不是扮演成其他任何人,就變得更加重要。”
少一點兒理性,多一點兒信念!
這些之外,還有更多的五味雜陳。
不久,跟隨他的小狗不見了,他驚慌地回頭尋找,費了很多的辛苦,在一個巴士站,看見小狗趴在一個年輕女孩腳邊,當巴士來了,小狗跟著她上了車。
他們仨,彼此沒有回頭,沒有揮手。
四季循環(huán)著走,日子一天天地悄然過去。
然后,遺忘。或是,想起。
最后一段旅程是最艱辛的。
它多像人生晚境,什么東西都沒有了,要飽嘗失去了一切的寂寞以及病痛的煎熬。最后,連生命也要沒有了,很無奈,很無助,很孤獨,很痛苦,人生活到了病苦、衰敗、朽老的境地,還有什么?還要什么?就只能靠一點兒信念,就只能靠一點兒精氣,撐著時日,唯一的,就是讓心魂安妥一些了。
塵世上,生死之間,繁復和喧囂無處不在,不做別人的跟隨者,不被跟隨者擾動,就一個人靜默,就一個人思考,就一個人悲戚,就一個人歡樂,就一個人行走,會很好的。
在掩卷的一刻,哈羅德·弗萊的行旅,卻還在我心里繼續(xù),他步履蹣跚,走向了遠方。
(作者單位:黑龍江雙礦集團新安輔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