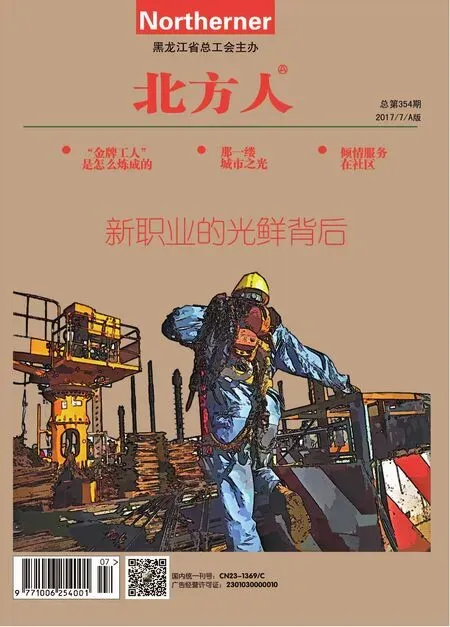讓我牽掛的娘
文/孫允剛
讓我牽掛的娘
文/孫允剛

爹去年走了,我們兄弟倆都生活在縣城,只有娘一個人還住在鄉(xiāng)下。雖然我和哥幾次勸說,讓娘進(jìn)城來與我們一起生活,但她都不肯來。娘總是說:“住在城里不習(xí)慣,你們都上班,太忙了,我又有早起晚睡的習(xí)慣,怕打擾你們休息。我現(xiàn)在還能照顧好自己,等娘到走不動了再去。”
每聽到娘這么說后,我便也無言以對了。但是我明白娘的心思,只是我不能對她說出,便深藏在了心里。看著娘那滿是皺紋的臉,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一陣酸楚,再次如鯁在喉。我知道娘是疼兒啊!
我清楚,娘年輕時就是個很要強(qiáng)的人,只要是自己能干的事,她從不麻煩別人,也包括我們。
我還是放心不下,心中時常牽掛著娘。早上我起床時,便想娘可能早就起來了,一定是軋碾去了吧?石碾那么重,娘已經(jīng)老了,還能推得動嗎?我知道,娘再也不是年輕時的娘了。娘從年輕時就有早起軋碾的習(xí)慣,雖然我常對她說,糧店有各種糧食面子,可以買著吃,但是她總不肯買,常說買會多花錢哩!軋碾,她到現(xiàn)在一直也沒間斷過,什么花生米、大米、玉米等,娘總是把它們碾碎了,拿回家做成香噴噴的糊涂。喝著娘做的糊涂,我們一天天地大了,娘卻一天天地變老了。
記得小時候,那時還處在生產(chǎn)隊時期,娘和村里大人都要頭頂炎炎烈日,在地里干活掙工分,再換成錢來買日常生活用品。娘為了多掙點工分,就讓生產(chǎn)隊給安排兩個活,一個是白天在地里干活,一個是晚上給集體看蘋果園,這樣就能多掙點工分,更好地來貼補(bǔ)家里的生活。那時候我們家人口多,日子過得非常貧困。我奶奶去世早,撇下了大小一共九個孩子,最小的小叔比我大伯家的大哥還小。爺爺是個農(nóng)村醫(yī)生,一天到晚不著家。大伯去了一個煤礦工作,一年到頭回不來幾趟。我父親和娘,還有我二姑,便擔(dān)起家庭的重?fù)?dān)。
記得在那個物質(zhì)貧乏的年代,能上供銷社里扯上幾尺布做件像樣的衣服,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了。每到過年時,娘就會給家里每個人扯上點布做一件衣服。但她對自己卻很吝嗇,總舍不得添衣服。娘的愛總能溫暖著全家,讓我們倍感幸福。后來,這一大家子人口都已開枝散葉,各自有了家庭,而娘卻還在一直守護(hù)著那個讓她付出了美好青春的家。
我能理解娘,一個伴她生活了七十多年的故土,對她來說是多么留戀和難以割舍,那里有她揮灑青春汗水的土地,有她的老屋和樸實的鄰里鄉(xiāng)親,有她最珍貴的記憶。
已到不惑之年的我,感覺自己還是一個最幸福的孩子,因為我有一位樸實善良、善解人意的娘,在我回到家的時候,還能喊上一聲娘,便知娘在,家就還在。我知道,我的娘無時無刻都在牽掛著我。雖然我不在娘身邊,但娘的愛總能像一股和煦的風(fēng)兒,從故鄉(xiāng)的方向緩緩吹來,溫暖著我這個離家的孩子。
娘牽掛著我,我牽掛著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