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作為一種尺度
艾江濤
“當你在商業、政治、交際、愛情諸如此類的東西中精疲力竭之后,你發現這些都不能讓人滿意,無法永久地忍受下去——那么還剩下了什么?自然剩了下來;從它們遲鈍的幽深處,引出一個人與戶外、樹木、田野、季節的變化——白天的太陽和夜晚天空的群星的密切關聯。”
在戶外,最初的日記
讀過《草葉集》的人,大概都會認同惠特曼為一位自然詩人。不僅如此大面積地書寫新大陸的一草一木,而且正如他雄心勃勃地要將美國文學提升到與歐洲文學并列的高度,在書的序言里,他對自然的書寫同樣自覺:“美國詩人們要總攬新舊,詩人的精神要與國家的精神相適應,詩人要體現國家的地理、自然生活以及湖泊與河流。”
有趣的是,印在1855年詩集初版本扉頁上的詩人照片,也更像一個30多歲略帶粗野的大地漫游者:留著一撮胡子,歪戴一頂寬邊黑呢帽,右手漫不經心地搭在腰際、左手插入粗布長袴的口袋,上身沒穿背心或外衣而是一件露著深色內衣的襯衫。在《我自己的歌》一詩里,惠特曼的自畫像是“瓦爾特·惠特曼,一個美國人,一個老粗,一個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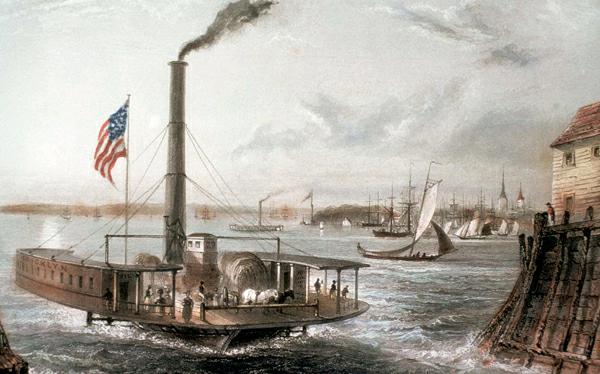
威廉·亨利·巴特萊特1838年畫作《布魯克林港口的船》(The Ferry at Brooklyn, New York)
換句話說,惠特曼是以一個來自山村的老粗形象登陸美國文壇的,自覺的形象塑造中,暗含著他渴望以自由而狂野的鄉野作風,滌蕩貧瘠而附庸風雅的文壇的想法。然而,對于這位失敗的小說家,不算成功的報人,一生先后八次不斷修訂一本詩集的詩人來說,真正將自然作為一個突出的主題描寫,還是他在1877~1881年所寫,后來收入《典型的日子》中的自然筆記。
惠特曼對鄉野景色自幼諳熟,1819年,他出生于美國長島(即印第安人舊稱的巴門諾克)亨廷頓區一個叫西山的村落里。在傳記作家的筆下,村莊的景色相當優美:“從郁郁蔥蔥的群山山巔上,尤其從山脈的最高點澤奈山上向北眺望,可以望見波光粼粼的長島灣。那紅色、粉紅色的橡樹和山茱萸、幽雅而古老的莊園、石砌的盤山路和潺潺的溪流,構成一幅別有洞天的畫面。”
雖然偶返鄉間,成年后的多數時間,惠特曼主要生活在當時尚未并入紐約的布魯克林,或者紐約。1873年1月23日,54歲的詩人在一次中風后得了至死未愈的半身不遂,不久后便去了新澤西坎姆登鄉下,和弟弟喬治住在一起。《典型的日子》里所描寫的內容,除了到美國西部與加拿大的一次旅行,多是坎姆登鄉下的景致。
惠特曼與同時代的著名作家愛默生、梭羅均有交往,與梭羅一樣,他也受到愛默生“超驗主義”思想的影響,強調萬物統一,一切都是宇宙的縮影,人的直覺可以直接抵達真理。在《我自己的歌》中,惠特曼便帶著泛神論的色彩寫道:“我相信一片草葉所需費的工程不會少于星星,/一只螞蟻、一粒沙和一個鷦鷯的卵都是同樣地完美,/而蛙也是造物者的一種精工的制作,/藤蔓四延的黑莓可以裝飾天堂里的華屋,/我手掌上一個極小的關節可以使所有的機器都顯得渺小可憐!/母牛低頭嚙草的樣子超越了任何的石像,/一個小鼠的神奇足夠使千千萬萬的異教徒吃驚。”
但與返回自然追求在簡樸生活中發現真理的梭羅不同,在投身報業熱心政治的惠特曼那里,自然更像是剩下來的東西:“當你在商業、政治、交際、愛情諸如此類的東西中精疲力竭之后,你發現這些都不能讓人滿意,無法永久地忍受下去——那么還剩下了什么?自然剩了下來;從它們遲鈍的幽深處,引出一個人與戶外、樹木、田野、季節的變化——白天的太陽和夜晚天空的群星的密切關聯。”尤其對于經歷內戰與死亡不久,對于一個半身癱瘓了三年多的人來說,更是如此。離開社會,返回偉大、寂靜、野性、接納一切的自然母親那里,整個人將得到平復與治愈。
在那些戶外樹下、溪流邊隨手寫就的便條式的日記里,惠特曼一邊用橡樹鍛煉自己的手臂,偶爾換換花樣,用大段的朗誦或歌唱練習發聲,一邊觀察著日暮中的草木魚蟲,感覺再度變得敏銳起來。他聽到午夜遷徙的鳥群發出的翅膀震動聲,看到一片黃蜂組成的移動的云彩,還有被航海者稱為“青花魚群”的大朵白羊毛似的云彩,聞到農夫燒荒時升騰起的辛辣的煙味。寫作的時候,他甚至還聽到一只蝗蟲在近午時的聲音:“一陣長長的呼呼聲,經久不絕,十分響亮,以獨特的螺旋或者飄忽的圓圈漸漸升高,其力度和速度增加到一定程度,隨著一陣振翼聲,悄悄地微弱下去。每一次用力都持續一兩分鐘。蝗蟲的歌與風景非常相配——噴涌出來,富有含義,充滿陽剛之氣,就像上好的陳酒,并不甜蜜,卻遠比甜蜜受用。”
有過鄉村生活經歷的人,對惠特曼的描述不會陌生,但那確乎屬于絕對的閑散與漫游,屬于無所事事的孩子與老人,屬于一雙發現的眼睛。在我幼年的鄉村記憶中,漫山遍野的杏樹林是絕對的樂園,我們摘下尚未成熟的青色杏子,吃掉酸掉牙的杏肉,用白色尚且柔軟的杏核作為武器,趁對方不備擠在臉上。暴雨過后,楊樹下死掉的麻雀堆了厚厚一層,觸目驚心。更要提防的是,當你在院子中洗臉時,說不定就會從窯頂的石板下掉下一條蛇來,它們專為掏食窯檐石下筑巢的鳥雀。
然而,已近六旬的老詩人惠特曼,發現得更多。在退居鄉野的那幾年間,大規模的創作已不可能,他倒更像隱居瓦爾登湖時期的梭羅,休憩在自然里,沉思冥想一會兒,隨手記下那些觸動他的片段。
獨處中發現自我
我曾在與一位半隱居在山間的畫家聊天時,流露出對山居生活的羨慕,他卻不以為然:那不過是葉公好龍,除非在已經頗為現代化的環境中生活,多少人無法忍受山居的孤獨。面對荒蠻的大自然,生存能力之外,更需要一份獨而不孤的心境。
換句話說,對自然的發現,同時伴隨著對自我的認識與發現。1876年11月8日,當城市中成百萬的人正在密切關注總統大選(最終,共和黨的拉瑟福德·海斯以一票優勢勝出)的消息與結果時,惠特曼正瘸著腿,來到一片寂靜的池塘邊坐著,在那個與世隔絕的地方,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關心。幾天前,就在樹木與天空之間,幸福的時刻會突然降臨:“但是當中午靠近,色彩變得更為明亮,有兩三個小時是很重的灰色——然后有片刻變得更灰暗,直到日落——我透過長滿大樹的山丘縫隙觀察著,令人目眩——投下火焰呈現出亮黃色、肝臟色和絢麗的紅色,還有水面上巨大閃耀的銀色斜光——透明的影子、箭矢、火花,以及超越了所有繪畫的生動色彩。”
這樣的時辰總讓人想起靈魂、無以言表,那種“一個人感覺通過他整個的存在,那情感的部分,主觀的他和客觀的自然之間的一致性,謝林和費希特如此喜愛的一致性”,也是詩人拜倫在死前告訴過朋友的他一生中僅有過的幸福的三小時,也是詩人彭斯在信中所寫到的狂喜時刻:“在一個多云的冬日散步在樹林的背風處,傾聽風暴在樹林中號叫,在平原上呼嘯。與之相比,幾乎沒有任何塵世的事物能給我更多——我不知道是否我應該稱之為快樂——但是有什么東西攫升我,讓我狂喜。那是我最好的奉獻的季節。”
早在《草葉集》里,惠特曼便在當時清教禁欲思想仍占據主流的社會大聲歌頌肉體與性愛:“‘性包含一切,肉體,靈魂,/意義、證據、純潔的東西、精致的東西、各種結果、各種傳播,/歌曲、命令、健康、驕傲、母性的奧秘、精子構成的乳汁,/地球上的一切希望、慈善的行為、饋贈、一切激情、愛、美、快樂,/地球上的一切政府、法官、神、被追隨的人們,/這些都包含在‘性里面,即它本身的各個部分和它本身/存在的正當理由。”
在《草葉集》第七版出版時,官方即特別指定《一個女人在等著我》《給一個普通妓女》等詩必須刪除。而在1860年3月,《草葉集》第三版出版前,惠特曼還因此與他素來尊敬的愛默生爭得面紅耳赤。愛默生建議他刪掉那些刻畫性生活的詩句,惠特曼卻不肯讓步,他甚至說:“在我的靈魂深處,我的意念是不服從任何約束的,我要走自己的路。”
在《典型的日子》里,惠特曼時常在一個隱秘的谷地里進行裸體日光浴,頭戴草帽,把衣服掛在附近的欄桿上,然后用硬而有彈性的鬃毛刷子刮擦手臂和身軀,直到把皮膚擦得發紅,然后要么在清澈見底的溪水中沐浴,要么在軟泥地上讓雙腳做黏糊糊的軟泥浴,要么在草地上緩慢地散步。惠特曼發現,尋找人與大地、光、空氣、樹木等等一切的和諧,僅靠眼睛和頭腦是不夠的,還必須通過整個身體,將身子裸露在自然的光影里。進行完日光浴,他還不忘嘲諷一下所謂文明的衛道者:“哦,如果城里的貧病之人、好色之人能真正再了解你一下,那該有多好!難道裸體不是下流?不,從本質上說,不是。下流的是你的思想、你的復雜、你的眼淚、你的體面。”
有些時候,惠特曼也會外出,受邀去外地訪問或演講。他喜歡看布魯克林渡口渡船上的人們,喜歡看一萬輛馬車奔馳著穿過公園,甚至喜歡看噴著濃煙奔向遠方的火車以及路邊掠過的景色。與梭羅不同,或許是出于一種難以解釋的“愛任何人、愛任何事物”,人類創造的城市文明如同荒野、群山與河流一樣,成為惠特曼謳歌與贊揚的自然的一部分。如果要說有所批評,正如早年的沈從文一樣,惠特曼是在對鄉村野性與生命力的挖掘中,映射出城市文明中人們精神的貧弱與病態,而非拒斥現代文明式的返回自然——“每當我多看一眼我們的上流階層,或者這個國家的財富和時尚的相當例外的方面,這個思想都會閃現——那就是,他們的安逸是病態的,太過刻意,罩在太多的裹尸布中,遠離了幸福——在他們身上沒有任何東西值得我們窮人和普通人嫉妒,與草木和岸灘永恒的氣息相反,他們典型的氣味是肥皂和香水味,也許非常昂貴,但讓人想起理發店——幾個小時就能發霉走味的東西。”
獨自裸身漫步在山谷中,惠特曼領悟到,一個人的時候是最不孤獨的。當然,還應該補充一句,是在大自然中,而孤獨的意義仍有待闡發。幾乎同時,在巴黎頹廢的街頭,波德萊爾在人群中發現并享受的孤獨,與惠特曼在河谷中發現的不孤獨,成為那個時代有趣的對照。
在一棵高達二三十米的大橡樹下,惠特曼有時會陷入夢境一般的恍惚:他看見他喜歡的樹走動起來,到處遛來遛去,奇怪極了,其中一棵經過時甚至俯下身子對他耳語:“我們現在這樣做可是例外的啊,這只是為了你。”也許在那一刻,惠特曼同樣領悟到近千年前一位中國作家的感受:“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在自然中寫生
寫作《沉思錄》的羅馬皇帝馬克·奧勒留曾說:“何為德行,只是對自然鮮活的、熱忱的同情而已。”對詩人惠特曼來說,大自然才是他用以考驗文學的前提,是一切“法則、標記與證明的最高結果”。
如果說海明威晚年的夢境里,經常逡巡著一只雄獅,那么老境中的惠特曼,則時常夢到海岸:“那不是別的,正是一片沒有盡頭的淺棕色的沙地,堅硬,平坦,寬闊,壯麗的海洋不停地在它上面翻滾,緩慢沖刷,沙沙作響,泡沫飛濺,如同低音鼓的重擊。”
在《海邊的幻想》一文中,惠特曼說他還是個孩子時,就幻想寫一首關于海岸的詩或什么東西,蠱惑他的地方在于:“那提示著、分割著的線條,接觸,聯合,使固體和液體聯姻——那奇怪的、潛伏著的什么東西(正如每個客觀形式最后都變成主觀精神一樣確鑿無疑),它意味著遠比最初看見的要多,這般壯麗,混合著真實和理想,彼此構成了對方的一部分。”
比起詩歌中描寫的廣度,惠特曼漫游的地方并不算多,年輕時候他長期徘徊在家鄉附近的羅克威島或科尼島的海岸,或者再往東去的漢普頓或蒙托克。惠特曼寫下大量關于海岸的詩句:“黑夜,獨自在海灘上,/那年老的母親在來回擺動著身子唱著她那沙啞的歌,/在我望著那照耀著的明亮星星時,我想到了宇宙和未來的基本曲調。”然而,海岸過于偉大,難以處理,更多時候它成為惠特曼寫作中一種彌漫著的尺度與標準。
盡管不像愛默生那樣對星空情有獨鐘,惠特曼在天文學家惠塔爾的影響下,學習到許多關于星空的知識。1880年2月19日夜間,一個晴朗而寒冷的夜晚,最適合觀察星空,惠特曼隨手記錄下觀察筆記:“月亮圓了四分之三——畢星團和昴星團的簇簇星體,中間是火星——巨大的“埃及人”橫躺在天空中(它由天狼星、南河三,還有天船座、天鴿座和獵戶座的主要星宿組成);就在東方牧夫座的北邊,在其膝蓋處,大角星升起在一小時方位高了,它登上天空,野心勃勃,發出火花,仿佛想與至尊的天狼星挑戰一般。”惠特曼的觀察帶有明顯的文學趣味,反過來,群星和月亮則讓他領會了所有自由的空白,那熔鑄在幾何學最高的精確之中的音樂與詩歌的不確定性。
寫作以外,一旦涉及對其他詩人的評論,惠特曼更是幾乎不能離開那些自然的譬喻,更多時候,他是以欣賞一棵樹、一片云彩、一條溪流的態度去看他們的作品。在他那里,愛默生的詩歌如琥珀般透明,像他喜歡歌唱的野蜂的蜂蜜一樣;布萊恩特則是河流與森林的歌手,帶給人們戶外的氣息,干草、葡萄、赤楊生長的邊界的芳香。
不僅是文學,一切都與自然發生著富有隱喻意味的本質聯系。惠特曼發現,民主與戶外的關系最為密切:“美國的民主,在它無數的個體方面,在工廠、車間、商店、辦公室中——擁擠的街道和城市的房屋,以及所有生活復雜的方方面面——都必須與戶外的光、空氣、生長物、農場景象、動物、田野、樹木、鳥、太陽的溫暖和自由的天空保持固定的接觸,以變得堅韌、有生機,否則,它肯定會縮小和變得蒼白。”
多少有些奇怪,這不正是《詩經》時代的語言與言說方式嗎?再想想,惠特曼意想中的和諧與融通,或許本就流淌在東方文化的河流中。
《典型的日子》
(Specimen Days in America)
作者:[美]瓦爾特·惠特曼
譯者:馬永波
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2008年8月
《瓦爾登湖》
作者: [美]亨利·戴維·梭羅
譯者:徐遲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年:2006年
《金薔薇》
作者: [俄]康·帕烏斯托夫斯基
譯者:戴驄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年: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