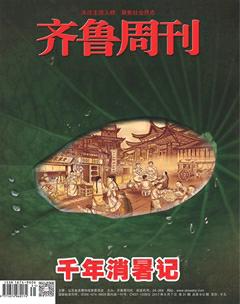千年消暑記
在自然中安適的能力
“燎沉香,消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檐語。葉上初陽干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宋代詞人周邦彥的這首《蘇幕遮》,可謂是寫盡了千百年來的夏日風情。
每一個季節(jié),自有風情,然而只有在那些更為極端的溫度中,我們才能更加深切體會涼風、火爐的生活詩意。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千百年前,《詩經》如此描繪炎炎夏日,那時,這是一段極為不適的時光,“暑景方徂,時惟六月。大火飄光,炎氣酷烈”,在沒有空調、冷氣機等設備的古代,炎夏日子是難熬的,所以有“苦夏”之說。
不過相應的,古時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遠比現在好得多,那時也沒有“暖室氣體”排放和所謂“熱島效應”。所以我們讀古代詠夏的詩歌,明顯可以感受到有絲絲涼風襲來,誠如秦觀詩云“芳菲歇去何須恨,夏木陰陰正可人”“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亭幽”。
“何處堪避暑?林間背日樓;何處好追涼?池上隨風舟”,這是白居易的納涼詩,滿篇洋溢悠閑恬淡,雖逢酷暑難當,但登上“林間背日樓”或者光顧“池上隨風舟”,就可優(yōu)哉游哉,盡享太平了。
在炎熱的夏日,古人只需走到臨水的亭臺樓榭,就可找到納涼的好去處,這是很值得現代人眼紅的事情。王維為了消暑,抱著古琴走進幽深碧翠的竹林,席地而彈樂而忘返,給后人留下了千吟不厭的《竹里館》:“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先人們能夠在炎夏里輕易找到“芳菲歇去何須恨,夏木陰陰正可人”“過雨荷花滿院香,沉李浮瓜冰雪涼”的好去處,值得我們羨慕的,今天的我們,似乎只有到景區(qū)、深山以及空調房中,才能體會到消暑的詩意與舒適。
現代技術的進步讓我們喪失了在自然中安適的能力,我們急迫地躲進空調房,以此隔離不再溫柔的世界。
閑暇世界的生長
漠漠花開無盡夏,在這個人間草木最為繁盛的季節(jié),藍天白云分外分明。熱辣辣的午后,最快樂要數在街上奔跑的孩子。他們可以肆意跑到噴水池邊,在水柱間來回穿梭,打水仗,仿佛這夏日水池是孩子們的天堂。
作家程乃珊曾寫到:我的暑假生活,是由痱子粉、浴皂和蚊香的混合型馨香、西瓜的清新和小伙伴們的喧笑構成的。那時沒有電視,也沒有游戲機,但我們的暑假是那樣豐富多彩,至今難以忘懷。那些年的夏天,沒有補習班,沒有夏令營,農業(yè)學校就是孩子們的補習班,天與地就是孩子們的夏令營。
如今,當城市的孩子們輾轉于各種夏令營、出國游學,甚至疲于應付各種補習班、才藝培訓之時,農村的“小候鳥”們也開始了漫長的旅途奔波,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為了到城市與父母團聚。消夏對他們而言是奢侈的,他們要消化的是父母的焦慮、親情的距離。
日本心理學家河合隼雄在《孩子的宇宙》一書中提出“彼側世界”的觀點。很多文學尤其是兒童文學作品中,都有一個“奇妙的超時空世界”,作者稱之為“彼側世界”,而“此側世界”就是我們的現實世界。河合隼雄提醒我們,空閑時間對孩子的成長意義重大,他們可以在此肆無忌憚的生長。
相比之下,如今的中國式假期,卻總是有那么多的無奈與惆悵。當假期被賦予過多功利主義的色彩,當放假的美好和現實生活結合,放松,減壓,通過休假尋找生活的真諦等等這些事情在中式特色假期中都來不及去思考。
邁過四時分明的時代
電影《菊次郎的夏天》中:背包上斜插的太陽花,頭頂上高撐的洋芋葉,叮當作響的天使之鈴。還有原野上綠意浩沛的植物,以及迷離的夏風,喧嘩的海浪。這些都只能成為當代少年的夏日想象,還有那只象征童年的蜻蜓也已經遠去很久。
現在,我們不過是從一間空調房鉆進另一間,從一臺電腦移向另一臺,從一個網頁走向另一個。如果沒有特別需要奔波的事情,會拉下防紫外線的雙重窗簾,把整個白天都封閉在水泥建筑物里。會在夜晚,以一個慢慢下滑趨于完美的“北京癱”姿勢,倒在沙發(fā)和空調的冷氣之中,刷著無窮無盡的朋友圈。
而在工業(yè)文明左右之下,季節(jié)對生活的影響明顯弱化。夏季還剩下些什么?人們用現代科技邁過了四時分明,傷春悲秋變成了一種足夠奢侈的情緒。
仿佛一切都在消失,夏天也是,它再也回不到從前的樣子。從農耕社會的夏天轉移到工業(yè)文明的夏天,夏天的外延在不斷擴展,它的精神內涵呢?泰戈爾的《飛鳥集》中寫道:“生如夏花之絢爛”。臺灣作家羅蘭曾在散文《夏天組曲》中也寫道:“夏天的花和春花不同,夏天的花有濃烈的生命之力。如果說,春花開放是因為風的溫慰,那么夏天的花就是由于太陽的激發(fā)了。”
那些奔馳、跳躍、飛翔的生命力量,那些對命運不斷追索,對生存環(huán)境不斷完善的人類靈魂,才是夏日變遷中的驚鴻一瞥,歷久彌新而又彌足珍貴。
(本專題12-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