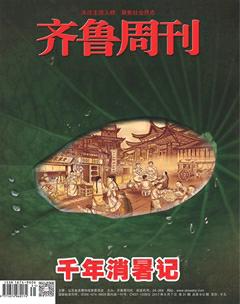消失的夏天:改變人類的力量
吳永強

仿佛一切都在消失,夏天也是。季節在不斷變化、升華,從農耕的夏天轉移到工業的夏天,夏天的外延在不斷擴展。而不變的是什么?對命運的不斷追索,對生存環境的不斷完善,充斥于季節之上的人類靈魂,為我們塑造了無數經典的季節輪回。
夏天從未停止消失的步伐,也從未停止更新的速度
90后歌手蔡有錢唱著《消失的夏天》:“你說那個消失的夏天,讓我再也回不到從前,現在的我還是很留戀。”那些美好的旋律,仿佛都存在于夏天,比如夢中的童年,叫著夏天的知了還在池塘邊的榕樹上,記憶還在,人已經不再。
仿佛人類的夏天也正在消失。
嗡嗡響的空調,把我們從夏天拯救出來,扔到和煦的環境下。房間不再是蒸籠,風扇鉆進博物館,夏天本該有的熱浪進入歷史的虛空。如同大棚菜改變了人的飲食結構,使得四季不再分明,如今的夏天,哪里還有夏天的樣子?
夏天是屬于故事的季節。瓜果的藤蔓爬上了木制的架子,夏日夜晚的架下,一群人坐在一起,遙看月中的嫦娥與吳剛,你一言我一語,故事就這樣產生了。清代就有一部短篇小說集《豆棚閑話》,以豆棚下輪流說故事為線索,串聯起12篇故事,類似《一千零一夜》《十日談》。“豆棚瓜架”也成為故事或小說的代名詞,王漁洋評價《聊齋志異》:“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蒲松齡擺攤賣茶收集故事的傳說,凸顯了小說的民間性,我們料定這也應該是發生在夏天的故事。
不只有故事,就連愛情也要發生在夏天,在月亮的見證下,新的游戲開始,在牽牛織女的見證下,由相識到相戀。如果有一個設定,“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這些經典的時刻,如果不是發生在夏天,其情其景是否會大打折扣?
古老文明塑造了獨特的夏季文化,從“刀耕火種”開始,人類就認識了這個萬物生長的季節的重要性。伴隨著雷電、暴雨、冰雹,一切自我認知和對世界的認知在悄然發生。直到飽滿的青紗帳,因其廣袤的神秘性,作為自然情欲和戰爭敘事而存在。就連黑瞎子和野豬也要到青紗帳里,去和人類分一杯羹。
這自然要說到物種的傳遞,近代文明將美洲的玉米帶到亞洲,同一塊土地養活的人數呈幾何倍數增長。也就是說,每周的夏季被移植到了亞洲,季節的外延無限擴展。
于是,作為蓄積能量的季節,大地和雨露把植物養到最飽滿的狀態,把動物的肚皮不斷撐圓。直到秋季來臨,新的一輪收獲和殺戮開始了。一切的決斷都要等到秋天,就連婚姻也是,夏天約會戀愛的那些日子逐漸失去,兩人約定“秋以為期”,步入常態化的婚姻。
而今,豆棚瓜架自然已淡出人們的視野,文化的制造者也不再是架下乘涼的那一批人,產業的細分使得文化也成為一種機器生產。在夏日的城市街頭,那些以無聊的名義喝酒、唱歌、瘋狂的人們,成為一種新的文化。
一種夏天消失了,新的夏天又來了。其實,夏天從未停止消失的步伐,也從未停止更新的速度。季節的模糊性成為新的命題,而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避暑勝地,又成為規避夏天的另一種方式。類似的躲避夏天,或者進入真正的夏天的行為,作為人類的天性而存在。
季節改變的人類命運
人類的成長充滿了對抗,首先是與自然的對抗,其次是與同類的對抗。在與自然的對抗中,抵御嚴寒的能力決定了一個族群的生命力。溫帶最先開始出現人類文明的曙光,比如黃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那時候更北的北方意味著什么?寒冷、饑餓、蠻夷,而南方呢?在更加炎熱的區域,以夏天為號召的地方,是煙瘴、溽熱的代名詞。抵御北方成為永恒不變的主題,而向南拓展則成為可能。
來自北方的異族,不論是匈奴還是契丹、女真,始終不變的主題就是南下,這些來自苦寒之地的人們,更加恐懼嚴寒。如同歐洲北方的日耳曼人,他們用幾個世紀的不斷襲擾,瓦解了強盛的羅馬帝國;在東方,這種情況也沒有太大改觀,雖然中原民族在某種程度上占據過上風,但對北方民族的抵御竟然成為數千年國防領域最嚴峻的主題。
而南方呢?那些溫柔的地方,老天賜給了他們足以生長植物的土地和降水,使得生活的成本降至最低,即使不事生產也不至于餓死,大自然提供了足夠的養料。熱帶的許多地方,時間好似停滯,沒有進步成為最大的進步。當近代的大幕徐徐拉開,這些地域幾乎無一例外成為溫帶崛起的現代國家的殖民地。
此時,夏天敗給了春秋。
嚴寒時刻打擊著人們,提醒人們去爭取更加自由的自然環境。而那些生活在夏天里的人們,衣食充足,陽光熾烈,在海灘上曬著日光浴,倏忽間就被另一群人超越。于是,夏天就有了一種享樂主義的味道。當此時,不斷瘋長的植物雖然提供了大量養分,但其虛空的本質并不足以抵御那些堅硬的襲擊。
當冬天和夏天對決呢?又會出現怎樣的情景?
如果將對季節的梳理融入歷史事件的探索,你會發現一個奇妙的現象:嚴寒拯救了俄羅斯的國家命運(拿破侖入侵、希特勒入侵),使這個國家成為“不可被侵略的國家”;干旱引起的饑荒引發農民起義,最終葬送了大明朝。夏天是攻伐的完美季節,1942年的夏季攻勢,德軍兵敗蘇聯;1947年的夏季攻勢,林彪率領的民主聯軍用50天,殲滅國民黨軍83200人,收復和一度收復城鎮42座,打通了南北滿的聯系,擴大了解放區;1951年的夏季攻勢,美軍在朝鮮經過一個月的苦戰,付出傷亡7.8萬人的代價,僅僅在東線推進了179平方公里,未達到此次攻擊的目的。
與季節有關的歷史事件還有很多:1788年夏天,法國遭遇持久冰雹的襲擊,民眾生存受到威脅,第二年爆發了大革命;中世紀的歐洲,一旦出現嚴寒天氣,年輕女子就會被指控操縱天氣,成為收成不好的替罪羊;過度采伐森林導致的持續干旱,最終摧毀了輝煌的瑪雅文明;在1939年的蘇芬戰爭中,在更不怕冷的芬蘭人面前,俄國人同樣被冰雪阻擋。
而在工業文明左右之下,季節對時代的影響明顯弱化。夏季還剩下什么?除了波德萊爾詩句中所說:“那時,我的美人,告訴那些蛆,接吻似的把你啃噬。”城市下水道里,蛆蟲肆虐,這似乎是現代文明無法掩飾的惡果:作為動物的蛆存在已久,只有披上現代文明的外衣,才有了改變時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