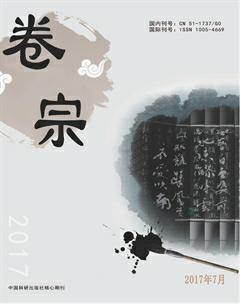淺談中國翻譯史中異化與歸化的翻譯主張
摘 要:歸化和異化是翻譯中的一個(gè)重要問題,同時(shí)也是一大爭議。本文簡單回顧了中國翻譯史上幾種歸化和異化的翻譯主張,指出歸化和異化都是重要的翻譯策略,不是相互排斥的對(duì)抗性概念,而是并存,相輔相成的。
關(guān)鍵詞:歸化;異化;并存
1 起源
回顧中國翻譯史,有關(guān)直譯與意譯的爭論一直不斷。隨著翻譯研究的重點(diǎn)從語言的操作轉(zhuǎn)移到跨文化交際的行為以及西方譯論的引入,異化與歸化成為了爭論的焦點(diǎn)。異化和歸化翻譯可謂直譯與意譯概念的延伸。1813 年,德國古典語言學(xué)家、翻譯理論家施萊爾馬赫在《論翻譯的方法》中提出:翻譯的途徑“只有兩種:一種是盡可能讓作者安居不動(dòng),而引導(dǎo)讀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種是盡可能讓讀者安居不動(dòng),而引導(dǎo)作者去接近讀者。”1995年,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在《譯者的隱身》一書中,將第一種方法稱作“異化法”,將第二種方法稱作“歸化法”。( Venuti, 1995: 20) 概括而言,異化法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yīng)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語表達(dá)方式,來傳達(dá)原文的內(nèi)容;而歸化法則要求譯者向目的語讀者靠攏,采取目的語讀者所習(xí)慣的目的語表達(dá)方式,來傳達(dá)原文的內(nèi)容。在中國翻譯史上,特別是民國時(shí)期以來,許多從事翻譯的人也提出了類似異化和歸化的翻譯主張。
2 異化主張
魯迅多次論述了“歐化”的問題,其實(shí)也就是異化的翻譯主張。早在1918年,他在寫給張壽明的信中說:“我認(rèn)為以后譯本,……要使中國文中容得別國文的度量,……又當(dāng)竭力保持原作的`風(fēng)氣習(xí)慣,語言條理。最好是逐字譯,不得已也應(yīng)逐句譯,寧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頭換面”。 (陳福康, 1992:176)1925年,魯迅又在譯文(出了象牙之塔)后記中寫道:“文句仍然是直譯,和我歷來所取的方法一樣;也蝎力想保存原書的口吻,大抵連語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顛倒”。(陳福康, 1992:176-177)1934年,魯迅又幾次論述了“歐化”問題,他說:“歐化文法的侵人中國白話中的一大原因,并非因?yàn)楹闷妫耸菫榱吮匾!逃械陌自挷粔蛴茫阒坏貌尚┩鈬木浞ā薄?(陳福康, 1992: 300)
1935年,魯迅在《“題未定”草二》中,還有過精彩的論述:“只求易解,不如創(chuàng)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為中國事,人也化為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shí),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它必須有異國情調(diào),就是所謂洋氣。其實(shí)世界上也不會(huì)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yán)辨析別起來,它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面當(dāng)然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著原作的豐姿,但這保存,卻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它原是洋鬼子,當(dāng)然睡也看不慣,為比較的順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裳,卻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剜眼的,所以有的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從這段中,可以看出魯迅對(duì)于“歐化”“洋氣”問題的主張,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是為了“益智”,與旅行外國相似,必須有“異國情調(diào)”;二是為了“輸入新的表現(xiàn)法”,以改進(jìn)中文的文法。(陳福康, 2011: 248-249)
盡管后來有關(guān)魯迅“寧信而不順”的主張頗受爭議,但我們必須理解,魯迅正是站在中國語言改革的高度來論述他的主張。而且在筆者看來,魯迅認(rèn)為在世界上也不會(huì)有完全歸化的譯文,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特別是一些獨(dú)具特色的異域詞匯和文化,是人類智慧的結(jié)晶。采取異化的翻譯策略有利于它們保留和傳播,讓更多人認(rèn)識(shí)和了解。
3 歸化主張
傅雷有著深厚的中外文化修養(yǎng),多次指出中西思維方式、美學(xué)情趣方面的異同,從而強(qiáng)調(diào)翻譯決不可按字面硬搬,而必須保存原作的精神和美感特征。1951年,傅雷在《<高老頭>重譯本序》中說:“以效果而論,翻譯應(yīng)當(dāng)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1963年, 傅雷在致羅新璋的信中,再次明確說:“愚對(duì)譯事看法甚簡單:重神似不重形似”。并且強(qiáng)調(diào):“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 (陳福康, 2011: 320)在筆者看來,傅雷的翻譯主張,類似于歸化,讓讀者讀的譯文仿佛是目的語的仿寫。而事實(shí)上,這種“神似”對(duì)譯者要求極高,幾乎是很難做到的。
錢鐘書在譯學(xué)界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1963年,錢鐘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談到了兩種翻譯法:“就文體或風(fēng)格而論,也許會(huì)有希萊爾馬訶區(qū)分的兩種翻譯,譬如說:一種盡量‘歐化,盡可能讓外國作家安居不動(dòng),而引導(dǎo)我國讀者走向他們那里去,另一種盡量‘漢化,盡可能讓我國讀者安居不動(dòng),而引導(dǎo)外國作家走向咱們這兒來。”(陳福康, 2011: 343)這里提到的兩種翻譯方法就是歸化和異化,但在這篇文章中錢鐘書沒有明確表態(tài)。不過在此文中,他把“化境”視為文學(xué)翻譯的最高理想,他說:“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zhuǎn)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xí)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拗口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fēng)味,那就算得人于‘化境”。這種造詣高的翻譯,就像原作的“投胎轉(zhuǎn)世”,軀體換了一個(gè),而精魂依然故我。他還說:“譯本對(duì)原作應(yīng)該忠實(shí)得以至于讀起來不像譯本,因?yàn)樽髌吩谠睦餂Q不會(huì)讀起來像翻譯出的東西”。 (陳福康, 2011: 341)這種“化境”,筆者認(rèn)為也算得上是歸化的翻譯主張,而錢鐘書自己也指出“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實(shí)現(xiàn)的理想。”可見,這是翻譯中的一種理想境界,現(xiàn)實(shí)中基本達(dá)不到。
4 結(jié)語
魯迅的“歐化”, 在后人的理解上有了一定的偏頗。傅雷的“神似”以及錢鐘書的“化境”,也只能是翻譯中的理想境界,在現(xiàn)實(shí)中也很難達(dá)到。而異化與歸化是文學(xué)翻譯研究中一對(duì)非常重要的范疇,近來國內(nèi)外已有許多學(xué)者對(duì)此作了較深人的論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數(shù)郭建中的《翻譯中的文化因素: 異化和歸化》一文,此文對(duì)歸化與異化孰好孰壞之爭做了一個(gè)終結(jié)性的回答:歸化與異化都有其存在的價(jià)值和意義,由于翻譯的目的、文本類型、作者意圖以及目標(biāo)讀者的不同,翻譯策略的選擇也不會(huì)相同,并且得出兩者永遠(yuǎn)共存的結(jié)論。(郭建中,2000:276—290)。這是一種折中的翻譯策略,但也是非常客觀的,異化與歸化不是相互排斥的對(duì)抗性概念,而是可以并存,相輔相成的。這對(duì)翻譯實(shí)踐,特別是文學(xué)翻譯實(shí)踐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隨著全球化不斷加深,異化可能會(huì)大放光彩。
參考文獻(xiàn)
[1]陳福康.中國譯學(xué)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
[2]陳福康.中國譯學(xué)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
[3]郭建中.翻譯中的文化因素:異化與歸化[J].外國語,1998,(2).
[4]錢鐘書.林紓的翻譯[A].七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 Venuti ,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London & New York: Routedge, 1995.
作者簡介
劉翠紅(1990-),女,山西呂梁,陜西師范大學(xué),2016級(jí)碩士,研究方向: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