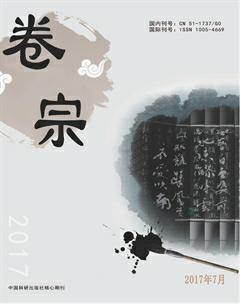“虛構”中的實相
陳路
摘 要:在《檔案中的虛構》中,娜莉塔·澤蒙·戴維斯通過對“虛構”(fiction),即塑造了文本的敘事技巧,來探究其背后所蘊含的社會、政治變量。戴維斯的研究手法,并非其獨創,而代表了新文化史這一史學研究的范式轉向。其最大特點,便是文化轉向與凸顯文本的敘事性;強調歷史文本書寫的敘事性;已經將人類學的若干方法,引入歷史研究之中。
關鍵詞:新文化史;人類學;歷史實相
1525年一位名叫路易·佩桑的屠夫因殺人而被囚于夏特萊監獄中。由于他罪證確鑿,因而如果是在我們的時代,他似乎難逃法律的制裁。但是在16世紀的法國,若他能購得一份由皇家公證人擬定,并獲得司法部法官們簽署的赦罪書。那其便很可能通過皇家法庭的審批而獲得國王的恩典,也就是說其罪行將會被赦免。而在這一過程中,由皇家公證人與敘述者共同建構的赦罪故事,在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盡管“虛構”總是史料的構成部分之一,但是很少有史料能如同赦罪書一樣,將“虛構”呈露的如此明顯。在托馬·曼尼的求赦書中,被害者——即求赦者的妻子,被描述為放蕩無恥、屢教不改的蕩婦,而求赦者則是一位品行優秀,有著良好聲譽并一再容忍妻子淫行的丈夫。而在瑪格麗特·瓦萊的求赦書中,被害者——即求赦者的丈夫則被描述成嗜酒暴躁的褻圣者,而求赦者雖品行端正卻在丈夫的虐待下被逼的精神失常,并一度面臨生命的威脅。在這里。求赦者與皇家公證人共同建構能夠為其博得同情的赦罪故事,以求獲得國王的恩典。對于此類史料,若按照通常的做法,唯有剝除文本中的虛構成分,“才能夠獲得干癟(bare)且不加修飾(unadorned)的真相。”
但戴維斯卻認為通過“虛構”——即建構文本的敘事技巧,同樣能夠觸摸到這背后的歷史實相。求赦者在陳述案件時,都必須由當下經驗出發,才能夠塑造出打動傾聽者的赦罪故事。這便使觸摸支撐著赦罪制度的司法體系,并觀察日益強大的王權如何將桀驁不馴的貴族馴服為順從的臣民等歷史實相成為可能。或者如本書作者那樣,去考察不同社群在敘述故事時的不同側重,尤其是注意到男性與女性在進行敘事時,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在書中所引用的赦罪書中,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發現,男性的赦罪故事往往以職業及社會地位為中心。當他在講述自己的赦罪故事時,“突如其來”的憤怒、財產糾紛及自我防衛構成了敘事技巧的主要部分,而場景的布置則往往與宗教節慶及社會地位密切相關。而若敘述者為女性,則構成赦罪故事中心,卻很少是職業及社會地位,而是性別。同時家庭、性名譽、繼承權構成了敘事的主題。男性的故事常常提到尊嚴,而女性的故事中,家庭與性侵則占據著主要部分。
何以如此?戴維斯認為這與“虛構”的社會性緊密相關,求赦者會根據社會對其的認知,來建構自己的赦罪故事。比如盡管憤怒為天主教所定義的七宗罪之一,不可能獲得上帝的寬恕。但是對于傾聽者來說,若憤怒是突如其來的,則在正當的情況下足以構成赦免的充分理由。但16世紀的法國社會卻普遍認為,女性的憤怒是日積月累而成,不易輕易消去,因而女性的憤怒很少是“突如其來”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女性試圖將憤怒編入她的赦罪故事之中,那么可能會使傾聽者認為這是一場預謀的罪行。故對于女性的求赦者而言,將恐懼而非憤怒作為觸發突然性事件的理由,便成為合理的選擇。另外因女性難以如男性一樣,從圣經與民間故事的傳統中,獲取赦罪故事的靈感,因而她們也就被迫在赦罪故事中,提供更多的原創性細節。而這些細節卻又不可避免的來自于日常生活,這個她們在傳統社會中被束縛其中的空間。
戴維斯在進行赦罪書研究時,所采取的獨特研究方式,與西方歷史學界發生的文化轉向緊密相關。所謂文化轉向,并非是指在眾多的歷史研究取向中,增加“文化”的概念。而是存在三個層面或維度。即就西方史學主流而言,由社會史向文化史的轉向;就文化史內部而言,由傳統文化史向新文化史轉向;就歷史學科其他分支而言,由非文化因素向重視文化因素的轉向。
這種轉向的發生,是內外雙重因素作用的結果。就內部因素而言,主要源于對馬克思主義及年鑒學派這兩種支配性范式反思。 “原先占據統治地位的真理、規律、客觀性、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等分析范疇成為批評的對象被重新審視。”這便導致人類學中的文化要素,被大量引入歷史研究的范式中。甚至連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代表人物E·P湯普森,也摒棄基礎/上層建筑的隱喻,而致力于研究其所謂的文化與道德調解,即處理物資經驗的文化方式。在年鑒學派方面,盡管勒華拉杜里的博士論文《朗格多克的農民》中,沿襲了布羅代爾的風格,并被認為是社會史的經典著作之一。但其隨后所著的《蒙塔尤》卻轉而去研究農民的心態與文化,而其所說的文化正是人類學家所認為的文化。可見,人類學特別是文化人類學構成這種轉向發生的一個重要外在因素。
除人類學外,來自語言學與文學批評也是促成此種轉向的重要原因。同時因海登·懷特、拉卡普斯等人的影響,“歷史學家愈來愈明確地意識到在他們工作中——包括研究和書寫——的文學與敘述成份這便促使對傳統宏大敘事及敘述中的虛構性的反思;以及從分析轉向敘事模式的敘事史的復興。此外,歷史學者也越發開始關注歷史文本中的敘事要素。而《檔案中的虛構》,無疑是此種歷史研究范式轉向的代表性著作。除了在戴維斯、羅伯特·達恩頓、彼得·伯克等新文化史家的著作中外,還可以在史景遷、孔飛力、黃仁宇等歷史學者的著作中,看到這種敘事史的明顯痕跡。
本書可以說是體現了此種轉向的代表性著作。就研究對象而言,本書的描述主體,是16世紀法國社會的民眾特別是下層民眾,這既是馬克思歷史學的顯著特色,也是新文化的主要研究對象。其次,作者通過引入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將民眾的心態與文化,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深描的手法去刻畫16世紀法國社會的眾生相。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文化,并非傳統文化史所研究的精英文化,也不純粹是新文化史關注較多的大眾文化,而更接近于兩者的混合狀態。戴維斯借由將赦罪故事與同時期的其他文本,特別是代表著精英文化的戲劇進行對比,揭示了不同階層文化互相影響的動態過程。
就研究方法而言,作者將虛構本身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從而分析出這背后所蘊含的歷史實相。既然求赦者所構建的赦罪故事,體現了社會對其的認知。那么我們自然也就能由此把握這些個體所構成的群體,在法國社會中的具體位置,并進一步了解當時法國社會的結構。
在寫作技巧上,本書也體現了敘事史的回歸。自年鑒學派以來的社會史,偏重于以社會作為分析對象,在其中幾乎看不到人的存在,而敘事技巧也不再是歷史學者關注的重點。而戴維斯通過一連串的故事,將16世紀的法國社會呈現在我們的面前。自戴維斯的筆下,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個體而非枯燥的數據占據了敘事的核心位置。由戴維斯開始,如何將歷史寫的生動有趣,成為越來越多歷史學家關注的問題。
然而作為新研究范式,新文化史研究自身,尚存若干不足。有學者擔心此研究取向會使“事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戴維斯的著作中便存在大量“虛構”,此種“虛構”并不總是如本書一樣經得起嚴格的史料考證。在其另一力作《馬丁·蓋爾的歸來》中,戴維斯便就被批判虛構歷史人物的思想世界。而在這部作品中,我們也不僅要問,作者在自己的想象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出了史料所能支撐的程度。也許歷史學者在學習并運作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式時,也需要牢記理查德·艾文斯的教誨,謹守平實的風格,若要使用文學性的技巧,必須確知自己在做什么,并確定是有意識地在使用它,而且是用它來澄清事實,而非使之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