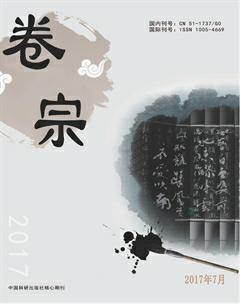論顯失公平制度
摘 要:對于乘人之危與顯失公平制度的立法安排,從《民法通則》、《民法通則意見》再到《民法總則》,立法者做出了幾近于完全不同的規定。我國早期民事立法草案關于兩者關系就存在一定爭議,而《民法通則》一錘定音,確立了二元分立的立法模式。司法實踐適用的混亂催生了《民法總則》第151條——乘人之危重歸“暴利行為”。對于顯失公平制度,兼采主觀要素與客觀要素才是最接近正義的選擇;而對于乘人之危,由于其僅對危困狀態加以利用,不足以單獨作為導致法律行為相對無效的事由。從比較法角度看,我國現行關于顯失公平的規定基本類似于德國法上的“暴利行為”,但由于缺失主觀要素彈性化的條款,《民法總則》第151條在具體適用時仍值得立法者關注。
關鍵詞:無權處分;合同;效力
1 早期立法者意圖探究
關于立法者選擇將乘人之危與顯失公平分別予以規定的考量,從《民法通則》主要起草人佟柔教授的意見中可窺之一二:首先,乘人之危的法律后果并不當然包含著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失衡。乘人之危有時并不產生顯失公平的結果。次之,顯失公平僅僅體現純粹利益失衡,因此法律對其作出否定性評價的原因在于內容的不適當。而乘人之危的評價基礎是采取違法手段造成表意人意思表示“不真實”。因此,乘人之危與欺詐、脅迫同為導致意思表示“不真實”的原因,既然欺詐、脅迫都不要求顯失公平的結果,乘人之危也無需具備此要件。又次之,乘人之危并不能由脅迫包容評價,原因在于困境產生的原因不同,后者是行為人積極創設,而前者只是對現有的困境加以利用[1]。關于立法者意圖,也有學者做出如下推測:在導致顯失公平的各種原因中,乘人之危的主觀惡性是最大的,基于對乘人之危的違法性以及民法的“制裁功能”的強調,立法者不能容忍將意思表示不真實的行為一律規定為相對無效的安排,因此,必須將乘人之危從暴利行為中分離出來[2]。
筆者認為,立法者上述考量的科學性值得進一步探究:首先,將顯示公平界定為權利義務的平衡過于狹隘。雖然現今實證法上對于顯失公平概念的解釋均如此界定,如《民法總則》第六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公平原則,合理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但如此界定是否合理,其實仍存在疑問——若是民法強調對于公平的保護,又何必將之局限于雙方權利義務的不對等,只要一方利益的嚴重損害超出合理限度,即使另一方為因此受有利益,也可徑行認定為“不公平”。其次,乘人之危并不會導致表意人意思表示的不真實,處于危難情景下的受損方明確的知道自己內心所想以及所表達的內容,其僅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自由”。又次,雖然在實踐中對顯失公平的認定只能依靠于合同內容,但由于缺乏主觀要件的顯失公平只是一種假想的不公,一律認定為絕對或相對無效事由反而侵犯了民事主體間的意思自治。再次,乘人之危并未達到欺詐、脅迫的主觀惡性程度。若立法者堅持要將其作為法律行為無效的事由,則需要對客觀結果加以要求以彌補主觀惡性的不足,如采取《民通意見》第70條的做法。最后,制裁效果始終未成為過民法的追求目標。在調整市民社會關系的民法中過分強調制裁功能反倒顯得本末倒置了。
2 《民法總則》關于顯失公平之規定
《民法總則》第151條使乘人之危重歸“暴力行為”,將其規定為造成顯失公平的多種原因之一,完全改變了《民法通則》的做法。其優勢顯而易見,其一,避免了兩者區分上的困難所導致的條文選擇上的沖突。其二,將法律效果規定為可撤銷更符合意思自決原則。其三,符合世界立法的潮流。所以,筆者認為,《民法總則》關于乘人之危與顯示公平的制度重構是一種合理地選擇。下文將結合法、德兩國關于合同損害制度以及暴利行為的規定,分別對顯失公平以及乘人之危制度的基本問題予以分析,并對于現行法律規定可能存在的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3 我國單純采用暴利行為存在的問題
《德國民法典》138條對意大利、瑞士、我國臺灣地區乃至如今的大陸均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甚至有學者指出,暴利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于《法國民法典》1674條的解釋方法[3]。但我國《民法總則》如此繼受是否還存在一定不足?筆者認為,仍存在著一定的探討空間。
首先,佛魯爾等學者指出,德國關于暴利行為的規定實際上只是咬文嚼字的游戲。因為,要求去證明相對方的主觀心理無疑是對受害方的沉重負擔。因此,主觀要件的規定使暴利行為條款適用率大大降低。司法實踐的確印證了“佛魯爾”的說法。從青海昆玉實業投資公司與福果典當公司合同糾紛按的判決[4]可窺之一二,該案件二審判決認定由于昆玉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證據證明其存在“不得已而選擇”的情況,亦未能證明福果公司存在乘人之危的事實,因此合同可撤銷的主張不予支持。由于要求原告證明自己或對方的主觀狀態的標準過于嚴苛,在實踐中一般難以做到,所以,法院對該類案件也就習慣性均以“不能證明別無選擇”為由不予支持受害人主張。這顯然不利于對原告合法權益的保護。鑒于此,如何降低受害人的證明責任成為法院關注的重點。《德國民法典》138條的第1款使該目的存在實現的可能。德國將暴利行為當作違反善良風俗的特別適用情形。則在無法完全證明主觀要件時,只要能夠證明客觀的不平衡結果已達到嚴重程度,則可降低對主觀的證明要求,直接適用第一款“違背公序良俗的,無效”的規定,此時,第1款與第2款產生了相同的效果,因此又被稱為“類似暴利的交易”或主觀要素的弱化。但應當特別注意的是,此時仍應要求行為人具有應受指責的想法。因為若完全虛化主觀要件,只根據客觀的不均衡為由主張違反公序良俗,實質擴大了138條的適用范圍,使法律對顯失公平的認定回歸到“客觀解釋理論”上去,此種擴大解釋是違背立法原意的。因此,筆者并不認同“138條第2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其意義”的觀點。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審判實踐的豐富,法國的合同損害制度與德國的暴利行為呈現出交融的趨勢,主觀要素的彈性化使得暴利制度進一步的向前發展。
回到我國的立法。鑒于法、德兩國的審判經驗,法院在運用《民法總則》151條時也將面臨著如此困境,對此應如何解決?朱廣新老師以及梁慧星老師曾提到可通過解釋使我國的乘人之危使其基本符合“暴利行為”的構成要件,再保留顯失公平條款作為“類似暴利的交易”,解決主觀要件難以證明的難題。從結果上看,《民法總則》基本實現了他們的第一個構想——建立了暴利行為制度,卻未保留獨立的顯失公平條款。而且,《合同法》54條隨總則變更內容是完全有理由相信的。因此,筆者認為,期待在立法層面重新規定獨立的顯失公平條款的可能性不大,并且,由于法律效果的限制,我們不能借鑒德國的思路,通過解釋基本原則,使“類似暴力的交易”被納入到基本原則的調整范圍。所以,在司法實踐中如何解決主觀要件難證明的問題以及《民法總則》151條會產生多大的效果還值得立法者關注。
注釋
[1]參見佟柔主編:《中國民法學·民法總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41頁
[2]尹田.《乘人之危與顯失公平行為的性質及立法安排》,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9年卷2。
[3]朱廣新.《合同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26-237頁
[4]源自裁判文書網,最高法民終234號。
參考文獻
[1]尹田.《法國現代合同法》[M].法律出版社.1995
[2]尹田.《乘人之危與顯失公平的性質及其立法安排》[J].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9
[3]曾大鵬.《論顯失公平的構成要件與體系定位》[J].法學.2011.
[4]朱廣新.《合同法總論》[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
霍婷,南昌大學法學院本科在讀,研究方向: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