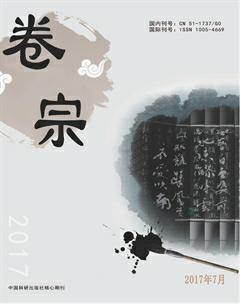淺說清代的平民訴訟問題
摘 要:清代在地方實行省、府、州縣三級行政管理制度,司法職能也主要以三級政府為依托。州縣作為行政機構(gòu)的最低一級,其對地方的管理起著重要的作用,一縣的長官被稱為“親民之官”。但是縣官是否真的親民還是有待商榷的,事實上除非迫不得已百姓也絕不輕易去縣衙擊鼓鳴冤。
關鍵詞:清代官府;解決糾紛;平民訴訟;官府受訟
1 清代地方官府
在清代的地方上,縣府是總管行政、司法的部門。幾乎所有的縣府都有基本相同的職官配置:知縣、縣丞各一人,主簿無定員,典吏一人,其他另有書吏、差役不定。其中知縣是縣府的最高長官,是正七品官員,知縣一職雖位不高、權(quán)不大,可是卻起著非常大的作用。他的主要職能是:維護當?shù)厣鐣伟病Π傩諏嵤┙袒捌辗ā⑷珯?quán)處理民事訴訟、擬律并上報刑事案件、監(jiān)禁與遞解犯人、管束在配犯人。可以說知縣集行政、公、檢、法大權(quán)于一身,所以“雖曰國非可以一人興也,非可以一人亡也,而其所興亡必自于縣令”[1]。清朝統(tǒng)治者對地方官員的選任以科舉為主,兼有捐納、恩蔭、貢生、行伍旗人等。這些人大多未曾涉世,是一向潛心于八股文的科舉人才,他們既沒有留意過律例,更無實踐的本領,甚至一批捐納為官者,更是以斂財為主要目的。雖然統(tǒng)治階級很注重培訓、歷練預備縣官,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這些預備官員卻很難達到他們所預期的效果。
2 平民如何解決糾紛
黎民百姓之間若是有了糾紛也是有一些自己的解決方法的。居住在同一村莊的人大多是同姓宗族,很多都有著親緣關系。每個宗族都會選出一個識字、有威望的男性家長作為族長。族長對本族的人有絕對的權(quán)威,雖不像帝王那樣擁有生殺予奪大權(quán),但卻是可以管理一村的各種重大的事務。比如家族的祭祀、土地的變更、晚輩的婚姻、讀書等都由族長定奪。“族眾有爭競者,必先鳴戶尊、房長處理,不得遽興訟端。倘有倚分逼挾恃符欺弱及遇事挑唆者,除戶長稟首外,家規(guī)懲治”[2]。所以平民一旦發(fā)生了糾紛,他們首先找到的是本族的族長或者其他的有威望的人,來作為中人調(diào)解,以解決存在的問題。等到事情和平解決后,糾紛兩邊人家中理虧的一方,或者由雙方共同出資承辦酒席款待中人,以示感激。這樣的方法比去縣衙打官司更省錢、更快捷,處理的結(jié)果也相對公正。而官府也承認本族、本村內(nèi)部的這種解決問題方式。在清代的司法實踐上,普遍的方式是首先依照習俗處理糾紛,如若遇到的糾紛傳統(tǒng)方式難以解決才會由官府進行司法審判。
另外特別要討論到的是縣城居住的手工業(yè)者和商人也是不愿意觸碰官司的群體。清代從事同樣手工藝工作者或是經(jīng)營相同生意的商人他們會組成行會或商會,一旦遇到糾紛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找自己所在的行會或商會,由其負責人出面調(diào)解。如果行會或商會的成員被人誣陷到官府,組織也會出面對其進行保護。行會或商會關于訴訟相應的也有自己的規(guī)章,大多要求是內(nèi)部人員出現(xiàn)糾紛不得擅自報官。有一個行會的章程這樣說到:“各位同仁一致認為,倘若彼此有錢財糾紛,應提交行會集議仲裁解決,為達成令各方滿意的解決方案,應竭盡全力。如果無法達成諒解,才可以告官;若有原告徑行告官,并未事先提交行會,他要受到大家一致斥責,以后他再有任何事情征求行會意見,均會被駁回,不予受理”[3]。之所以有如此規(guī)定或許是因為那些實力較強的成員欲意把持行會,如若所謂的丑事一旦被曝光,很可能會遭到衙門不可預料的某些干涉;也或許是組織的領導者擔心內(nèi)部團結(jié)會遭到破壞,假使任由組織成員對簿公堂,顯然訴訟雙方易結(jié)下仇怨;另有可能便是行會商會首領畏懼同仁因?qū)ν馊藷o故挑起訴訟而損壞整個行會商會的名聲進而會破壞本身在行業(yè)中的影響力。
3 平民不喜訟的原因
諺云:“衙門六扇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非謂官之必貪,吏之必墨也。一詞準理,差役到家則有饋贈之資;探信入城則有舟車之費;及示審有期,而訟師、詞證以及關切之親朋相率而前,無不取給于具呈之人;或?qū)徠诟鼡Q更換,則費將重出。其他差房陋規(guī)明目不一,有官法之所不能禁者;索詐之贓,又無論已。……如鄉(xiāng)民有田四十畝,夫耕婦織可給數(shù)口,一訟之累,費錢三千文,便需假子錢以濟。不二年,必至鬻田,鬻一畝則少一畝之入,輾轉(zhuǎn)借售,不七八年而無以為生。其貧在七八年之后,而致貧之故實在準詞之初,故事非急切,宜批示開導,不宜傳訊差提……少喚一人即少累一人。堂上一點朱,民間千點血,下筆時多費一刻之心,涉訟者已受無窮之惠,故幕中之存心,以省事為上”[4]。這是汪輝祖從幕友角度出發(fā),就詞訟對百姓的危害說的一段話。重點主要針對自耕農(nóng)而言,對一開始的訴訟費用還有能力承擔,其貧只在“七八年之后”。而對于收入更低的半自耕農(nóng)、佃客、雇工等平民來說,與人發(fā)生糾紛,就不得不考慮無底的訴訟費用而自動或經(jīng)本村的大家長調(diào)解息訟了。“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為生。如州縣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稱好官。”[5]這是康熙皇帝在1709年給河南巡撫(鹿佑)的上諭中說的,表明了皇帝對州縣官員貪取的態(tài)度。朝廷是默認縣官對百姓的盤剝的,縣官只要把該交的稅錢都如數(shù)上交國家,國家對于他們的附加稅是不予理會的,這樣就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負擔。
平民百姓不喜訟事,政府官員有的也不愿意受理案件。因為當時評判基層官員好壞的標準有時甚至不需要考察其業(yè)績,只要官員能有效維護地方的穩(wěn)定就可順利升遷。而官員一旦錯判了案件,就會承擔被罷免甚至被砍頭的風險。所以很多時候案件都會被堆積起來,面對如此情形百姓怎會還有請求官府解決自己問題的想法呢?“族中有口角小忿及田土差役賬目等項,必須先經(jīng)投訴族眾剖斷是非,不得經(jīng)往府縣訟告滋蔓。[6]”這種族規(guī)與國法的基本思想和作用都是一致的,違國法即違家規(guī)。《大清律例》專門引入“族長”的司法權(quán)限。執(zhí)法者也認為“各祠既有族長、房長,莫若官給牌照,假以事權(quán),專司化導約束……子弟不法,輕則治以家法,重則稟官究處。”[7]官府對于平民訴訟的拒絕已經(jīng)表現(xiàn)得很明顯。
4 結(jié)語
“不吃毒藥,不打官司。屈死不告官,餓死不做賊。勸君莫告官,煩惱說不完。贏了官司,賠了錢。衙役見錢,蒼蠅見血。官司未見官,衙役先吃飽。官吏要走,官司未結(jié)。無冤不成獄。人死不能復生,刑傷難以復原。縣官斷案緣故多,十有八九人不知。……”[8]這些諺語很清楚的表達了布衣蒼生對于訟事的立場。知縣們的目的達到了,省去了諸多的煩憂。但是官員的這種畸形的思考方式必定是不能長久的,滿清官員的積弊已久,他們常常做著迷夢,以為自己的生活可以一直在無為中度過,直到列強的堅船利炮一次一次的打開了國門,直到太平天國農(nóng)民起義,直到溥儀的退位……。他們拒絕了百姓,也失去了民心。
參考文獻
[1]《皇朝經(jīng)世文編》卷二一,張望《讀史縣令筏》
[2]安徽桐城《祝氏宗譜》卷一
[3] (英)S.斯普林克,清代法制導論—從社會學角度加以分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頁
[4]汪輝祖,《佐治要言.省事》
[5] (英)S.斯普林克,清代法制導論—從社會學角度加以分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頁
[6]江西南昌《魏氏宗譜》卷一一
[7] 《清史資料》第三輯,第216頁,中華書局,1982年
[8] (英)S.斯普林克,清代法制導論—從社會學角度加以分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頁
作者簡介
王吉娜(1993-),女,漢族,河南駐馬店市人,河南大學歷,中國近代史,2016級碩士在讀,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