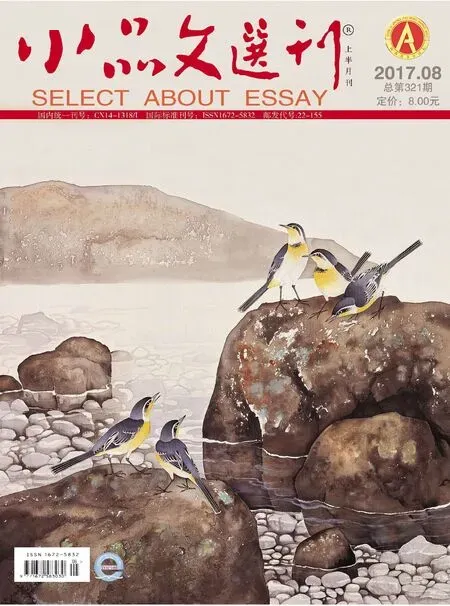小提琴
□阮文生
小提琴
□阮文生

我是上了大學之后才見到小提琴的。藝術系的“藝術家”們在樓房之間的草地里練琴,“葫蘆瓢”里的聲音好像躲得很深,被一下一下拉出來后,就非常燦爛。我剛從鄉下來,沒聽過這么新鮮的聲音。陽光和空氣如從中過濾了一般,讓早晨更加清新了。“藝術家”們偏著頭,下巴和肩膀夾住琴托,勢頭有點左傾,手往上一托,就穩住了境界。好比神仙吹了口氣,繞一繞,就成青山白云。真是美極了!特別是如虎皮樣的琴背,道道斑紋簡直是從音符里跳蕩出來一樣迷人。從那時起,我就喜歡上了小提琴。
雖然我們那里是鄉下,但喜歡藝術的人還真夠密集。我家對門的理發師大B會拉胡琴,他和瓦壟的兩位主胡一起坐臺上,胡琴在翹起的二郎腿上被拉得昏天黑地,臺下是黑壓壓的人群。《紅燈記》《沙家浜》的旋律在汽燈的照耀下閃閃發亮,胡琴的鋼絲弦也在閃閃發亮。隔壁是師范生老W,他花不少錢買了把發紅的彎頭胡琴,拉《病中吟》,后來整夜整夜地拉《江河水》,為考上海音樂學院加緊練習。夜晚琴聲突出,隔條馬路也沒減輕多少,也許是吵了大B睡覺,大B沒好氣地說:要是老W能考取上音,我到馬路上倒著爬!
有一天,大B放下老舊的胡琴,我就胡亂地操起來。沒幾天我能拉革命歌曲,后來拉厭了也拉《病中吟》。不遠的中學里有個宋宗謙,胡琴到了他手里,立馬精神起來,一出聲就不一樣,總有一大圈人圍著看。《二泉映月》拉到興頭上,他會歪起嘴巴聳動著面部肌肉,頭對著我們一點一點的。鄉下的胡琴算是給我打了點底子,見到藝術系的“藝術家”們,我就不能自已了。系里一把屁股有點裂的小提琴到了我手里,我喜不自禁。有人說我是將胡琴放到肩膀上拉,管他呢,我喜歡!后來藝術系的人給我介紹了拉小提琴的蔣克水。為了拜師我從家里帶了瓶香油給他。那時,香油可是緊俏的東西!蔣克水高興,他示范,指導我拉卡塞和帕格尼尼。我曉得了正規訓練是硬道理。后來,開門辦學到了池州,我帶著小提琴住在池州師范,老鄉給我介紹了池州地區文工團的指揮周更生,他是姜壩人,也是老鄉。他戴著黑框眼鏡,腋下夾了個譜架送到池師,看我拉了會兒小提琴,沒作聲,繼續抽他的煙。一堆堆的青煙在他頭上,緩緩地往高飄。
我們每天去農機廠,在成堆的鋼鐵里轉來轉去。有一天,同學王會華用搖把搖機器,手沒及時撒開,飛轉的搖把將她像一團泥巴砸在地上……這個印象真深。抽空,我還是去拉拉卡塞吧!
有一天廣播里出現前所未有的沉重口氣。聽后,大家呆了,是毛主席逝世了。我們排隊低頭站在寬大的池州體育場,九月的太陽熱辣辣的,知了還在樹上叫。我們參加浩大的悼念儀式。一個女同學昏倒在地。在雜亂的鋼鐵堆,在彎曲的街巷,在巨大的恍惚里,哀樂不斷地挖掘淚水,推動著悲情。哀樂多了,我就記住了旋律,能用口哨將它吹出來。好幾天沒拉琴了,手有些癢,但有一個禮拜不許文娛活動的規定。到了第四天,我偷偷跑到池師長滿雜草的操場,拉起哀樂。我簡直成了一個廣播,在夜晚里清晰又孤獨。我在演練一首叫哀樂的名曲,似乎也在演練一個悲痛。不一會兒,來了兩個人,他們有點驚異地用電筒照了照我,像是照見巨大的悲哀里出現的一個漏洞。我從漆黑的操場給帶進明亮的辦公室,成了一個被強行打斷的半吊子——半途而廢在陌生的訊問里。
毛主席逝世了,你怎么還拉小提琴?我在拉哀樂,在悼念他老人家。其中一個人白了我一眼。是的,他們印象中的哀樂不是這樣子。又來了兩個人,我差不多陷入重圍,但沒有亂套,我之前早就給自己定了原則:今夜除了哀樂,別的都不拉。怪誰呢,我的愛好和大地里的悲哀一樣強烈而持久。他們應該是老師,我用鎮靜抵抗帶著熱度的疑問。局面還算過得去,小提琴在桌上發出暗紅的光芒,屁股上的裂縫早被我熬的膠水給補起。我說,哀樂不是娛樂,我也沒有一點娛樂的意思。他們交換了下臉色,看得出來,是在回憶:無邊的黑暗里,的確沒有一點歡樂的跡象,小提琴就像圓圓的操場,不固守一個方向,也不全是歡樂的證據。他們再次打量我,我很簡單,簡單得有些單薄,面部除了一副眼鏡再也沒有多余的東西。作為老師,應該一眼就能看透一個心里只有喜歡、還沒有生出仇恨的人。一行簡單的練習曲,藏不了什么隱晦甚至蠢蠢欲動的惡意。
長久的燈火里,這點事情,生不出新東西了。老師們當然不認為自己在反對自發的悼念,也許那時,東方的大悲哀和西方的小提琴搞到一起,難免糾纏不清。我懵懵懂懂,后來才意識到其實我的這個行為不比飛旋的搖把安全多少。
辦公室的燈火越來越亮,窗外的蟲鳴長一聲短一聲,一些表情從生硬到疲軟,爭辯也從激烈歸于平緩。“算了算了,夜夠深了,明天還有明天的事,不要都在這里沒事找事,睡覺去吧!”
幾年之后,我以一個老師的身份前來池州師范師,參加高中數理化暑期培訓班。搞會務的人盯住我:“你是那個拉小提琴的人!”而他就曾是那個夜晚的忠實捍衛者。其他人不明白這親熱中的緣由,我們也不說明,只是笑。是的是的,我們早就是熟人了。
選自《朝花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