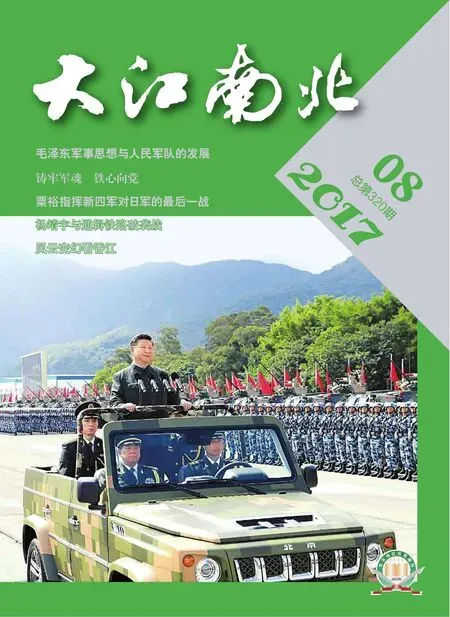戰斗在四明山的日子
錢逸華
戰斗在四明山的日子
錢逸華
我今年88周歲,日前偶然翻出一張珍藏了70多年的一寸黑白照片,那是1945年5月8日我在浙東抗日軍政干校時,在余姚縣梁弄鎮照相館拍攝的,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照相,相片中我穿著新四軍軍裝,手持步槍,一個標準的抗日小戰士形象。捧著老照片,打開了我塵封的記憶,好像又回到了在四明山那段火紅的抗戰歲月中……
1942年,我的家被日本鬼子燒沒了。當年末,在中共地下黨員帶領下,我投奔四明山何克希司令、譚啟龍政委領導的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
精干的修械所
我參軍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位于白龍潭小村的修械所當練習生。修械所和后方機關的被服廠、印刷廠、醫院等單位不適合頻繁的行動,只得分散隱蔽在四明山腹地。全所從所長、指導員到技工、練習生,總共不到30人。所里骨干力量是鉗工,當地人稱他們是“銅匠師傅”,都是從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動員來的產業工人,覺悟高、干勁足。兩個和我一樣十四五歲的練習生,被同志們稱為“小鬼”,擔負生烘爐、拉風箱、整理工具、鋸銼毛坯,打菜打飯等雜活。
修械所平時的工作,就是修理前方送來已損壞的槍支,以修配步槍的零部件為主,如折斷的撞針、扳機、扒子鉤(退出槍膛內子彈或彈殼的鉤子),或失靈的保險、斷裂的木質槍托等。
1943年4月,我軍打了一個大勝仗,奪取了敵軍占領的重鎮——梁弄。前方送來許多繳獲的和我部自己需要修理的武器,有步槍、手槍、輕機槍,也有重機槍。為了讓這些武器早日回到戰士手中,我們加緊工作。那時山里沒有電,每天早起早干,除去吃飯一點時間,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因為沒有車床,要修換的零部件,全靠烘爐打鐵,制成毛坯,然后用手鋸、鏟刀、銼刀一點一點加工而成,很消耗體力。大家雖然辛苦,可是因為前方打了勝仗,心里高興,所以干活的勁頭更足了。
要修的槍械多了,加工零部件所需的金屬材料消耗得也多,眼看要供應不上,山溝里又沒處買、沒處找,怎么辦?指導員徐言遜發動大家出主意、想辦法解決困難。這時,一位工人師傅說:“咱們唱的歌中,不是說‘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嗎?咱們也來它一個沒有鋼、沒有鐵,去向敵人要。”經他的啟發,大家想出一個好辦法,就是去破壞幾十公里外的敵人據點——鄞江橋(地名)的鐵欄桿,這樣,既給敵人“添了亂”,又解決了金屬材料來源,一舉兩得。于是,所里組織了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的身強力壯的小分隊,人人拿著手鋸,急行軍到敵人據點外潛伏起來,天黑后,在夜幕掩護下,除擔任警戒的人以外,全部上橋,分工合作,鋸斷橋上的鐵柱、鐵欄。就這樣,人不知鬼不覺地搶回來一批寶貴的金屬物資,滿足了加工零部件的需要。
新建的榴彈廠
1943年夏天,前方部隊戰區逐漸擴大、戰斗也更頻繁,所以需要更多的武器彈藥裝備部隊,尤其是適用于近戰和殺傷力較大的手榴彈。在這種情形下,在名叫鄭天龍的小山村,縱隊后勤部以修械所為基礎新建了一座榴彈廠。我被抽調到榴彈廠當練習生。
榴彈廠“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廠內有鑄造彈體的翻砂小組,有配制炸藥的裝配小組,有鏇制手榴彈木柄的木鏇小組(鏇床沒有電力,靠人用腳踩踏),我被安排在制造雷管的小組。做雷管必須用銅皮,建廠初期,一時搞不到這種貴重的紫銅金屬材料,怎么辦?我們有辦法!我們從民間市場上收集流通的銅幣來替代,沒有沖壓機床,就用鐵榔頭一錘一錘把銅幣砸成銅皮,再裁剪成長方形,卷起來焊成雷管,困難就這樣被我們一個一個克服了。
第一批木柄手榴彈制造出來了。要判斷它的爆炸力和彈體炸裂后彈片的大小,還需經過試驗。只有彈片大小適中,才能具有更大的殺傷力。最初試驗,手榴彈只炸成幾大塊,殺傷面積不大。以后,經過對彈體外形的改造、彈壁厚度的調整和彈藥比例的重新配制,才生產出合格的手榴彈,源源不斷地供應前方。當然爆炸試驗是不能在山林野地里進行的,因為山谷中回聲很大,如果被敵人偵聽到,就會招來襲擊和破壞。所以,爆炸試驗就要選在遠離工廠的山洞里進行。在山洞中還要挖小洞,試驗彈扔進小洞爆炸后,再將洞壁中的殘土挖出來,清查土中的彈片大小,確定手榴彈的威力。
后方機關工作人員勞動強度大,生活十分艱苦。沒有工資薪金,每月發一點津貼,也只夠買幾包煙卷,每月發一包牙粉、半塊肥皂,因為無處洗澡,沒有多余衣服洗換,冬天幾乎人人身上生虱子(大伙戲稱革命蟲)。每天伙食兩稀一干,就飯的菜常是蠶豆、咸菜、蘿卜干,一個月也難得吃一次咸魚或鮮肉。山里竹筍倒是很多,可是食用油很缺,只能咸水煮了吃,同志們開玩笑說:“本來腸子就沒多少油,都叫竹筍刮沒了。”物質生活雖艱苦,但是政治學習和文化生活很活躍。我們每周上兩次政治課,學唱抗戰歌曲一首接一首,人人具有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一心跟著共產黨打鬼子救中國。
頑強的印刷廠
到1943年6月,隨著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浙東區黨委在四明山腹地杜徐岙的山上,選擇一處只有十來戶居民的泥屋小村,建起了印刷廠,我被選調去學習排字。
建廠初期,小村唯一的二層樓,是邦土伯伯家,他把樓上讓出來給我們作排字車間,樓下安一臺用腳踩的四開印刷機和一臺圓盤機。7月7日為紀念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六周年而印刷第一份宣傳品之后,原來的《時事簡訊》也由油印報紙變為鉛印報紙了。然而,好景不長,1944年初春,國民黨部隊以顧祝同為首的3萬多大軍勾結日偽,向四明山根據地發起第二次“圍剿”。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我軍主力按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的指示撤出四明山,渡過姚江實行分散游擊。我們印刷廠也奉命掩埋機器設備,人員轉移到“三北”(余姚、慈溪、鎮海三縣的姚江以北)地區,暫時編入慈北縣委的地方武裝中。
同年4月,縱隊政治部為加強對部隊的宣傳教育,要求印刷廠出版《戰斗報》,于是工廠派人潛回四明山,挖出已掩埋的一部分鉛字和圓盤機,在“三北”茅山的石步村印刷《戰斗報》。這個地區山不高林不密,隱蔽比較困難。十幾個人的小小印刷廠,工作、生活都擠在不大的半地下室的窩棚里,光線陰暗,夏季白天室內悶熱,晚上蚊蟲叮咬,有時晚上下大雨,棚子漏雨,無法睡覺,只得撐著雨傘,坐在鋪板上打盹。排字時有鉛字不夠用的情況,因為沒有鑄字機,就用刀子刻;沒有切紙機,就用菜刀切。經過大家努力克服各種困難,八開四版的鉛印《戰斗報》,如期出版發往部隊。與此同時,還印刷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內部讀物。
10月的一天,日本鬼子帶偽軍來山區“掃蕩”,由于有當地百姓冒著危險跑來向我們報信,我們及時分散隱蔽到山上。危急時刻敵人搜索到距離我們只有一百多米的地方,幸好沒有發現我們,印刷廠也躲過一劫。
四明山反頑自衛戰役取得勝利后,印刷廠遷回杜徐岙山上,新搭建了幾處草棚,恢復生產。隨著形勢好轉,工廠添設備進人員,以鉛印的四開四版《新浙東報》取代《時事簡訊》,每周三期,發行量達到1500份。《戰斗報》也同時繼續出版,每周一期印發500份。
1945年4月,我被選調進入浙東抗日軍政干校去學習前后,印刷廠取得了很大發展,不但負責印刷報紙、文件、毛主席和劉少奇著作,還印刷軍用地圖、布告、票證等。直到1945年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我新四軍浙東縱隊奉黨中央命令撤離浙東,印刷廠也完成了歷史使命。
(編輯 陶麗)

位于余姚梁弄古鎮的四明山革命烈士事跡陳列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