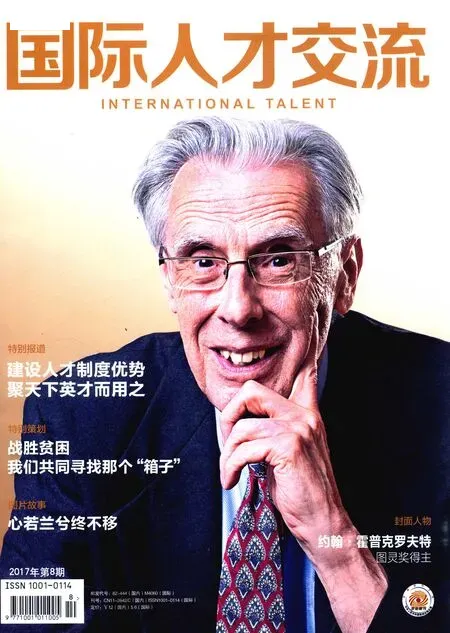戰勝貧困,我們共同尋找那個“箱子”
文/本刊記者 左娜
特別策劃IN FOCUS
戰勝貧困,我們共同尋找那個“箱子”
文/本刊記者 左娜

為幫助雪域高原無電區的孩子們解決沒電帶來的困境,中華環保基金會2013年6月啟動了首個公募項目“螢火行動”。圖為青海省索加鄉寄宿小學女學生永吉巴毛領到燈后,在宿舍的被窩里讀書學習(攝影:新華社記者 何俊昌)
新浪微博上曾出現過一張引發國民大討論的漫畫。
三位場外觀眾都想觀看球賽,每人腳下都墊著箱子。在左邊的高個子眼里,球場一覽無余,中間的女生剛剛好,而右邊的小朋友即使站在箱子上也什么都看不到。在提名為“正義”的圖畫里,高個子腳下的箱子被墊在了小朋友的腳下,這下無論高矮,三人都可以在同一水平線上看球了。
在中國,一場關于扶貧脫貧的攻堅戰正是對“正義”的精準注解。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絕不能讓一個少數民族、一個地區掉隊,要讓13億中國人民共享全面小康的成果。”黨的十八大以來,貧困人口脫貧一直是習近平總書記最關心的工作之一。每到一個地方調研,他總不忘到貧困村、貧困戶了解情況,有時還專門到貧困縣走訪。
在中國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今天,黨和政府將打贏脫貧攻堅戰作為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重大舉措,這就是要為那些掙扎在溫飽線上的同胞,那些深陷貧困、疾病、失學中的同胞再墊上一只“箱子”,讓他們和其他中國人一起欣賞“小康線”內的美麗風景。
2016年12月27日,中國社科院和國務院扶貧辦聯合編撰的《中國扶貧開發報告2016》公布了一個振奮人心的數字:在2016年,中國有超過1000萬人告別貧困。
這場與貧困的鏖戰,中國已經堅守了30多年。
我國從1986年就啟動了大規模減貧計劃,2013—2016年,我國貧困人口每年減少超過1000萬人,累計脫貧5564萬人,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總量;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年底的4.5%。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亮麗成績單的背后,是千萬困難百姓喜迎美好未來的笑臉。未來,中國向貧困下了決戰書。2016年,我國貧困人口還有4300多萬,計劃到2020年實現現存貧困人口,特別是深度貧困地區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
在這場世界范圍內的脫貧戰爭中,中國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智慧和耀眼的成就贏得世界點贊。
聯合國《2015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顯示,中國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61%,下降到2014年的4.2%,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中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
《紐約時報》評價,極端貧困人口的大幅減少主要應歸功于中國取得的經濟進步。《赫芬頓郵報》則指出,世界減貧成績“最大的功勞來自中國。中國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顯著的成績,歸功于經濟發展,離不開政府在改革方面作出的努力”。
在戰勝貧困的道路上,有這么一批外國專家、國際人才,選擇了與中國同行,把自己的事業扎根在了中國。
在扶貧第一線,他們有的是見證者,把中國的扶貧故事講述給世界;有的是實踐者,用專業知識技術為需要幫助的人找到了“致富之路”;有的是創新者,把最新的經驗、模式帶到了前線,打破了貧困的惡性循環……
“扶貧始終是我最關注的領域之一。”《中國日報》的美籍記者聶子瑞(Erik Nillson)是2016年中國政府友誼獎獲得者。在華的十余年間,他一直工作在新聞采編第一線,走遍了中國34個省級行政區,他多次深入汶川、玉樹地震災區,在玉樹還發起了一個志愿者扶貧組織。李克強總理稱贊他“不僅用筆、用嘴介紹中國,也在用行動為中國的發展做貢獻”。“我經常到中國的偏遠地區采訪,行程踏遍了絕大多數的省份。我親眼目睹、親身經歷了中國如何治理貧困,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卻不為外界熟知的成就。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像中國一樣,在如此短的時間里讓如此多的人脫離貧困,這理應成為回答‘何為中國’的最佳答案之一。” 2017年1月20日,聶子瑞在李克強總理與外國專家的座談會中如是說。未來,他的目標是利用新媒體的力量,更好地向世界講述中國的扶貧故事。
曾經“苦甲天下”的甘肅定西是精準扶貧的主戰場之一,但這里卻讓加拿大植物病害防治專家亞仕都博士一見傾心。從1997年開始,他在十年間幾乎每年夏天都要到定西進行技術指導與培訓。在種植土豆的田間地頭,人們經常看到他活躍的身影,教農業技術人員和廣大種植戶識別土豆病蟲害、控制溫度和濕度,以及如何使用種薯等,據不完全統計,經他專門培訓的當地科研推廣人員和農業技術人員達500多人次。在他的幫助下,定西建立了甘肅省第一家馬鈴薯病毒檢測實驗室,引進了脫毒種薯快繁技術,解決了許多關鍵性的技術難題,如營養液配方、栽培基質配方、質量檢測標準……將定西百姓曾經的“救命薯”“溫飽薯”,打造成定西的“脫貧薯”“致富薯”。2007年,亞仕都因對定西土豆產業的發展所做的巨大貢獻榮獲了中國政府友誼獎。

喀什市乃則爾巴格鎮的海仁古麗居瑪在鎮上婦女創業脫貧基地的縫紉企業里裁剪布料(攝影:新華社記者 陳寂)
“我是失明了,但我可以向世界證明,我并不因此而失去價值。”德國人薩布瑞亞·田貝肯(Sabriye Tenberken)是一位盲人,也是西藏盲童學校的創始人,在西藏生活近20年,從最初騎著馬走170公里找到6個盲童,創立“盲人無國界”(Braille Without Borders,以下簡稱BWB),到今天在西藏、印度開設若干家覆蓋幼兒、學前和技能教育的綜合機構,薩布瑞亞和丈夫保羅帶領團隊,幫助盲童獲得生活的知識、技能。截至2013年年末,BWB在西藏幫助并培養了約200名盲人,其中約150人從拉薩BWB盲文預備學校畢業,60余人在日喀則的農場學習勞動技能和就業培訓。
而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美國男孩兒 Sam和Andrew則為中國鄉村的孩子們賣起公益眼鏡。早在2010年,兩個美國男孩兒來到云南偏遠山區支教,他們發現在落后的山區根本沒有條件讓孩子們去醫院定期檢查視力,家長們還存有“戴了眼鏡就再也摘不掉了”之類的錯誤觀點,很多孩子的近視越來越嚴重,嚴重影響學習效果和學習興趣,甚至導致失學。2012年,他們創辦了“點亮眼睛”公益組織,為貧困地區的農村學生提供免費的視力檢查和健康教育,免費配制近視眼鏡。截至2016年的4年里已經為超過11萬的云南貧困學生進行免費的視力檢查,無償為有需要的學生配制1.6萬副眼鏡。為了幫助更多的農村孩子獲得平等的受教育機會,Sam還創立公益潮牌眼鏡Mantra,并引入美國成熟的“買一捐一”的創新公益模式。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
中國首家孤獨癥兒童康復機構“星星雨”的志愿者、法國著名精神分析家米歇爾·吉布爾,創建“彩線云南”扶貧工程的丹麥人胡蘭君,創建牦牛絨手工品牌Norlha為藏區打開自立謀生方式的美國人益西德成,在中國公益行醫20余年,成為3000位鄉村醫生“導師”的非洲馬里人迪亞拉…… 這些人被稱為“老外”,但卻把公益踏踏實實地做在了中國。他們用自己的行動參與到扶貧中,為中國各個地區、不同的貧困群體帶來了“國際經驗”,用自己的方式和中國同行行進在戰勝貧困的路上。
《中國日報》高級記者聶子瑞深入扶貧一線采訪報道的經歷,讓我們看到新媒體的力量如何幫助世界更加了解中國的扶貧成就。
美國小伙兒潘勛卓起初讓我們不解,一個前途大好的普林斯頓大學學生為何退學來到中國?在看到他創辦的“美麗中國”鄉村支教項目中那些孩子們燦爛的笑臉后,我們找到了答案。
智行基金會創始人杜聰讓我們看到了艾滋病孤兒們的堅強和希望。艾滋病帶走了這些孩子們的父母(他們的父母多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杜聰卻給他們帶去了自信和尊嚴。這位畢業于哈佛大學、曾在華爾街工作的“銀行家”,用教育和社會企業讓受艾滋病家庭遺孤有尊嚴地成長、成才。
本期特別策劃講述的這三個扶貧故事,只是滄海一粟,卻是大海洶涌澎湃、波瀾壯闊的交響樂中最美的華章。
為了尋找到那只“箱子”,他們遠道而來,與我們一起在戰勝貧困——這個全球性問題的道路上,披荊斬棘,一定會收獲更加美好的明天。

近年來,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河北省武邑縣在實施產業扶貧過程中,積極引導農民因地制宜發展韭花、油用牡丹、油葵等特色種植,圖為武邑縣清涼店村農民在地里采摘韭花(攝影:新華社記者 朱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