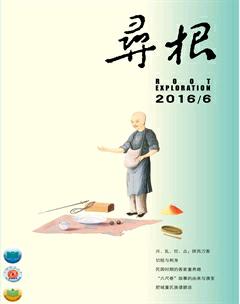切膾與刺身
周朝暉
說起日本菜,人們就想到被叫作“刺身”的生魚片。日本人嗜生,舉世皆知,讀音“sashimi”也被收入英語字典。韓國人不服,說日本的“刺身”源自他們高麗王朝時代的“膾”(hoe),一副欲與日本刺身比高,爭專利申報文化遺產的架勢。其實,“刺身”也罷,“膾”也罷,都與中國古代食俗脫不了干系。
人類在掌握用火技術之前,都經歷過茹毛飲血、活剝生吞的歷史階段。地球上很多民族和地區都有過生食魚貝、肉類的歷史,有的地區至今古風猶存,如北歐一些海洋國家,還有我國東北阿穆爾河流域乃至閩西某些村落,仍有吃魚生的習俗。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中國飲食文化史上有關生吃的食俗也是可圈可點的,不僅源遠流長,還深刻影響了周邊的國家。
一部日本古代史,幾乎大半是中日交流史。曾在北京留學數年的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為刺身尋根溯源,將食魚生的歷史推到周朝,見《詩經》中的《小雅·六月》:“飲御諸友,焦鱉膾鯉。”公元前823年,周宣王肱股尹吉甫北征勝利歸來,大開盛宴,用燉甲魚和鯉膾與朋友痛飲歡慶,膾在周朝是一種高端佳肴。何謂膾?杜詩邵注:“膾,即今之魚生,肉生。”膾鯉就是切得非常薄的鯉魚肉。怎么吃呢?《禮記》說:“魚膾用芥醬,春用蔥,秋用芥。”淡水魚有土腥味,配以姜、蔥、芥可以去腥味。不過這里的“芥”,并不是今天日本料理常用的芥末泥(山葵),而是用芥菜籽曬干研磨而成,氣息和辛辣度更近于柔和的洋芥末。我國古代王朝大多定都中原,黃河流域的鯉魚是最常見的食用淡水魚類,或生吃,或腌漬,都是首選食材,延續了數千年。在孔子生活的時代,食膾應該比較常見,《論語·鄉黨》有“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一說,“食”與“膾”相提并論,可見其日常性,又說“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把食膾上升到禮儀的文化高度。北魏農政學家賈思勰《齊民要術》里收了很多古代流傳在中原的食譜,其中“切膾”與“魚鲊”分別是今天日本菜中刺身與壽司的雛形。唐宋時代切膾風俗似乎更加普遍,頻頻出現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歐陽修、蘇東坡等詩人騷客的酬唱宴飲食單上,清新優雅,如詩如畫。13世紀,游牧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帶來飲食風氣的變化,但由于習俗具有一定延續性,所以并沒有馬上隨民族征服帶來的食俗變遷而消亡。元初關漢卿雜劇有一出《望江亭中秋切繪旦》,就是以切膾譜寫的傳奇故事:權貴楊衙內垂涎寡婦譚記兒的美貌,在她改嫁白士中后,百般構陷,并挾皇上勢劍金牌之威欲置白于死地。譚寡婦假扮漁婦,在望江亭上薦楊衙內以美味切膾,用美貌美味作誘餌把他灌醉,騙得金牌,最終將其扳倒,挽救夫君和愛情于險境。這說明切膾在元代還未消失。
日本美食家北大路魯山人說:中國菜在明朝達到了最高潮。但切膾食俗似乎難得一見,梁山泊一百單八將,個個生猛,大口喝酒大塊吃肉,但他們的酒桌上似乎不見生魚生肉。而到清朝,切膾就從中國人餐桌和酒肆里消失得干干凈凈了,有我國封建社會生活百科全書之稱的《紅樓夢》,不厭其煩寫了一場又一場盛宴食事,就是不見切膾的影子。1877年,晚清詩界領袖黃遵憲到日本,得以近距離觀察甚至體驗大和食俗,將生食魚膾之俗當作新鮮事記入《日本國志》:“以生魚聶而切之,以初出水潑刺者,去其皮劍,洗其血鯉,細劊之為片,紅肌白理,輕可吹起,薄如蟬翼,兩兩相比,姜芥之外具染而已,人口冰融至甘旨矣。”在黃參贊眼中,膾已是不折不扣的異域食風了。
日本的食膾起源于何時已不可考,從列島四處都有繩文時代留下的魚骨貝類殘骸推想,生魚生肉無疑也曾長期是大和民族的家常便飯,原始而古樸,猶如天地混沌初開。漫長年代之后,終于有一天仿佛得到某種啟示似的突然覺醒,而且進步神速,自成一家格局,令世人驚艷,其中一大奧秘來自中國文化的啟蒙和點化之功。
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國通”內藤湖南曾以做豆腐為例,生動闡釋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啟蒙和點化作用。按照他的說法:日本文化由來已久,很多事物的種子已經存在,好比做豆腐,用豆磨成液體的素材一直存在,經過中國文化鹵水的點化,一鍋混沌初開的豆乳才凝聚成塊。像切膾之類的食俗也是這樣,古已有之,但經過中國文化的啟示,使日本從原本混沌、模糊、庸常的既存事物找到一種規范、表達和升華的門道。作為飲食文化一環的切膾,在日本發揚光大即是中國文化影響日本文化的一個范例。
按照《后漢書·東夷列傳》的記載,公元57年,倭奴國遣使來漢都洛陽稱臣入貢,此后千年延綿不絕,迄唐為盛。對此,東洋最早國史《日本書紀》直言不諱他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遠渡汪洋前來大唐的初衷,“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從7世紀到9世紀的兩百余年,日本先后向中國派遣近二十批次遣隋使、遣唐使,大量學者、僧人居住長安求學問道,甚至在長安做官,包括切膾在內的大唐食尚東傳扶桑是可以想見的,至今不少日本人都深信刺身即由海歸遣唐使從長安帶回的。切膾在日本食文化史上的影像開始清晰起來的平安時代(8-12世紀)基本與唐宋重合,顯示了某種意味深長的淵源關系。
切膾第一次見諸日本文獻,是編撰于8世紀的正史《日本書紀》中,寫成“膾”或“繪”,分別指的是細切的動物肉類和魚類肉片,與醋等調味作料拌著食用,訓讀成“生醋”,不難看出與中原食風的相近性。8世紀一首和歌“醬醋搗蒜合鮮鯛”,歌詠大和王朝宮廷宴席上的佳肴。兩百年后,律令書《延喜式》里出現了生鯉和鯛魚切絲與姜蔥同食的記載,已是一種飲饌制度了。
“物”的影響方面,豆豉、醬油等的引入引起調味料的巨大革新,提升了切膾的美味。8世紀,日本從中國學習做豆醬的技術,豆豉成為一大生活調味料。工匠做醬時無意中從積存桶底的液體中發現了醬油。這一發現使得日本菜肴開始有了獨特的味道,切膾從此在鮮美一途一以貫之發展下來。
由于醬油的食用,切膾從薄片切成絲縷,變成大厚片如軒,“切身”之名即由此而來。但室町時代武家登場,忌諱“切身”與“切腹”“切首”的“切”,改為“刺身”,叫法因循至今。
從切膾到刺身,在日本得以一枝獨秀地發展,還與日本島國獨特的食語傳統密切相關。人類從生食到熟食,在烹飪上是一種進步。切膾在華夏中原源遠流長,但最后式微,乃至從中國人餐桌上消失,異民族征服帶來食尚變遷是一大因素,最主要的恐怕還是在衛生防疫條件落后的古代,生食尤其是以淡水魚為主的中原切膾帶來的寄生蟲疾病,使人們最終遠離這種鮮美的吃法,專在煎、炒、燉、煮、炸上下功夫,形成調和鼎鼐、五味共融的飲饌風貌。與中國不同,日本四島環海,海洋魚類十分豐富,比起淡水魚,海鮮大多生息在水溫極低的深水海域,寄生蟲和細菌相對較少。此外,某些調味作料被開發利用,如山葵芥末、蘿卜、紫蘇被作為刺身搭配,不僅增加其風味而且因為具備強大的消毒、殺菌功效,有效解決了由生食引起的食物中毒和寄生蟲危害,也使得這一傳統食尚一直被保留下來。
吃刺身不可或缺的芥末泥,日語叫山葵(wasabi),原產于日本,與西洋芥末氣息相近但辛辣刺鼻得多,具有強大的殺菌消毒之效,最早在日本是作為藥用,被供奉在皇家宮苑里。奈良明日村大和朝廷宮城遺址出土的一塊木簡,上面用墨筆寫著草藥名稱,其中有“倭佐俾二升”字樣清晰可見,據考證“倭佐俾”就是wasabi的萬葉假名讀音。日本最古草藥事典《本草和名》也是作為藥用草本,寫作“山葵”,至今通用。山葵有潔癖,對空氣、水、土壤都有很高要求,人工培植相當困難,被當作貴重草藥。17世紀初期,武士出身的望月六郎右衛門在靜岡安倍川上游人工栽培山葵獲得成功,山葵由貴重藥成為吃刺身的作料。一般的餐館上刺身會附帶一塊芥末粉和成的芥末泥,高級餐廳則上一段指根粗細的生鮮山葵,在金屬凸起板上研磨。大宮車站前的百年壽司老店“東鮨”,用鯊魚皮貼在小木板上,細細研磨,是山葵的最考究吃法。和山葵一起作為刺身搭配和作料的還有蘿卜和紫蘇葉子。蘿卜用柳葉刀削成片,細切成粉絲浸泡去除辛辣味瀝干,團成蓬松狀,墊上蒼翠的紫蘇葉,專業術語叫“妻”,就是專門和生魚片搭配,紅白翠綠相間格外養眼,不僅是審美,最主要的還是解毒殺菌。日本舉國大吃生魚,卻很少出現食物中毒事件,功勞恐怕要記在這些被當作陪襯的“妻”上。
魚類肉柔軟,切成片最見刀上功夫。杜甫詩里常見切膾的生動描寫,“無聲細下飛碎雪”意即刀工卓絕。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里就寫了善切膾、刀工一流的南孝廉能將生魚片切得“谷薄絲縷,輕可吹起”,神技近乎道,但在日本廚師行業,至今也不難見到。日本制刀技術源自大唐,但日本出產優質鋼材,加上奇巧精煉的工匠氣質,經過精心鍛造研磨,削鐵如泥,無論制刀或用刀,都后來居上,到北宋時竟返銷中國,連歐陽修都嘖嘖稱道,寫入《日本刀歌》里。歷史上,武士曾長期居于社會主流,江戶時代,每日到將軍居城或大名藩府上通勤的就有“庖丁武士”,專門負責主君的膳食,身上插的兩把刀只是身份象征,但案板上的刀工更勝一籌。也許是這一傳統,至今日本料理職人在對待刀具的虔誠與專一上也頗有武士之風。筆者曾在大宮一家百年老字號工作數年,對這種職人氣質印象深刻,店里每個廚師都有自己一個精致的“庖丁箱”,切生魚用二尺長的“柳刃庖丁”,宰殺魚貝用刀背寬厚的“出刃庖丁”,切菜用“菜庖丁”,雕刻竹葉用“花庖丁”,分得清清楚楚,自己選購,自己養護,連磨刀石也各有專用,每天打烊離店前,就在各自的操作臺前一絲不茍地磨刀,同時也是磨心,很有一種儀式感。筆者曾在日本料理達人神田川俊朗開在大阪梅田的河豚老鋪里見識過他切河豚肉片,一片片薄如蟬翼,快如雪花飄落,一片片貼在青瓷盤里,透出盤子的紋路,“運肘生風看斫膾,雪隨刀落驚飛縷”,簡直就是蘇軾筆下北宋“膾匠”神技再現,令人感嘆華夏飲食之道在扶桑傳承不衰。
在選取切膾用食材的喜好上,日本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歷程。在遙遠的古代,中國王朝大多定都于黃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哪里是王都,哪里就是中心,遠離中心的海邊只能是邊鄙,是化外蠻荒,因此,魚類以河魚為貴,海魚為賤。黃河鯉魚是魚中之王,這一觀念也影響到日本。長期以來,作為刺身原料的魚類就是鯉魚。京都曾長期作為日本首都,離大海較遠,附近滋賀縣琵琶湖盛產鮒魚,也就是鯽魚,肥大鮮美,長期供應王宮和貴胄,切膾或做成鲊,分別是今天日本刺身和壽司的雛形。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戶城開設幕府,原本荒蕪的小漁村成為另立中央的行政中樞,迅速發展成為人口超百萬的大都市。與京都不同,江戶人崇尚新鮮口味,講究“旬物”,即當季食材。江戶時代,現今皇居前的日本橋沿河岸一帶,有個日本乃至亞洲最大的“魚河岸”(海鮮批發市場),來自紀州灣、伊勢灣、瀨戶內海的新鮮魚介都在這里集散,食用海魚成為市民食桌主流。武士是日本社會中堅,本來無人過問的鰹魚因為讀音類同“勝男武士”,用其做成的刺身大受追捧,奇貨可居。鰹魚汛期未到,就有按捺不住的武士立在岸邊數著銀子癡癡地等,甚至有人典當宅邸去大快朵頤。今天刺身食材中不可或缺的金槍魚,也是江戶時代才開始進入切膾案板的。18世紀后,日本深海捕魚技術大進,鯨魚、金槍魚大豐收,開始進入江戶市民餐桌。不過當初只吃金槍魚身上清淡的“赤身”部位,脂肪堆積如雪花的肚腩沒人要,買魚時,店家附送帶回去喂貓喂狗,干粗活的人用它加醬油煮湯補充油水。二戰后,美軍占領日本,吃慣油膩的山姆大叔不欣賞自身赤身的淡泊清雅之美,到壽司店專點沒人問津的肥膩的金槍魚肚腩,世風跟著轉向,令金槍魚肚腩價格扶搖直上,成了高嶺之花。
飲食文化的流播與傳承,既有普遍性也有偶然性。“膾”“炙”人口的華夏食俗,被周邊國家的接受和傳承也各有偏向,可謂——花開五葉。日本得其“膾”,即刺身,因緣際會發揚光大成為大和“國菜”;朝鮮得其“炙”也就是燒烤,如今也是滿世界煙熏火燎大行其道。韓國歷史上也盛行過膾,今天韓菜里的“hoe”,即是“膾”的漢字音讀。據考證,膾在三國時代傳到朝鮮半島,生魚寫作“膾”,生肉作“鲙”,高麗王朝時代因為佛教被立為國教,“鲙”被廢止,剩下“膾”,原料主要來自自身魚類,如鯉魚、鯛魚,又叫“生鮮膾”,蘸料則是豆瓣醬、辣椒醬、大蒜片,口味渾濁潑辣,與淡泊清雅的日本刺身大相徑庭,色相也黯然無光。花葉同根,如果要爭專利,先得尋根,那就穿越到兩三千年前的華夏中原來吧。
華夏飲食文化后來轉型,專在煎、炒、燉、煮、炸上下功夫,形成調和鼎鼐、五味共融的飲饌風貌。堂皇始大,從人類文明進程來說是一種進步,膾、炙被遠遠甩在后頭。無論和膾還是韓炙,各自將中原食俗某一特點發揚光大乃至趨于極致,但就是學不來中華飲饌之道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氣派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