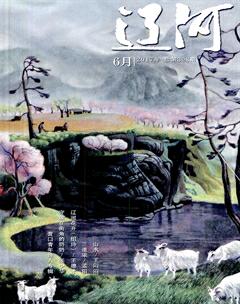玉米是我們的手足兄弟
程遠
丁酉除夕,早上九點鐘還賴在床上的我,想著妻子交代的事情:貼春聯,掛燈籠,把書櫥頂上的那塊石頭搬下來,危險不說,一年到頭的總是懸著干嘛?妻不迷信,我也不,但搬下來總還是安穩些,于是,起床。于是,收到國棟的微信:
旭光走了!
我回:什么意思?
旭光永遠地走了……
怔在那里,傻住,頭腦一片空白或急速飛旋——我想,我當時該是這樣的狀態?我撥通國棟的手機:
什么旭光永遠地走了?
我以為是旭光與國棟昨晚一起喝酒,喝著喝著,一個伏案睡著,一個踉蹌回家,上樓,看老爸老媽,醒來時,昏暗的小酒館只有國棟一人,發微信,抱怨旭光酒沒喝完就走了,甚至懵里懵懂中以為還有我……結果,當然不是這樣,公元2017年1月27日,上午9時,農歷大年三十,旭光突發心梗,死于老家寬甸,時年47歲。
旭光,本名趙旭光,小名石頭。
我把石頭放在地板上,淚水奪眶而出,
與旭光相識于1989年春天,遼寧文學院青年作家班預科班。短短的三個月時間,雖然沒有什么深交,但用句俗話說:是文學讓我們拉近了距離。因為,那是一個文學的時代,純凈,真誠,執著,是我們的代名詞,盡管現在想來有些二的意思。
此時,桌上擺有兩張發黃的照片,是作家班預科班的合影,一個在北陵公園,一個在文學院。照片中的旭光總是站在后排,個子不高,面部清瘦,頭發中分,戴一副近視鏡,謙虛而略帶憂郁的樣子。印象中,旭光的話也不多,手里總是拿著書或雜志——這也是那時文學青年的標志吧!我們住隔壁,我的上鋪是來自東港的寫兒童文學的李德杰,與旭光、于曉威、王輝同屬于丹東,故他們往來多些。我則與撫順的同學常在一起。其實,原本班上就三四十人,彼此熟悉自在情理之中。若干年后,旭光的詩歌、曉威的小說,已成為我們這屆同學的翹楚,當然還有李輕松、李保平、李見心等等——因與本文無關,暫且打住。
文學院預科班學習很快結束,秋季開始的兩年正式班,由于種種原因,我雖被錄取,但終未就讀。從此,與文學院同學也少了聯系。
1998年,我辭職,從故鄉來到沈城打工,兩年后就職一家報社。一天,在眾多的報刊中抽出一本《滿族文學》,見上面發有滿族詞典系列文章,署名趙旭光。心想,一定是我的同學吧!遂給編輯部打電話,索要作者的聯系方式。
之后,我出差丹東,與旭光久別重逢。
那時,沈陽到丹東還不通高鐵,一般都要乘坐快客,中午從沈陽走,到丹東通常也就五六點鐘了。旭光在報社樓下等我,手里拎著一個牛皮紙袋,里面裝有他編輯的《丹東日撊文化副刊,還有文稿。那時,旭光還沒結婚,更沒有女兒櫻桃。我們沒有過多的寒暄,握了手,就直奔飯店而去。那晚,還有他的兩位朋友,一個是馬云飛,一個是黃文科,都是詩人。酒,一定是上了,那種叫做大綠棒子的地方啤酒,而最有名氣的東港黃蜆子、鴨綠江小銀魚,寬甸繭蛹等等更是少不了,甚至讓我吃到了多年不見的雞血糊糊(一種雞血做法)。酒足飯飽,回賓館已是深夜。
次日,旭光陪我到鴨綠江風景區采訪,又將他的朋友欒德君、溫向陽介紹給我,使我順利完成工作任務,且在日后,與欒、溫結下友誼。
之后數次去丹東,無論因公因私,我都是首先知會旭光。也不論他在與不在丹東,都是一句話:來吧!然后默默地給我安排好行程,甚至先后兩次住在他家,喝茶,聊天,看他收藏的書畫,也不管他的妻子巍巍煩不煩,朋友圈中,旭光重友情、講道義、奉獻自己、成全他人的美德,由此可見一斑。
2011年國慶節長假,我的朋友、安慶作家余毛毛想來看紅葉,我說,在遼寧看紅葉主要有兩個地方,一是本溪桓仁,一是丹東寬甸。毛毛選了后者。知會旭光,還是那句話:來吧!不過他得先回寬甸看望父母,并在那里等我們,遂囑咐云飛安排我們游覽了鴨綠江斷橋和虎山長城。次日趕到寬甸,正趕上櫻桃感冒,在醫院打吊針,旭光歉意地說:不能陪你們去山里看紅葉了,讓我的發小國棟陪你們去吧!
國棟是縣林業局干部,也是詩人、作家。
后來,余毛毛和他的朋友感慨:東北的文友真夠哥們!
2008年秋天,旅行作家阿堅一行七人來東北,在沈陽停留一晚后去長白山,我們約定:長白歸來寬甸見。如你所知,我還是知會旭光,得到的依然是那句話:來吧!
類似的事情,想來不下四五次。而旭光來沈陽,單獨奔我的只有一次。這不公平。我在尋找回贈的機緣。
終于,前年冬天,朋友組織黔東南采風活動,要我約幾位同仁前往,我第一個想到旭光。這樣,我們才有了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遠行。本來我約他前一天到沈陽,住在我家,第二天一起去機場。可他說,已約好了另一位沈陽的朋友,我就沒有堅持,現在想來,也許是他不愿意打擾我吧!
黔東南五日,讓我們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時光。
我將十余家報刊副刊編輯引薦給旭光,大焱,袁毅,阿占,肖瑛,魏振強,張檣,李貴平,伍斌,趙永濤,亦之……我們同游了榕江大利、黎平黃崗、從江占里、岜沙苗寨和西江千戶苗寨,我與旭光形影不離。我給他拍照,給他和朋友們和漂亮的侗族苗族姑娘們合影,我甘愿做他的御用攝影師。而當夜幕降臨,朋友們熱鬧地圍坐在一張桌子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時候,我與旭光,又總是淹沒在這些來自北京、上海、廣東、湖北、山東、安徽、四川的南腔北調中。不僅是聲音,就是身材(旭光比我略高)和酒量,也與朋友們相去甚遠,難怪安慶的魏振強揶揄道:你倆是東北人么?
其實,我與旭光還是能喝點酒的。只是那幾天行程緊張,有些累,懶得干杯,
好在有沈陽北漂者大焱解圍,雖然他不勝酒力,卻高大威猛。大焱建議,此次活動結束,大家也要保持聯絡。我說對,我們干脆就成立一個全國副刊編輯后旅行小組吧!模仿阿堅的后小組,時不時地搞搞采風活動,別都悶著。
旭光贊成。雖然他多數時間沉默,這時卻十分真誠地說:歡迎各位來遼寧玩,我負責遼西南,遠負責遼東北,管吃管喝,包車包住。
一片歡呼!是啊,誰不喜歡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呢。
此次采風活動,旭光寫了一組詩,不僅發表在他主持的《丹東日報,鴨綠江周刊》上,而且被《滿族文學》轉載。主辦方很是滿意,我的臉上自然也沾了光。
旭光小我三歲,不僅詩歌寫得好,散文、報告文學、新聞寫作也頗有建樹,對地域文化更是深入研究,我們不僅是三個月的同窗好友,亦是工作、事業上的同道。我們先后合作了《國家公園。丹東專輯》、《老兵傳奇>>、《流金歲月——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等書刊的編輯、設計,尤其是由其策劃、業已進入出版階段的大型叢書《鴨綠江傳》,歷經半年,兩次駕車沿著鴨綠江邊境采訪,不僅加深了彼此間的交流、信任、友誼,也增進了相互的理解與學識的互補。
現在,我依稀記得他的召喚——
去長白山啊!自駕。
冰天雪地的自駕?
“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聽王安石先生的吧!哥們,
2016年1月10日至15日,我與旭光、云飛,還有司機小趙,從丹東出發,一路經過集安、通化、白山、臨江,直到長白,開始了第一次鴨綠江之旅。兩個月后的3月13日,二走鴨綠江再次啟程,路線與第一次大致相同,人員多了《丹東日報》女記者、作家李燕子。
這一行又是七天。兩次旅行,我拍了大量照片,且分別寫了流水。旭光、云飛、李燕子則各自撰有書稿,完成《鴨綠江傳》之史話、風物、紀行三卷,由我與朋友設計、排版,最終交給沈陽出版社——二校已過,旭光卻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我能借用這樣的詩句形容這突如其來的噩耗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從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我幾次淚流滿面,無語凝噎,妻子說:你不能總這樣啊!翻看手機,旭光的微信永遠定格在1月26日,共三條,均為舊體詩:
其一:
哀哀父母堪憐,生我劬勞艱辛。新春逾添年輪,發白再生眼昏,歲月最是無情,今夕有何不同。子孫外女嘈嘈,還得強打精神。
其二:
整日白眼睥睨,守著土雞兩只。管它鳳凰涅槃,兀自獨坐井底。天地鴻毛一羽,江湖你算老幾。不過夸克激素,挪轉乾坤亂啼。
其三:
鍋里燉土雞,微信炒金雞,始信土生金,貌似成風時。
在第一條后,我留言:祝老人家新年吉祥、身體健康!旭光即復三個握手——嗚呼!這,就是我們的最后一次交流!文科說,從來不寫舊體詩的旭光卻突然連寫了三首。難道這是讖語嗎?我想起書櫥上的那塊石頭。
此時,當我寫這篇文字的時候,翻開這條微信,看著機屏,看著鴨綠江邊一個拿著手機拍照的背影,我點燃一支煙,我說:旭光,這張照片還是我給你拍的呢!我甚至嘴角露出一絲笑,很難看的笑。旭光,你真忍心!你看看你都寫了些什么?你不是承諾朋友們來遼寧玩么?你不是告訴我,春暖花開時,我們再走一次鴨綠江么?如今草長鶯飛,鴨綠江水開始解凍,約定的日期一天天逼近,可是,你在哪里?
桌上放著一本旭光贈我的詩集《抒情的光焰》,連日來,我分別用鋼筆、鉛筆、水筆抄寫他的詩句,尤其是那首《玉米是我們的手足兄弟》,盡管抄了撕,撕了抄,依然讓我感到誠實與溫暖:
五谷之中
稻麥是貴族
被詩歌贊美著
其實 玉米
才是我們的手足兄弟
我們無法拒絕它質樸的熱誠:
災荒年節它是俠客
風調雨順它是隱者
我也用毛筆在宣紙上涂寫了阿彌陀佛、追光破俗,然后折疊起來,裝進兜里,初五,和沈陽的朋友驅車去寬甸送旭光,悄悄地在雪地上燒掉。
傍晚回到賓館,當室內只剩下我和英軍的時候,我們不約而同地相擁痛哭。是的,如上所述,旭光把丹東很多朋友介紹給了我,英軍即是其一。旭光走后,我與英軍每天微信相望,雙手合十,茶飯不思,心猿意馬——今天,我們終于找到出口,如開閘的洪水。而旭光生前建的《鴨綠江周刊》微信群,包括我們黔東南采風團的臨時群,亦是一片悲情,魏振強兄甚至在大年三十寫了悼念文字,雨作的云,雖兩次半路加入鴨綠江之旅,與旭光僅僅幾日之緣,卻也堅持從沈陽趕來,再見一面。甚至,與旭光未曾謀面的詩人李皓也囑我代獻花圈。初六,在旭光追悼會上,近三百人為旭光送行,有親人,有朋友,有同學,有同事,有他幾年來悄悄資助的失學兒童的家長……旭光,我為你感到驕傲。人生,也不過如此罷了。
現在,當我寫下這篇文字的時候,我想起于曉威同學代表文友們發表的致辭,他說:
我還想起旭光朋友圈的微信簽名上寫著:上帝說,要有光,于是有了光。這是《圣經》創世紀里的篇首語,那么,旭光就是上帝之子。旭光是快樂的,因為他永遠休息在他魂牽夢縈的故鄉,旭光是幸福的,因為他的靈魂去了天國。在那里,他的住處必是圖書館的模樣,他在那里,那里必是詩的盛會,他熱愛新聞事業,他所聽到的人間信息,必是無憂無慮和快樂童真的!
旭光,請你慢慢地走好……朋友們會繼續珍惜彼此后續的友誼,互相溫暖,直至人間的冬天最終變得飄渺而逝去。
誠哉斯言,是為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