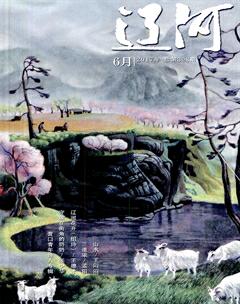含香(外一篇)
鹿禾先生
回到家,我發現家里多了一個人。在客廳里,坐著一個小姑娘,大約有十五六歲吧,低著頭,在忙著收拾東西,手腳很麻利。雖然穿著很樸素的衣服,但是看得出來,也是新買的,干凈得體。妻子看見我一些詫異,對我說:“她叫含香,是我從鄉下領來的。這不是剛剛初中畢業嗎,在家里沒事,她爸媽就讓我帶來了。我們家也缺少一個保姆。就讓她在咱家干吧。”含香這時候才抬起頭來,羞紅了臉,對我鞠了一個躬:“先生,多多包涵,請多關照。”
橫濱的春天,是一個櫻花爛漫的季節,我家門口的櫻花樹早早就開放了。含香沒事的時候,就會坐在櫻花樹下,看著櫻花,捧著下顎,在想什么。含香的眼睛非常清純,一點也沒北海道姑娘那種野性。她也會拿著一本書,在櫻花樹下,仔細地閱讀。我從報社回來的時候,會聽到含香很認真地大聲讀出來,就像是在學校里讀書的樣子。
看到我回來,含香會老遠來迎接我。“先生,您辛苦了。”這時,含香就會放下手中的書,給我烹茶。她很認真地守在茶爐前,認真地看著里邊的火苗。茶已經煮好,她也會小心翼翼地端過來。
含香坐在我的身邊,看著我讀書看報。有時候,含香會認真地問:“先生,我們的西邊,有一個很遼闊的國度,是叫中國嗎?”我看著含香,不知道她想說什么:“是的,是有一個中國。”含香繼續問:“中國的男人都很優秀嗎?他們和我們不友好嗎?”我看著她,不知道她想表達什么,我對她說:“那是一個古老的國家,他們現在和我們友好呢,田中首相架起了我們友好的橋梁。”含香不理解,她一臉的迷茫,是的,他們這些孩子。看到的都是中國威脅論。怎么知道我們的黨派政治家們的用心呢?
我的妻子是國會議員,每天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報社編輯,所以在家的時候也要多些。我有時候,竟然發現含香也會寫很優美的文字。我發現這個秘密的時候,含香有點不好意思,她會偷偷地把自己的文稿放在自己的枕頭底下。我鼓勵含香整理出來。合適的話是可以在我的報社發表的。
一番鼓勵下,我終于看到含香的文章了,這是少女清秀的文字,涵蓋著少女天真純潔的夢。她說自己夢見了中國,她夢見的中國不是報紙上說的那樣。“再斟酌一下,可以發表。”我對她說。
幾經修改,投稿后,沒多久含香的文字就被報社刊用了,給她帶來第一筆稿費。她非常高興,給我燒了好幾道菜,我和含香在一起吃飯。含香給我鞠躬,深深地謝謝我。含香說自己很早就喜歡文字。家里人不讓她寫東西,于是她就偷偷地寫,她喜歡那個古老的國家。她說自己的姥姥就是在那個國家長大,她聽姥姥說起很多那個神秘國度的故事。
含香除了做家政外,開始很勤奮地寫作。含香的文字總是帶著夢幻一般的想象力,她的筆下,出現了童話般的世界,這些故事就發生在那個夢里的國度。
一天,我家里來了一位中國朋友。含香非常興奮,她坐在朋友身邊,開始問長問短。我竟然發現,含香能夠說出很多標準的中國話。她興奮地說,自己的中國話是姥姥教給的。她問我的朋友:“中國的大學收日本留學生嗎?我可以申請到中國居住嗎?”
一次含香從街里回來,非常傷心地坐在沙發上,含香的目光開始深沉。我走過去,看著含香:“遇到什么不開心的事情嗎?”含香流著眼淚:“怎么可以這樣呢,我們的民族怎么可以這么樣呢?”我看到,含香的面前,有一份左翼政黨的報紙,揭露日本右翼不光彩的歷史。后來,我發現,含香開始在左翼報紙上發表文章。
含香的文章越來越多了,后來竟然出了集子,妻子和我都為含香高興。我們設宴給含香慶功,含香說了很多感激的話,然后含香請假要回家,說是要把喜訊和爸爸媽媽分享一下。我同意她的請求,送她去了火車站。
含香走了以后再也沒有回來,以后又來了幾個保姆,都沒有含香那么勤快。問妻子含香的情況,妻子也總是支支吾吾的,我不再追問,以后再沒有見到含香這個人。
直到有一天我去北京訪問,在一個學校里,正在走路,忽然有一個熟悉的聲音。我回頭一看,幾個留學生中,我看到含香,含香朝我招手。
我和含香在一個中餐館一起吃了一頓飯,含香送給我一本精致漢文書籍,她興奮地說,現在她已經開始用中文寫作了。末了。含香拿出一封信,遞給我,一臉虔誠地說:“請您將這封信交給姐姐,請她接受我這份無以言說的感激之情!”
鞋匠阿三
阿三是個修鞋匠。
在一個繁華地段的拐角處,阿三在那里擺了個地攤,每天天不亮,就推著攤子出來了。阿三的腿不好使,有人說阿三是當兵時參加戰斗負的傷。也確實有那么回事,因為有人看到過阿三的胸前曾經戴過英雄勛章。阿三依舊是阿三,是一個補鞋匠,每天天不亮就出攤,圍著他的是身邊堆積的很多需要修理的舊鞋。阿三呢?也總是埋頭修理著。
半晌的時候,秀姑會坐在阿三身邊。秀姑是負責這個地段的清潔工,她長得并不像她的名字那樣秀,身體肥胖,皮膚很黑,且是個寡婦,聽說她男人是個清潔工,出車禍死了。男人死了,秀姑頂替男人繼續掃大街。
阿三認識秀姑的男人,也認識秀姑。秀姑的廢話很多,多數是道聽途說來的。秀姑會指著城管隊員說東答西,阿三只顧聽,繼續修鞋,從不搭腔。秀姑坐著,嘮叨著,說累了,就會站起來,到大街上拾垃圾。每當這時候,阿三就從后頭看著秀姑扭動的大屁股,吧唧一下嘴:“喪門星,克死男人的女人。”自然,他是不敢大聲的,秀姑聽不見。
阿三繼續修自己的鞋,很少離開自己的座位,來修鞋的很多都是漂亮的女人。女人們坐在阿三身邊,就和阿三聊天,他也會說起自己的故事。阿三總是眉飛色舞地講自己當年戰場上的往事:“那些女特務都是光著屁股,奶奶的,要是有邪念,槍子是沒長眼睛的。”女人們捂著嘴笑:“阿三,你難道一點也不動心?”阿三會盯著問他話的女人:“那些都是玩命的女人。”
阿三的手工活非常好,女人們剛買的鞋需要加固的,也會來找阿三。阿三總是一邊釘鞋,一邊和她們說一些往事。慢慢地大家都曉得了,從阿三口里知道他復員后,就已經是一級傷殘軍人了。阿三的撫恤金不少,但阿三在家里呆了幾個月,覺得實在沒意思,就向街道申請了這個位置,開始給大家補鞋。
那些女人走后,秀姑就轉回來了,會靠過來,坐阿三身邊,露出討厭的神色說:“都是些不要臉的東西,穿的都是什么呀。大腿露著,臉蓋著,胸半裸著。”
阿三看一眼秀姑,就朝地上吐了口唾沫。秀姑不高興:“阿三,你吐誰?”阿三指了指地上說:“吐沫。”
秀姑憤然離開。
有好事人看到秀姑總愛坐在阿三身邊,就開始勸阿三娶了秀姑。阿三的頭搖得和撥浪鼓似的:“萬萬使不得的,那女的,方男人的,一臉克夫相。”接著,阿三會說出很多理由來。
等到這些規勸的人離開后,秀姑會轉回來,再坐在阿三身邊。秀姑會奪過阿三手中的鞋,扔在地上:“阿三,你不許這么造謠呀,你這么說,俺以后還咋找男人?”阿三盯秀姑一眼,再不緊不慢地拾起地上的鞋,拿起來繼續補:“怎么,你還想找對象呀?”
秀姑生氣了:“咋能不找呀,俺四十歲不到。”阿三聽了,不說話,只朝地上吐吐沫。秀姑生氣,朝阿三吐一口:“阿三,你別以為自己是戰斗英雄就了不起,告訴你,追我的男人多的是,看見那個老王嗎?昨天還敲我的門呢,我是那么隨便的人嗎?”
阿三繼續吐。
秀姑站起來,紅了脖子大聲嚷起來:“你個瘸阿三。死阿三!”
立即圍上來很多人,秀姑憤憤不平繼續又說又罵,阿三不搭理,繼續修手中的鞋。秀姑就哭著離開阿三的攤位。大家也都搖著頭散了。
和往常一樣,阿三到了路燈發亮的時候,開始收拾自己的鞋攤。當他把修鞋機子搬到三輪車上的時候,秀姑站到了阿三身邊:“阿三,你就給我一個痛快話。你愿不愿意?”阿三不說話,繼續搬自己的家什。秀姑摁住阿三的手:“你給我一個痛快話呀。”
阿三把秀姑的手拿開,看著秀姑:“什么痛快話?我和你家里的是兄弟,我答應過他照應你,缺什么,我這里有,你可以拿走。”秀姑看著阿三:“你說我缺什么?我啥都不缺,就缺個男人。”阿三慌張地看著秀姑,眼里流動著復雜的神情:“你說的啥呀?我還得回家加班修鞋,明天等著拿呢。”
后來,阿三繼續在那個地方修鞋,秀姑則繼續在那掃大街,但再也沒在阿三的攤位旁坐過。
再后來的一天,秀姑衣著光鮮地走到阿三攤位旁,說,“過幾天是我與老王湊合到一起的日子,去熱鬧下,好嗎?”阿三一聽,“呼”地站起來,盯著秀姑吼:“我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