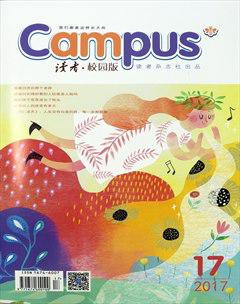搬家記
一葉知秋
非洲坦桑尼亞的角馬群、北羅納島的灰海豹、美國北部的帝王金斑蝶,一年一度的大遷徙,已經成為它們的一種習慣。或許,我也是一只小小的金斑蝶,休憩在載滿陽光的枝頭,尋找著遠方的故鄉(xiāng)。
彎彎曲曲的小路,通往兒時居住的老屋。
老屋幾乎和外公、外婆一樣老,那時我與外公外婆一起住在老屋里。老屋雖老,卻充滿了樂趣。打雷時和我一樣嚇得抖灰的土墻壁,屋頂上爬滿了青苔的青瓦片,風中抖得吱呀作響的紅木門,它們都是與我一起長大的有著深厚情誼的小伙伴。而我想要永遠待在老屋的愿望卻沒有實現(xiàn)——5歲時,到了上學的年齡,父母提出要把我接到城里去住,說城里有我最愛的糖果和玩具。這就是我經歷的第一次搬家。汽車呼嘯著離開,我不帶任何眷戀地朝背后揮了揮手,就此丟下了孤零零的老屋。
老屋真的老了,我仿佛聽見它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窗臺上的仙人掌開出了粉嫩的小花,每一根刺的尖上,都扎著金黃色的明媚,把小小的新房照得亮堂堂的。
我們搬進了一間80平方米的出租屋。出租屋雖小,卻擁有一份擁擠的溫馨。挨挨擠擠地躺在沙發(fā)上看電視,擠在洗手間刷牙時牙膏沫子亂濺,小飯桌上升起的香噴噴的熱氣,臨睡前溫柔地道聲“晚安”,我們過著平凡卻又快樂的日子。幾年后,爸爸的事業(yè)風生水起,便決定買一套新房。這時的我不再相信糖果與玩具的騙局,第二次搬家,是一種難以言說的感覺。難過與不舍如潮水般一齊涌上我的心頭,仿佛即將與一位親密的老朋友告別。看看這個,摸摸那個,突然發(fā)現(xiàn)這小屋竟是如此的可愛。“快收拾東西吧!”媽媽催促道。這把破梳子要,這張舊報紙要,這臺壞了的風扇也要……我恨不得把那墻角上的蜘蛛網也給扯下來帶到新房子里去。“日久生情”,不僅是對人,對房子也是如此。“我們不搬家好不好?”這句話一直憋在我的心里,卻直至大門合上的那一刻也沒有說出口。
再見了。看著卑微的出租屋漸漸消失在視線外,我終于帶著哭腔小聲地朝它道了聲“再見”。
是不是我再也不會回來了。是不是人越長大,放不下的東西便越多。
我想,不是的。
舍不得不是因為念舊,而是因為越長大,便越懂得家的意義。
不管在哪兒,不論何時,再簡陋的屋子,但凡安上了“家”的名號,便多了一份明媚溫暖在里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