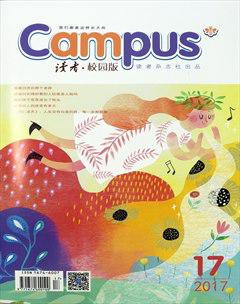奶奶的比喻句
肖爻悄悄
壯得像滾筒洗衣機
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寫日記:“今天天氣很好,云朵白得像棉花糖,又像我的奶奶,悠閑地在天上散步。”我爸看了之后,訓斥道:“把在天上散步這句改了!奶奶怎么會在天上呢?”奶奶反倒瞪了我爸一眼,不介意地笑著問我:“云云,今天不是陰天嗎,云怎么會是白的?”
我說:“沒錯,可我總不能寫白云不白吧。”
奶奶又問我:“為什么一定要寫白云很白呢?”
我想了想,說:“因為這樣就能湊成一個比喻句了。”
奶奶嚴肅起來,拋出兩個問題:“第一,仔細觀察、準確描寫是否重要?第二,云不是白的怎么就不能用比喻呢?”我想了很久,終于換了一種描述:“今天的云朵一點也不白,有點像弄臟了的棉花,里面帶著灰塵。”
奶奶大笑道:“也像你這臟兮兮的臉。看看你,每天干干凈凈地出門上學,回家后,臉總是臟得跟家里剛用完的拖把一樣。”
那時候,奶奶還沒有退休,在縣里的一所中學教語文。她身材矮壯、骨架大、手掌厚,不像舞文弄墨的語文老師,倒像鍛煉過度的體育老師。
小學六年級時,我帶幾個同學來我家玩。一見廚房里揮刀如風的奶奶,有人大驚道:“好一個壯婦!”還有人操著蹩腳的英語說:“Wow,like a man.”這兩個人當即被我驅逐,卻又被奶奶請了回來。
奶奶對我說:“云云,他們沒說錯。我們家永遠對說實話的人敞開大門。我就是壯得像咱家那臺滾筒洗衣機。”我哭喪著臉說:“哪有人這么形容自己的。奶奶,你好歹也是教語文的,非要把自己說得跟家電一樣嗎?”
不管是作文還是做人,真實都是奶奶的第一要義。特別是退休后,奶奶徹底撇開了學校的規矩和同事的看法,真實度越來越高。她總在吃飯時喝兩杯白酒,飯后必吸一支煙。除此之外,奶奶還養了一只大黑貓,在頂樓種菜,在陽臺種花。奶奶還總在腰間別一個收音機,聽著里面“咿咿呀呀”的京劇,在家里走來走去。
停在花朵上的胖蒼蠅
大二那年,我回老家過暑假,見奶奶隔三岔五就把家里的那只黑貓扔進臉盆里。貓剛跳出來,奶奶就趕緊抓住它的身子,大笑著又將它扔回去;貓再逃,奶奶再抓、再扔,奶奶的笑聲一次比一次大。
我在旁邊看得膽戰心驚,趕緊向爸爸反映。我爸說:“你奶奶的這些行為,是在緩解寂寞啊。”
“那怎么辦?”
沉默片刻,我爸說:“給你奶奶找個老伴兒吧。”
一天,奶奶打量了我半晌,驚訝地問:“云云,你怎么瘦了?”我翻了翻眼皮:“我早就瘦了,你現在才看出來嗎?”
奶奶不無遺憾地說:“唉,你胖的時候多可愛啊。記得你有一次寫作文,說‘我像停在花朵上的蜜蜂一般稍作歇息……我還糾正了你,說你那么胖,應該是停在花朵上的胖蒼蠅。還有,你小的時候總臟兮兮的,多有趣啊,怎么現在白白凈凈的了?”
我生氣地說:“奶奶,我都是大姑娘了,怎么還能像個野丫頭一樣臟兮兮的呢?”奶奶搖著頭說:“還是小時候又臟又胖的你好,可愛、真實。”我快哭了:“我要再那么真實,還會有男孩子喜歡我嗎?”奶奶想了想說:“也是啊。”
我趁機切入:“奶奶,你一個人住的這兩年不寂寞嗎?”
“不寂寞。”
“那……奶奶想沒想過找一個老伴兒?”
奶奶沉默了很久,終于說:“萬一我和他沒結為夫妻,反倒成了兄妹怎么辦?”
我震驚于奶奶的接受能力,更敬佩奶奶的自知之明,正琢磨說句什么話來安慰奶奶時,她已經搶先自我安慰了一番:
“沒關系,就算不能成為一起過的老伴兒,也能成為一起玩的伙伴。”
他像一篇短篇小說
沒過多久,經親戚朋友的推薦,來找奶奶玩兒的伙伴出現了。那人叫大金,是個木匠,雖然已經65歲了,但身子骨硬朗,整天樂呵呵的。
大金很幽默,也很會討人開心。奶奶曾經當過語文老師,大金就稱奶奶為“知識分子”;奶奶抽煙喝酒,大金就稱贊奶奶豪放;奶奶種向日葵,大金就說奶奶有愛心。總之,奶奶的特點成了大金心里的優點,奶奶的惡習也成了大金眼里的亮點。
奶奶和大金在一起生活的三年里,兩人從沒跟對方紅過一次臉,是大金讓著她、順著她。可這種讓反倒成了一種進,這種順反倒成了一種改變。
大金對奶奶說:“梁老師,你看你啊,抽煙、喝酒、種菜、養花,愛好挺豐富的。興趣廣泛是好事,可我怕你累著。要不,咱把抽煙和喝酒給省了,我陪你散步、曬太陽?”奶奶居然說:“好。”
大金笑了,趕緊替奶奶搬一把椅子到陽臺上,自己則鉆進廚房洗碗。
奶奶盯著大金的背影說:“我這一輩子啊,剩下的時間只夠寫一篇短篇小說了。”
大金沒聽懂奶奶的話,正要問,發現她已經歪在椅子上閉目養神了。
奶奶沒能熬過那個冬天。她去世后,大金一直一個人住在奶奶的屋子里,直到因病去世。我們回去參加他的葬禮,發現家里還是老樣子,陳舊而樸實。陽臺上,一溜兒向日葵寂靜地開得熱鬧,一抬頭,天空拂過幾朵緩緩移動的白云。
我忽然想起了小學一年級時寫的日記:“今天天氣很好,云朵白得像棉花,又像我的奶奶,悠閑地在天上散步。”
大金走在奶奶身邊,陪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