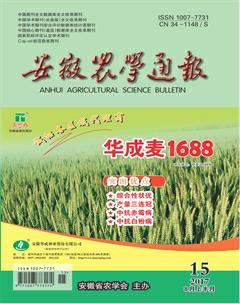我國碳稅建設的系統性思考
郭承龍
摘 要:全球性氣候變暖已是環境議題焦點。自主承諾2030年停止二氧化碳增長,嚴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是我國面臨的嚴峻考題。碳稅是碳減排工具中的一種有效經濟手段,碳稅是一項復雜系統工程。該文探討了法律(制度)層面的效應、經濟層面的效應和環境層面的效應,并指出碳稅應作為一個獨立稅種,與環境稅、資源稅等其他稅種相互配合,滿足我國碳排放的發展權,同時兼顧與經濟和環境的和諧。
關鍵詞:碳稅;法律效應;經濟效應;環境效應
中圖分類號 F812.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31(2017)15-0001-3
1 引言
世界各國已經認可溫室氣體是全球溫度上升的“元兇”。遏制氣溫繼續上升的直接方法就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除了技術手段外,經濟政策領域中的稅收是調節溫室氣體排放的方法之一。從理論上來看,通過對二氧化碳(CO2)、氫氟碳化物、甲烷和全氟化碳等溫室氣體全面征稅以期達到減排目的。但是對各種溫室氣體排放進行全面檢測不具操作性,征管難度大、成本高昂。而CO2排放約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77%,相應的技術監測水平和征管成本較容易,直接針對CO2排放所征收的碳稅應運而生。碳稅與碳排放交易等市場手段不同,碳稅征管只需額外增加非常少的管理成本就可以實現。碳稅對減少CO2排放保護環境有積極影響,但是也要考慮到碳稅對國民福利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碳稅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既要考慮到稅基、稅率、征管主客體,也要考慮到與其他具有間接環境效應的稅種間的疊加問題。碳稅就是通過對煤、油、氣及其衍生品等化石能源,測算出碳含量或者碳排放量進行征稅。碳稅本質上是利用價格手段干預所帶來的經濟效應減少化石能源消費從而達到降低CO2排放量的目的。相對于行政性手段,碳稅具有不扭曲稅制、低成本監管、避免尋租以及無需確定基準年等優點;碳稅還會帶來環境治理的協同效應,降低其他污染物的排放;碳稅收入還可用于節能減排技術的研發,用于補貼效率為先引發的碳排放的不公平性而加重的稅負,用于財政轉移支持部分行業、落后地區的發展,實現共同發展,從而更好地促進我國持續性發展綠色經濟。因此,本文認為碳稅是法律制度、環境效應和經濟效應的集合體(圖1)。
2 法律效應
20世紀90年代初,戴維皮爾斯首次提出碳稅概念,庇古稅可視為其發源點,碳稅具有較完整的法律理論體系。芬蘭于1990年實施了碳稅,是碳稅立法的先行國。之后,北歐的荷蘭、挪威和瑞典等國家紛紛開征碳稅。碳稅的法律性問題之一就是協調與各種環境稅種、環境性稅目的關系。我國排污費、燃油稅、資源稅等各自分離、分立,環境保護屬性不突出。我國將于2018年1月1日實施的《環境稅》,在一定程度上規范了上述問題,但是只是針對污染物排放,并不包括CO2,因此,如果碳稅的設立必然對現有環境稅費法律產生沖擊和影響。我國暫無獨立的碳稅法律制度,只是在資源稅、消費稅部分條目中體現著一定的碳稅功能。我國是以煤炭為主導的能源費結構。現行的各種法律(煤炭法、電力法等)并沒有將這一最大的消費客體納入征管范圍,僅僅涉及資源稅等。煤炭消費不僅是污染物的排放,更是碳源的最大來源。當前的制度設計并不足以解決節能減排,霧霾、PM2.5爆表、屢破高溫記錄等已經深刻地影響到居民健康和生活。這與化石能源等消費密不可分。碳稅法律意在減緩國內生態環境壓力,憑借法律本身的強制力促使能源結構調整、消費效率提高,控制CO2排放同時減少其他污染物排放。
2.1 碳稅法律意在保障碳減排國際承諾 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其中提到CO2減排措施之一就是碳稅。我國明確表態,2020年,單位產值CO2排放較2005年減少40%~45%;2030年,我國化石能源的CO2絕對排放停止。我國將碳減排目標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保證受到法律的監督。碳稅法律為今后的碳政治、碳外交等國際談判奠定基礎,掌握一定的主動權。
2.2 碳稅法律也是突破國際綠色壁壘的武器 國際貿易中碳關稅本質上具有碳稅功能,同時也是新型綠色保護壁壘。例如《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規定從2020年征收碳關稅以保護國內產業競爭力。碳關稅實質是發達國家(需要承擔CO2減排義務)變相保護本國產業,降低非減排義務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產品競爭力,嚴重損害了發展中國家利益,包括我國。為了避免雙重征稅(林伯強,2010)[1],我國應盡早制定碳稅法律,以法律武器打破綠色壁壘,迎接全球性的碳稅趨勢。
2.3 碳稅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動力轉型 碳稅具有明顯的導向作用,促使經濟增長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移。通過向高碳排放企業征收碳稅,推動資本和資源流向低碳部門。企業為轉嫁稅負中,主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快技術研發、推出低碳產品,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動力轉變,也實現溫室氣體排放。因此,在我國,碳稅應當作為一種獨立稅種,從法律層面立規,以國家機器的強制力保障碳稅得到如實執行。
3 經濟效應
碳稅對經濟影響主要分為以下幾種觀點:碳稅征收短期內對經濟增長影響相當大,長期影響小得多(魏濤遠,格羅姆斯洛陽德,2002)[2];碳稅對GDP負面影響有限(AA Yusuf, BP Resosudarmo,2007)[3],影響不大(姚晞,劉希穎,2010)[4]。碳稅對GDP影響不確定,主要視碳稅的替代效應而定,使用碳稅替代資本稅可促進GDP增長,替代勞動稅和消費稅則無法有效促進GDP增長(Takedaa S,2007)[5]。碳稅對經濟的負面效應可以通過碳稅設計、各種稅負調節,分配與轉移優化,促進實現碳稅對經濟正向效應。
3.1 獲得雙重紅利效應 經濟學中的稅收理論認為,稅負改變商品和要素的均衡水平,從而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效應,產生福利的凈損失。當商品的稅率遵循逆彈性法則時,稅收對經濟扭曲效應減少到最低;而所得稅(個人、公司)具有較嚴重的扭曲效應。在征收碳稅同時降低所得稅或資本稅等生產性稅率,避免或減弱其扭曲效應,加快資本形成和提高勞動供給,進而直接引起產出品成本降低,價格下降,消費需求增加,推動生產部門擴大生產規模,推動經濟增長。雖然經濟增長增加了能源需求,但是碳稅抑制了能源消費和生產性CO2排放,尋求低碳能源和替代能源等,而CO2排放量增幅小于經濟規模擴張幅度,可實現碳稅的“雙重紅利”。正如瑞典開征碳稅同時降低所得稅,使得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占GDP比重下降到1.9%和19.5%;芬蘭損失的所得稅和勞動稅被開征的生態稅和能源稅所補償。德國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02年底,碳稅征收創造了6萬個新的就業崗位。由此可見設計合理的碳稅制度能獲得“雙重紅利”。
3.2 優化稅負支出結構 稅收是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當前,我國有關環境改善的稅種和條目眾多,不成體系,容易造成部分行業稅負輕重不一。在碳稅設計和實施中必然需要對現行稅收的結構、稅種、稅率進行調整和優化,均衡各行業稅負。本著不增加稅負負擔為原則,實施優惠稅收返還、補貼、降低其他稅種的稅負等政策。例如丹麥對同時繳納碳稅和增值稅的企業,碳稅返還50%。稅收優惠是碳稅國家普遍做法。通過稅收優惠,調節稅負大小,優化稅收結構,實現稅負不增和經濟增長的目的。
3.3 調節財政支出 征收碳稅可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政府儲蓄增加有利于擴大投資規模和資本積累,逐步提高生產率。通過財政支出調整,調節和鼓勵企業生產經營低碳化方向和居民消費行為,減輕稅收本身的累退性問題。
3.4 促進技術進步 碳稅開征必然使得能源價格提高,敦促企業研發、采用新能源技術,經輻射和擴散作用,帶動整個社會的技術進步。碳稅長期效用會抵消短期內不利影響,對經濟總量、就業、進出口、財政收入具有積極的提升效應。
4 環境效應
碳稅不僅是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也是實踐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環境庫茲涅茨存在已被認可(賈康,王桂娟,2013)[6]。盡快發揮后發優勢,采取措施步入生態環境友善的較高階段,減少未來付出更高代價。碳稅正是其中的手段。碳稅征收使得CO2排放減少(Floros,Vlachou,2005)[7]。根據對北歐國家碳稅評估,丹麥碳稅政策使得能源耗費降低10%,CO2減少3.8%,挪威碳稅效果評估顯示碳稅使得CO2排放下降3%~4%。學者模擬研究也表明碳稅征收對我國CO2排放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王金南,2009;Alton T,Arndt C,et al,2014)[8-9]。由于我國對化石能源消費依賴度高,石油進口已超過國內需求的50%,豐富的煤炭資源優勢造成改變能源消費結構阻力大。如果不提前做好控制CO2減排技術研發、開發新型能源,很可能陷入碳鎖定和碳依賴的困境,使得未來減排成本劇增。據荷蘭環境評估機構研究表明,采取減排措施越晚,遠期經濟代價越高,排放限定值后移10a實現屆時減排幅度至少要擴大1倍,成本大大增加。
碳排放交易和碳稅都是有效的環境政策工具。但是碳排放交易是事先確定碳排放總量,單位排放價格波動;碳稅是事先規定單位排放價格,總量不確定。當氣候變化臨界點和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關系逐漸清晰的時候,總量控制的碳交易政策愈來愈受到發達國家歡迎。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發展仍然是主要內容,基于碳排放的發展權是基本權利,短期內總量控制對我國發展不利。碳稅總量不限定保證了我國碳排放發展權。但是從長期來看,總量控制全球共同義務,我國也不例外。兩者相結合才能真正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保護環境目的。因此,我國碳排放短期內應以碳稅為先,長期內兼顧總量控制。
5 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碳稅建設不能單純只考慮法律、經濟效應和環境效應其一,應將其視為一個系統化工程。碳稅產生的經濟效應、稅負轉嫁以及環境影響,可以通過碳稅制度設計以及相應的財政收益分配方式加以彌補[10]。因此,將碳稅作為一個獨立稅種,與環境稅、資源稅等其他稅種相互配合,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建設生態文明和環境友善,也能兼顧我國發展權。
參考文獻
[1]林伯強.碳稅陰謀論[J].中國經濟和信息化,2010(10):27-27.
[2]魏濤遠,格羅姆斯洛德.征收碳稅對中國經濟與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8):47-49.
[3]AA Yusuf,BP Resosudarmo. On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 of carbon tax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indonesia[R].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 Development Studies,2007,17(1):131-156
[4]姚晞,劉希穎.基于增長視角的中國最優碳稅研究[J].經濟研究,2010(1):48-58.
[5]Takedaa S. The double dividend from carbon regulations in Japan[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 International Economies,2007,21(3):336-364.
[6]賈康,王桂娟.以稅制綠化和碳稅開啟新一輪環境稅制改革[J].中國電力企業管理,2013(7):15-17.
[7]Floros N,Vlachou A. Energy demand and energy-related CO2 emissions in Greek manufacturing: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 carbon tax[J]. Energy Economics,2005,27(3):387-413.
[8]王金南,嚴剛,姜克雋,等.應對氣候變化的中國碳稅政策研究[J].中國環境科學,2009,29(1):101-105.
[9]Alton T,Arndt C,Davies R,et al. Introducing carbon taxes in South Africa[J]. Applied Energy,2014,116(3):344-354.
[10]Baranzini A,Goldemberg J,Speck S. A future for carbon taxes[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0,32(3):395-412.
(責編:徐煥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