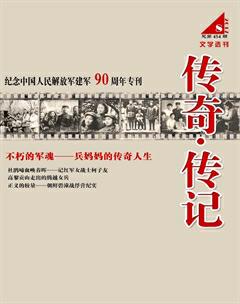團(tuán)圓
洪杰勵(lì)
簡 介
周莊,1920年出生,原名周莊美,上海市人。1938年冬在上海華東女中參加市學(xué)生抗日救亡協(xié)會,任小組長、執(zhí)行委員。1939年底加入中共地下黨并任支部書記。1942年10月因黨員身份暴露,轉(zhuǎn)移到江蘇盱眙縣馬場區(qū)任區(qū)委委員,后任地委組織部干事、山東兵團(tuán)新華分社、淮南日報(bào)社編輯等職。解放后,歷任《南京公安報(bào)》主編,南京市公安局辦公室副主任,江蘇省司法廳副處長,華東水利學(xué)院宣傳部副部長,南京師范學(xué)院數(shù)學(xué)系、音樂系總支書記等職。1980年離休,享受副省級醫(yī)療待遇。
母親周莊今年已經(jīng)97歲高齡了,但是身體健康,思維清晰。每天讀書、看報(bào)、散步,生活極有規(guī)律。即便在風(fēng)云激蕩的戰(zhàn)爭年代和命運(yùn)跌宕沉浮的動亂年頭,她都保持著樂觀、開朗、豁達(dá)、隨遇而安的良好心態(tài)。
母親有時(shí)會拄著拐杖獨(dú)自坐在陽臺上,沉思默想,深情地回顧和父親洪沛霖離多聚少卻伉儷情深的歲月。每一次的團(tuán)圓,無疑是全家人最幸福的時(shí)刻。
往事如煙,卻已深深地烙在母親的腦海之中,定格于那些波瀾起伏的歷史瞬間。
遍地狼煙,父母分離再聚首
母親穿著上海最時(shí)髦的短袖碎花月白色旗袍,清秀的臉龐上洋溢著幸福的微笑。我們母女倆坐在上海美亞照相館的道具轎車?yán)铮袷且霭l(fā)的樣子,其實(shí)那是母親將要留下我,獨(dú)自一人在我黨地下交通員的護(hù)送下返回蘇中解放區(qū)和父親團(tuán)聚。照片的背面寫著攝影時(shí)間:1947.9.2。
她在笑,因?yàn)槟菚r(shí)她要來解放區(qū)了。孩子那幾天因我不好而有些發(fā)燒,較平時(shí)瘦,不過很像我。
1948.2
這是我父親的手筆。顯然這張照片是母親帶給父親看的,以解他對女兒的思念之情。
母親出生在上海的一個(gè)手工業(yè)者家庭。外公周煥祥13歲出門拜師學(xué)藝,成為木匠師傅的徒弟。外公雖然沒有接受過科班教育,但是天性聰穎,加上格外勤奮,從一個(gè)打下手的徒弟做起,最終練就了一門好手藝。他自辦了“祥記營造廠”,還承包了不少高檔建筑工程(如永安公司、錦江飯店裝潢的木工活等),在同行和外國商人中漸漸小有名氣,生意也越做越火,家境漸漸殷實(shí)。
外公有3個(gè)女兒,我母親是老大,其后還有過幾個(gè)妹妹,但因當(dāng)時(shí)封建迷信和醫(yī)療條件有限,只剩下2個(gè)妹妹,都比母親小了十幾歲。因我母親自小聰明伶俐,長得端莊秀麗,外公視她為掌上明珠,看作是自己未來的希望。
當(dāng)時(shí)外公已經(jīng)積累了一點(diǎn)資本,因無子,按照封建傳統(tǒng),家中的資產(chǎn)就要傳給侄子。而我的外公是一個(gè)思想開放、觀念新潮的人,他見母親好學(xué)上進(jìn),頗有巾幗不讓須眉之氣魄,便不顧眾親戚的指責(zé),排除萬難送我母親去上學(xué)。
因品德優(yōu)秀,學(xué)習(xí)努力,母親在高中時(shí)就接受進(jìn)步思想,被黨的地下組織看中,于1938年參加了上海市學(xué)生救亡協(xié)會,1939年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她一邊讀書,一邊做抗日宣傳工作。外公雖不識字,但抗日救國的烈火一直在他的心中燃燒著,為了支持母親的工作,外公特地做了一個(gè)夾層大衣櫥,給母親收藏進(jìn)步書籍和黨內(nèi)秘密文件等,黨組織也經(jīng)常在家里的閣樓上開會,組織活動。這個(gè)大衣櫥至今仍保留在上海的家中。
高中畢業(yè)后,為減輕家庭負(fù)擔(dān),母親決心報(bào)考當(dāng)時(shí)收費(fèi)較少的國立大學(xué)。當(dāng)時(shí)讀得起大學(xué)的大多是達(dá)官貴人的子女,不少學(xué)生坐著汽車在家長的陪同下前往學(xué)校報(bào)名。家長大都西裝革履,皮鞋锃亮,他們邊看《報(bào)名須知》,邊為子女填寫表格。而我的外公則身穿一件干干凈凈的中式布衫,門襟處是一排中式扣子,衣服的左上角還插著一個(gè)木匠尺筆袋。為了表示隆重,外公特地雇了一輛祥生出租車一同前往。可是看著家長們都在為他們的子女填寫表格,不識字的他頓時(shí)束手無策,這時(shí)候只見母親略微瀏覽了一眼報(bào)名《須知》,便很有把握地說:“沒關(guān)系,我自己來填。”外公這才松了一口氣。
考試結(jié)束,母親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取了國立暨南大學(xué),成為周家祖祖輩輩中第一個(gè)女大學(xué)生。
1942年8月,因母親身份暴露,組織決定秘密將她送往淮南抗日根據(jù)地。臨行前,母親考慮到,被視為掌上明珠的她如果忽然失蹤將會給外公帶來致命的打擊,于是她對外公說:“我到敵后打日本人去。”有著深深愛國激情的外公雖萬分不舍,還是毅然支持母親離開家,奔赴抗日敵后戰(zhàn)場。
母親只身來到津浦路東抗日根據(jù)地,任淮南路東地委組織干事。1943年結(jié)識了地委公安處的保衛(wèi)科長——我的父親洪沛霖。
父親1917年出生在安徽涇縣茂林鎮(zhèn)的一個(gè)小手工業(yè)者家庭,父母以種地和編制竹器為生。因家境貧寒,父親只讀到小學(xué)二年級就輟學(xué)在家,過早地走上了艱辛的謀生之路。他采過茶,種過地,沿街叫賣過燒餅油條。但他酷愛讀書,敏而好學(xué),1934年在涇縣麻嶺坑當(dāng)上了私塾老師。不久,經(jīng)中共涇縣地下黨負(fù)責(zé)人介紹,他寫下“我愿意參加共產(chǎn)黨,打土豪分田地”的志愿,擔(dān)任了紅軍游擊隊(duì)的地下交通員。1938年,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duì)改編成新四軍,父親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皖南事變前夕,他奉命隨張?jiān)埔輩⒅\長北上,開辟淮北革命根據(jù)地,轉(zhuǎn)戰(zhàn)淮北、淮南等地。
1944年,父親調(diào)任甘泉縣公安局任局長,母親也調(diào)入甘泉縣委任秘書。工作中,父親的精明能干得到首長和同志們的贊譽(yù),也贏得了母親的芳心,雙方相約,等待抗戰(zhàn)勝利的那一天走進(jìn)婚姻的殿堂。
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后,父母在淮南解放區(qū)簡單地舉辦了結(jié)婚儀式,從此他們相約白頭,不離不棄。然而,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他們總是聚少離多,常常面臨生離死別的考驗(yàn)。
1946年春天,蔣介石發(fā)動內(nèi)戰(zhàn),大舉向我根據(jù)地進(jìn)攻。這時(shí)母親已懷有身孕,隨軍行動不方便。為了不耽誤父親工作,夫妻倆商量后決定母親回上海娘家生孩子。母親脫下軍裝,換上從上海帶來的旗袍,在黨組織派來的秘密交通員的幫助下,步履艱難地前去上海。
這是一段危險(xiǎn)而又艱難的路程。一路上國民黨設(shè)卡布哨,母親因長期穿長袖軍裝,臂膀較白,而手卻曬得黝黑,在路過敵占區(qū)揚(yáng)州哨卡時(shí),母親穿著短袖,黑白分明的反差立即引起哨兵的懷疑。他用槍指著母親,問她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聰明機(jī)智的母親聽出哨兵是上海口音,非常鎮(zhèn)定地用上海話對答,解釋自己嫁到蘇北,現(xiàn)回娘家生孩子。哨兵聽到鄉(xiāng)音,立馬露出笑臉,并很快將她放了過去。跟在后面的地下交通員卻嚇出了一身冷汗,幸好有驚無險(xiǎn),安全過關(guān)。經(jīng)過一周的輾轉(zhuǎn)奔波,母親終于平安回到了家。
在上海老家,母親和父親的第一個(gè)孩子——我出生了。這是一個(gè)充滿喜悅和希望的時(shí)刻,本該是全家濟(jì)濟(jì)一堂,舉行慶祝新生命誕生的儀式,母親卻形單影只,與組織和父親徹底失去了聯(lián)系。
隨著我一天天長大,母親對組織和父親越來越牽掛。她獨(dú)自去馬斯南路(現(xiàn)思南路)周公館中共辦事處尋找組織,發(fā)現(xiàn)門口有幾個(gè)特務(wù)模樣的人活動,考慮再三,沒有貿(mào)然進(jìn)去。其后又化名一男性讀者給中共機(jī)關(guān)刊物《群眾》雜志聯(lián)系。果然《群眾》雜志刊出一則啟事“某某先生,請來一談”。興奮的母親急忙前往。接待她的同志警惕性很高,問了幾個(gè)問題,在確認(rèn)了母親身份后,對母親說:“現(xiàn)在形勢很緊張,路上危險(xiǎn)性太大,等以后形勢好轉(zhuǎn)后再通知你,你帶好孩子,為革命培養(yǎng)好后代也是對革命的支持。”
母親不氣餒,見外公家中有學(xué)徒的親戚劃小船從蘇北來,便試探著詢問。這個(gè)來自海門的親戚說,家鄉(xiāng)白天是國民黨,晚上是共產(chǎn)黨。母親立即就明白,海門是國共拉鋸地區(qū),一定會有黨的組織,于是說自己有一親戚在海門,希望下次來能把她帶去探望。
臨行前,母親特地帶著一歲多的我到附近的照相館照相,準(zhǔn)備帶給我從未謀面的父親,以解他的相思之情,于是便有了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張照片。
1947年9月,母親悄悄丟下我,搭乘外公徒弟的小船,輾轉(zhuǎn)到達(dá)海門靈甸解放區(qū)。當(dāng)她看到政府門前貼的標(biāo)語口號時(shí),心中頓時(shí)感到陣陣溫暖,巨大的歸屬感油然而生,一如孩子回到母親的身邊。
組織找到了,可是父親隨解放大軍究竟去了何處卻無從知曉,母親一連寫了20幾封信寄往有關(guān)部隊(duì),遠(yuǎn)在山東前線的父親終于收到了其中的一封。當(dāng)父親看到信封上那熟悉的字體和右下角母親姓名落款時(shí),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他激動得徹夜難眠,以前聽說的母親被捕犧牲的消息就這樣統(tǒng)統(tǒng)化為烏有。為慶祝得到母親的音訊,第二天他特地包餃子請大家吃。
同樣,母親得到父親的消息后也激動得熱淚盈眶,所聞父親英勇犧牲的傳言也煙消云散。不久組織上將母親調(diào)到山東工作,跋涉十多天后,母親終于到了山東淄博。這時(shí)父親已經(jīng)擔(dān)任了華野七縱保衛(wèi)部部長,距離他們分別已經(jīng)整整兩年!
母親被組織分配去新華社山東兵團(tuán)分社擔(dān)任編輯。相逢總是短暫的,他們無法長相廝守。父親在前線戰(zhàn)斗,母親則編輯捷報(bào)傳向全中國。他們只能在戰(zhàn)斗間隙,部隊(duì)休整時(shí)才能享受短暫相聚的歡樂。
上海解放,父母尋女喜相逢
1949年4月,百萬雄師過大江,父親一路隨軍打到上海。5月27日上海迎來解放。
幾天后,父親按母親所說的地址找到了上海中正東路(現(xiàn)延安東路)1462弄永貴里102號。這天正是端午節(jié),石庫門的外公家中高朋數(shù)桌,場面頗為隆重。我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3歲,坐在小桌旁。
這時(shí)有兩名軍人一前一后從后門進(jìn)來,其中一個(gè)又高又瘦,小腿上裹著綁腿,腰間挎著手槍,身后跟著一位挎長槍的戰(zhàn)士。見到這兩位不請自來的軍人,滿堂賓客皆大驚失色,不知所措。那時(shí),上海市民受國民黨謠言宣傳影響,說共產(chǎn)黨共產(chǎn)共妻,還設(shè)了聞香隊(duì)專門查搶請客吃飯的人家,在場的人都認(rèn)為他倆是來攪局搶飯的,母親的二嬸甚至嚇得逃進(jìn)了房間,躲在門后直打哆嗦。
只見外公不慌不忙地迎了上去。來人問,您老是不是周莊的父親?外公點(diǎn)點(diǎn)頭。雖然我不足3歲,可能是因?yàn)檠壍年P(guān)系,冥冥中感到來人正是我從未見過面的父親。他愛憐地從上到下打量著我,撫摸著我的頭,操著外地口音不知問我些什么。接著他留下7尺布給外公,連飯也沒吃一口,便帶著小戰(zhàn)士匆匆離去。全場嘩然,親朋好友問外公,這就是你女婿?是真的還是假的?才十幾歲的兩個(gè)小姨曾聽我母親說過父親右小指關(guān)節(jié)是彎曲的,后悔沒看個(gè)仔細(xì)。眾人議論紛紛,有的評論父親,有的說原來共產(chǎn)黨沒有共產(chǎn)共妻,也根本沒有什么聞香隊(duì)。只有我外公堅(jiān)定地確認(rèn)這個(gè)女婿是真的,是個(gè)能人,是個(gè)做大事的人。
隨著全國解放號角的吹響,解放軍很快解放了大江南北。一天,我站在上海家中的門口,只見一輛三輪車載著一個(gè)年輕的女子,從弄堂不遠(yuǎn)處向我駛來。她的手上還抱著一個(gè)男孩子,兩眼直盯著我看。不知是心靈感應(yīng),還是血脈相承的親人呼喚,我轉(zhuǎn)身向家中飛奔而去,對著正在炒菜的外婆說:“我媽回來了!”外婆驚得差點(diǎn)把菜勺子掉在地上,繼而定了定神說:“小孩子不要瞎講。”那時(shí),我母親已經(jīng)站在了外婆面前。
多年后,母親回憶當(dāng)時(shí)的情景時(shí)說,她遠(yuǎn)遠(yuǎn)看見我斜倚在門口看著她,那樣子,那神態(tài),都是我父親的翻版。
在這段時(shí)間,我家又增加了一個(gè)男孩——我的大弟。1949年1月,父親所在部隊(duì)到達(dá)安徽明光做渡江前的準(zhǔn)備,母親仍在山東的留守處。她快臨產(chǎn)了,按照當(dāng)時(shí)的規(guī)定,她必須在留守處待產(chǎn),這樣不僅有人照顧,而且不會有危險(xiǎn)。但是母親放心不下父親,不愿意獨(dú)自待在后方。倔強(qiáng)的母親不顧勸阻,決定從山東趕到安徽前線。
行程中的一天晚上,須換乘小船,母親挺著大肚子小心翼翼地跨上小船,但是進(jìn)船艙要從一條窄窄的梯道下去,梯道的進(jìn)口特別小,挺著大肚子的母親怎么也進(jìn)不去,她索性脫掉軍大衣,可依然難以躬身進(jìn)入船艙。無計(jì)可施下,她蓋著軍大衣在船板上睡了一夜。嚴(yán)冬的夜晚,北風(fēng)料峭,寒氣逼人,醒來時(shí),大衣已經(jīng)被夜霜染得雪白。就這樣艱難跋涉了20多天,母親終于到了明光前線,來到了父親身邊。6天以后弟弟順利降生,父親給這個(gè)孕育在山東臨淄,降生在安徽明光,懷胎十月都在征戰(zhàn)途中的男孩取名為淄明,象征著父母征戰(zhàn)倥傯,迎接光明的那段艱難歲月。
外公眉開眼笑地抱起他的孫兒,看著三代同堂的喜慶場面,臉上浮現(xiàn)出由衷的喜悅。多年來,外公燒香求佛,為我母親祈禱平安。如今全國解放了,女兒女婿回來了,還生了個(gè)男孩,使得一生沒有兒子的外公格外高興,短短幾天竟然胖了一圈。他重新為女兒女婿擺婚宴,慶祝全家在勝利的鑼鼓聲中團(tuán)圓。
“四害”肆虐,六載生死兩茫茫
新中國成立以后,父親和母親共同戰(zhàn)斗在江蘇公安戰(zhàn)線上,為鞏固新中國秩序,肅清殘余敵對勢力,維護(hù)社會治安,保障中央首長和外國元首到訪安全,培養(yǎng)公安人才等,做出了杰出貢獻(xiàn)。1955年初,父親出任江蘇省公安廳廳長兼黨組書記。考慮到省公安系統(tǒng)有不少是夫妻倆在一條戰(zhàn)線工作,為利于開展工作,父親提出,處級以上領(lǐng)導(dǎo)的夫妻工作必須回避。父親勸母親帶頭調(diào)離公安戰(zhàn)線去文教系統(tǒng)工作,母親理解并支持父親的工作,帶頭從南京公安學(xué)校副校長任上先后調(diào)華東水利學(xué)院和南京師范學(xué)院擔(dān)任院系總支書記。
至今使我記憶猶新的是,1967年的夏天的一個(gè)傍晚,我們?nèi)胰讼裢R粯訃谠鹤永锍酝盹垼蝗粋鱽怼斑诉恕钡那瞄T聲。一伙氣勢洶洶的造反派闖進(jìn)門來開始抄家。在此之前,在與廳領(lǐng)導(dǎo)談起社會上紅衛(wèi)兵抄家時(shí),父親曾明確指出,有些抄家的紅衛(wèi)兵,特別是有的高干子弟,借“破四舊”的名義中飽私囊,他憤怒地說:“現(xiàn)在還要偷嗎?只要有個(gè)紅袖套,到人家拿就是了。”沒有想到抄家的事情卻發(fā)生在自己的家里!
真是天有不測風(fēng)云,“文革”的濁流滾滾而來,首先受到?jīng)_擊的就是公安政法系統(tǒng)。江青曾經(jīng)十多次在公眾場合叫囂要“砸爛公檢法”。身為公安廳長的父親首當(dāng)其沖,不僅失去了工作的權(quán)利,而且漸漸失去了人身自由。起初白天被軟禁在機(jī)關(guān)一所小房子里“學(xué)習(xí)反省”,晚上則可以回家“思過”。在此期間,母親給予父親很大的精神安慰。母親經(jīng)常穿得衣衫齊整出入公安廳大院,有時(shí)直入食堂在眾目睽睽下和父親一起就餐,和父親談笑如常,甚至迎著那些異樣的目光相互對視,毫不畏懼,對造反派表示了最大的蔑視。
母親堅(jiān)強(qiáng)地對我們子女說:“造反派想搞得我們難過,我偏不難過,在他們面前我們不能有絲毫落魄的樣子。”在那是非顛倒的年頭,母親給予父親最大的支持是精神上的鼓勵(lì),傳遞抗拒邪惡的力量,并在苦難面前擔(dān)負(fù)起支撐整個(gè)家庭的責(zé)任,給心靈受到戕害的孩子們以最大的愛心。
更加嚴(yán)厲的迫害,隨著運(yùn)動的深入撲面而來。1968年初,江青在一次群眾集會中點(diǎn)名誣陷父親,言稱有人揭發(fā)父親擅自銷毀敵偽檔案(其實(shí)那是根據(jù)公安部的要求,在部里派員監(jiān)督下銷毀的檔案副本和一些無關(guān)緊要的資料,全部有案可查),并在3月用專機(jī)押送父親到北京關(guān)押。
誰也沒有想到,這一關(guān)就是7年!整整7年,父親也沒能回家!此后,造反派曾多次催促母親搬家,均被嚴(yán)詞拒絕,她堅(jiān)定地回答:“要我搬家,除非用八抬大轎來抬!”
這就是我那堅(jiān)強(qiáng)而又充滿柔情的老媽媽。此后,3個(gè)弟妹全部下放到農(nóng)村插隊(duì),在體育學(xué)院附中上學(xué)的我也去了工廠,只有節(jié)假日全家才能團(tuán)聚在母親周圍。
當(dāng)時(shí),軍管人員經(jīng)常上門和母親“促膝談心”,要求母親和父親劃清界限,母親卻淡然一笑地反問:“洪沛霖同志還是不是共產(chǎn)黨員?黨籍有沒有被開除?”對方回答“沒有”。“那么你們叫我怎么和一個(gè)共產(chǎn)黨員劃清界限,劃清什么界限?!”
兩名軍人呆坐片刻無言以對,只能悻然而去。
事后得知,父親是在江青指使下被關(guān)進(jìn)監(jiān)獄的,同時(shí)被押往北京的還有江蘇省分管政法的省委副書記李士英。說來說去,還是因?yàn)榻喈?dāng)年在上海那段見不得光的歷史。因?yàn)槟切n案都封存在上海市公安局,江浙滬公安系統(tǒng)負(fù)責(zé)人來往密切,江青惟恐這段歷史被曝光,因此對知情者進(jìn)行了殘酷打擊,無情迫害,亟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關(guān)押的理由是所謂銷毀敵偽檔案和“竊聽器”事件之類的問題,還多次逼供、指供、誘供,希望父親提供“炮彈”,打擊公安部領(lǐng)導(dǎo),被父親嚴(yán)詞拒絕。他寧可被關(guān)押3天不給水喝,也絕不誣陷上級領(lǐng)導(dǎo),體現(xiàn)了一個(gè)共產(chǎn)黨員的堂堂正氣。
整整6年時(shí)間,全家人都不知道父親的生死和下落。
在令人心碎的牽掛和煎熬中,全家人度過了一段漫長而無望的歲月。1972年冬天,一縷微光終于照亮了全家人暗如死海的心靈。父親還活著!全家人可以去和父親見面了!打來電話的是中共中央專案組第二辦公室。
按照和二辦工作人員的約定,母親帶著我的3個(gè)弟妹手持《人民日報(bào)》在北京火車站出站口和一位同樣手持《人民日報(bào)》的年輕軍人接頭。母親后來調(diào)侃說,這倒很像是當(dāng)年他們地下黨的接頭方式。隨后他們上車從北折向東,穿越北京城,來到東城區(qū)一所由學(xué)校改造成的臨時(shí)監(jiān)獄。
在關(guān)押地的會見室里,父親和母親及弟妹們終于團(tuán)聚。母親仔細(xì)端詳著父親,僅僅6年時(shí)間,父親蒼老了許多,原來濃密堅(jiān)硬的黑發(fā)變得稀疏花白,原來瘦瘦的、有彈性的臉頰,現(xiàn)在變得皺紋叢生,顴骨高聳,瘦弱不堪,走路輕飄飄的像是踩在棉花上,隨時(shí)可能被風(fēng)吹倒的樣子……
一陣心酸涌向心頭,但是堅(jiān)強(qiáng)的母親硬是忍住淚水,沒有流出來。那天父親穿著一件洗得發(fā)白的軍用舊棉襖,下身穿著洗得干干凈凈的藏青色棉罩褲:這條褲子是母親親手為父親做的,看來已經(jīng)很長時(shí)間沒有穿了,今天特意穿在身上,從細(xì)微處表達(dá)著對親人們的無盡思念。整個(gè)會見過程中父母親硬是裝著什么事也沒有發(fā)生過的樣子,絕口不提雙方遭受的磨難,努力克制著彼此內(nèi)心中情感上掀起的巨大波瀾,沒有掉一滴眼淚,只是以頑強(qiáng)的意志、鎮(zhèn)靜堅(jiān)定的表情給對方以抵抗邪惡的勇氣。
在黑暗中期盼光明的信心油然而生,為了家庭的再次團(tuán)圓,母親鼓勵(lì)父親一定要活下去。
1974年春天,父親被押解回江蘇高淳花山勞改農(nóng)場繼續(xù)關(guān)押軟禁,但是生活條件改善了許多,行動上也相對自由。母親和我們可以經(jīng)常去探望父親,甚至有時(shí)可以和父親去山林散步。
支撐著父母走過這段艱難歲月的是他們對黨和人民正義事業(yè)的堅(jiān)定信念,夫妻間生死相依的深厚情感以及對孩子們的責(zé)任親情。
主審江青,以正壓邪斗智斗勇
苦海茫茫終有岸,烏云滾滾終放晴。粉碎“四人幫”以后,父親的冤案得到徹底平反,并且很快恢復(fù)了工作,全家歷經(jīng)劫難后終于團(tuán)圓,整個(gè)小院一片歡樂。
為了把失去的時(shí)間奪回來,父親不顧自己年邁多病,全身心地投入到撥亂反正的工作中去:平反冤假錯(cuò)案、整頓社會治安、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狠抓公安隊(duì)伍建設(shè),完善社會主義法制。
晚年最值得書寫的是他奉命主審江青。
由于在“文革”中遭到長期關(guān)押、備受折磨,父親當(dāng)時(shí)的健康狀況已經(jīng)十分糟糕,患有肺結(jié)核病和嚴(yán)重的哮喘,但是接到任務(wù)后,母親還是愉快地為父親收拾行裝,送他踏上了北去的征程。在他們看來,這是祖國和人民交給父親的光榮任務(wù),是對父親政治上最大的信任,必須不折不扣地圓滿完成。
據(jù)父親說,剛開始審訊時(shí),江青披件大衣,一到審訊室就趾高氣揚(yáng)地坐下,跟父親他們預(yù)審組同志對著干。后來,父親和公安部副部長凌云商量,首先要打掉江青自命不凡的臭架子才能正常開展預(yù)審工作。應(yīng)該給她立個(gè)規(guī)矩:一是大衣要穿就穿好,不穿就拉倒,放到一邊,不能隨便披著;二是押她到審訊室門口時(shí),押解員要喊報(bào)告,叫進(jìn)來,才能進(jìn)來,進(jìn)來以后,讓她規(guī)規(guī)矩矩地站在那兒,允許她坐時(shí)她才能坐。對待她,就得立規(guī)矩,打掉她的氣焰。
開始審理時(shí),斗爭就十分激烈,江青自恃身份特殊,端著架子,刁蠻耍賴,氣焰囂張。父親領(lǐng)導(dǎo)預(yù)審組在充分閱讀、研究大量資料的基礎(chǔ)上,先后調(diào)查了汪東興、王光美、王海容、趙丹、黃宗英以及陳伯達(dá)、戚本禹、遲群、謝靜宜等幾十名當(dāng)事人和知情人,獲取了大量的人證、物證及書證。在此基礎(chǔ)上,根據(jù)《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相關(guān)法律規(guī)定,父親親自制定審判原則和方案,在不涉及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不涉及黨內(nèi)路線斗爭錯(cuò)誤的前提下,以《憲法》和《刑法》為武器,主攻江青涉嫌違法犯罪的事實(shí)。
父親作為公安戰(zhàn)線上的老戰(zhàn)士,對于預(yù)審的經(jīng)驗(yàn)是十分豐富的。江青越是對著干,越是胡攪蠻纏,父親就越是“較真兒”。剛開始審訊時(shí),兩人每次都要先吵一陣子,父親以洪亮的嗓音壓住江青的囂張氣焰。有一次江青罵父親是“瘋狗”,父親則針鋒相對地說:“我這只瘋狗就是咬你這只癩皮狗的!”后來江青軟了,說:“咱們還是好好談吧。”這樣,父親才按計(jì)劃把要問的問題問完了。父親憑著對黨的忠誠和豐富的斗爭經(jīng)驗(yàn),終于制服江青,迫使她老老實(shí)實(shí)交代問題。江青后來對監(jiān)管人員說:“這個(gè)人很厲害,一看就是個(gè)搞公安的。”
在主審江青的8個(gè)月里,時(shí)年63歲的父親率領(lǐng)預(yù)審小組,殫精竭慮,晝夜奮戰(zhàn),由于工作緊張,操勞過度,一度哮喘病復(fù)發(fā),經(jīng)過搶救,病情稍有緩解,身體剛恢復(fù)父親就又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對審訊組的同志說:“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tuán),是全黨全國人民關(guān)心和舉世矚目的大事,江青是主犯,我們這部分任務(wù)要抓緊完成,決不能影響審判工作的全局,要像打仗那樣,到了關(guān)鍵時(shí)刻就是要拼。”
1981年1月25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依法判決江青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
1981年春節(jié)前夕,離家8個(gè)月之久的父親帶著勝利的喜悅,返回南京。那年春節(jié),闔家團(tuán)圓,充滿著歡聲笑語,全家人饒有興趣地聆聽了父親在主審江青過程中的那些逸聞趣事,那真是全家最高興的日子。
(本刊節(jié)選)
〔本刊責(zé)任編輯 袁小玲〕
〔原載上海人民出版社《兵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