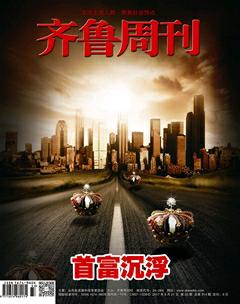黃三角富豪群
江寒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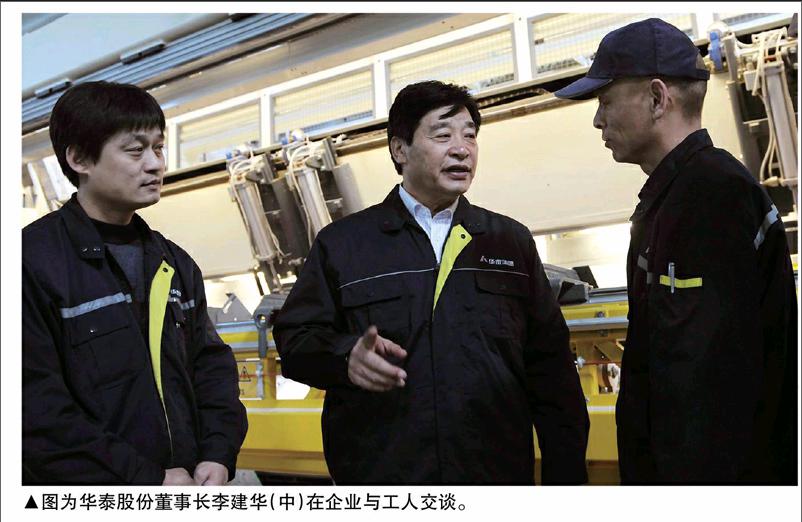
與長三角、珠三角等著名的城市群經濟帶相比,黃三角的知名度略顯一般,其經濟體量與所含城市的知名度與前兩者相比,不在一個層級上,其對一省經濟的帶動,客觀而言,也很難說起到了龍頭作用。
不過,這片共和國最年輕的土地上,蘊藏著極為猛烈的造富動能,在山東版富豪榜中,以東營、濱州為代表的黃三角城市,其所誕生富豪群,成為了魯商板塊中數量最為龐大的一極。
產業分布
山東哪里生產的富豪最多?答案不是省會濟南,也不是準一線城市青島,而是來自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的濱州和東營兩市。
在山東商報編制的歷屆《山東富豪榜》中,以往的6屆富豪榜,東營都以微弱優勢力壓濱州,蟬聯山東造富人數最多的城市,而在2016年,濱州91人上榜,比東營多19人,成為名符其實的山東造富第一城。在2016年的財富總額排名中,東營衛冕冠軍寶座,創造財富總額3515.51億元,占上榜富豪財富總值的18.03%,比排名第二位的濱州多出737.67億元。
同時,作為山東最能造富的縣,鄒平以造富1616.82億元也連續第三屆登上該榜單縣域造富榜首,而鄒平縣也正是首富張士平家族所在地。
2016年,濱州博興縣以1017億元的造富值超過東營廣饒縣成為第二富豪縣,入榜富豪數26人。而廣饒縣以955.79億元的財富總額排在富豪縣第三的位置,擁有富豪數9人,而這三座縣城,無一例外,都位于黃三角高效生態經濟區中。
山東是縣域經濟大省,黃三角地區發達的縣域經濟,正在傳統的濟青煙地區外,創造新的區域經濟引擎。
再往下探究,在更為基層的村域經濟中,黃三角也大放異彩。鄒平縣的西王村,單上市公司就有4家,這個數目甚至要超過一些縣級市。
西王村掌門人王勇是西王集團的第一大股東,通過西王集團,他控制了3家上市公司,西王食品、西王特鋼和西王置業。
但這還不是全部,西王村另一家上市公司長壽花食品也同樣出名,就算你沒吃過他們公司的長壽花玉米油,你一定對范冰冰代言的那個黃燦燦的廣告印象深刻。
從產業分布來看,黃三角富豪們大多集中分布在石化、紡織、造紙、橡膠等傳統產業領域,客觀而言,這些產業顯得并不那么高大上,屬于資源密集型產業,以高耗能、高污染而著稱。
不過,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些領域的企業家搶占了政策機遇,塑造了山東產業地理。
以山東“地煉企業”為例,其發展起源于1998年我國石油石化行業的宏觀調整,在山東境內“地煉企業”主要集中于東營、菏澤、淄博、日照和濱州5市,其總能力占全省地方煉化產業的93.6%。其中,位于黃三角的地煉企業又占了其中大部。
其所催生出的富豪有:濱州博興的京博控股董事長馬韻升、東營的中國萬達集團董事長尚吉永、東營富海集團羅冰、東營萬通石化的王軍、濰坊壽光魯清石化王學清、東營中海化工劉士勤、東營海科化工楊曉宏。
創業路徑
盡管創業路徑不同,不過這些黃三角富豪們,無一例外的都可以用“白手起家”來描繪其財富的積累過程。在2016年“全省加強企業家隊伍建設工作會議”上,時任省長郭樹清認為,山東的發展得益于企業家的勤勞智慧和創造性勞動。
“山東有很多企業家是‘白手起家,以前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與基層干部。但是他們趕上了社會潮流,敏銳地捕捉到了市場機遇,不斷推動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把企業從很小的手工作坊發展成了現代化集團,把產品從產業鏈最低端做到了高端甚至是最高端。”華泰集團董事長李建華就是這其中典型的代表。
李建華的創業起步都非常艱苦。他是農民家庭出身,沒有經過高等教育,很早便參加了工作。
“我是農民家庭出身,五六十年代農民家庭都很窮。14歲那年,父親得了胃潰瘍,沒錢治療去世了,給我心里留下了創傷。大哥在外地當兵,就靠我母親支撐著家庭。為解決生計難題,15歲就跟隨村里的人推著小車上臨淄、濰坊,把生產隊每年每人分的60斤小麥、100斤玉米,換成地瓜干和煤,就是為能多維持幾天生活”。李建華說,“高中畢業后,我在生產小隊當會計,那時的理想就是當兵、當工人。”
1976年,靠拼湊起來的舊設備,鎮辦造紙廠成立,李建華的工人夢想成真,成為一名企業職工,進廠后,領導安排他帶領幾十個人去外地學習。李建華是一個懂得珍惜的人,他暗下決心,一定干出樣子。“在外地學習期間,住在菜園子里、打地鋪,沒白沒黑地學,沒白沒黑地干,不知道苦和累,學習回來,立即進入造紙、制漿、鍋爐的緊張安裝中。每天干到夜里9 點多,有使不完的勁。就是靠一根筋、一股勁、鼓著一口氣,日夜奮戰,用一年的時間,硬把拼湊的設備安裝起來。”
1983年,李建華低價購買了倒閉企業設備。拆設備時,正是寒冬臘月、地凍三尺的季節,為了節省資金,他和職工們一起挖地三尺,把埋在地下的大大小小管道全部挖出來;沒有起重設備和吊車,硬是靠人工把六七噸的蒸球拆下來。不到一年就投產,公司產能擴大了5倍,第二年實現利潤100多萬元。1993年底,華泰以150萬元購買了江蘇無錫一套價值六百多萬元造紙設備,李建華指揮 “十八勇士” 下江南拆設備。對方安裝這套設備用了足足五年時間,他們只用了25天就拆完運回,不到8個月就安裝完畢,當年就盈利400多萬元,第二年盈利1000多萬。
分析山東富豪的創業歷程,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富豪的企業均由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國有小型企業改制而來。以黃三角的地煉企業為例,京博控股由國有校辦工廠改制創業而來,與王健林的萬達集團名稱相近的中國萬達集團,由墾利縣一家安裝公司發展、改制而來。王學清的魯清石化由一家鄉集體企業改制發展而來。退伍軍人劉士勤的中海化工由一家軍辦化工企業改制而來,楊曉宏的海科化工同樣也是由地方小型國有企業改制而來。
還有一部分富豪,在當年的下海大潮中,辭去公職,投身地煉行業。比如,富海集團的羅冰辭去公職,從最初的運輸經營發展到如今以石化為主的多元化企業。
自主創業的則有東營萬通石化的王軍。王軍是退伍軍人,在1998年時融資500萬,興辦萬通石油化工廠,成為山東民營投資煉油行業的“第一人”。
這些企業之所以發展起來,一方面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源于近乎摳門的精細化管理。在這一點上,無論企業規模大小,他們與首富張士平的魏橋集團有著相同的管理之道。
比如在京博石化,流傳著董事長馬韻升的一句話:“垃圾和廢資源是好東西放錯了地方”,他要求京博“利用三廢而非治理三廢。”
“每降一分錢成本,就是獲得一分錢利潤。”一位地煉企業管理人員表示,“在運輸汽車尾部卸油管纏上塑料袋,將卸車時殘留的原料油回收使用”,“抓好化工輔料管理,每套裝置每年節約數百萬元”;“壓縮各項費用開支,降低財務費用,優先清還高利率貸款”等等這些措施讓企業在夾縫中生存下來。
他們的執行力也讓一些國企嘆為觀止。比如作為中國萬達集團全資子公司的山東天弘化學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總投資43億元,建設了9萬噸乙丙橡膠及500萬噸石化聯合裝置,是東營港經濟技術開發區內建成投產最大的石化項目。該項目僅用了15個月的時間便建成投產,原油綜合加工能力達1000萬噸,年可實現銷售收入330億元。
這樣的發展模式不由得讓我們想起魏橋集團自建發電廠實現盈利的案例,它從一個側面展示出了民營企業的強大生存能力:只要政策給予一定的空間,其便能在夾縫之中獲得長足發展。
低調的商業性格
低調是魯商根深蒂固的商業性格,在這一點上,黃三角富豪們也與張士平一樣,保持著甚低的曝光度。這或許與其大多從事傳統產業有一定的關系,他們的商業哲學更多地體現在成本控制上,而不是天花亂墜的模式上。
甚低的曝光度,使得一些在行業內頗具分量的企業不為大眾所熟知。黃三角富豪們對自己公共形象的打造也似乎不太上心。比如東營是中國輪胎產業聚集區,但你若問一個普通人,東營最著名的輪胎富豪是誰,他多半答不上來。即便是山東最為著名的輪胎大佬丁玉華,其曝光度也不過是在去年上市時,在財經圈掀起一定的波瀾。
除丁玉華外,位于東營的永泰集團董事局主席尤學中以及其擔任總裁的兒子尤曉明,他們曝光率還比較高。2013年,永泰集團與考普萊國際控股公司簽署了并購協議。此刻,一場民營企業海外并購百年老字號的好戲正在上演,這是東營建市以來本地民企創造的最大一起海外并購案例,而這場好戲的“導演”就是永泰集團董事長尤學中。
作為“50后”,尤學中經歷過建國后一系列發展時期,最困難的時候他甚至還去東北“要過飯”,他也曾經在南京軍區60軍179師服役5年,1979年轉業退伍后,他回到家鄉大王鎮供銷公司任總經理,也是在這里,他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時代。從為勝利油田服務的鄉鎮企業起步,尤學中經歷過鄉鎮工廠紅火的股份制改造和破產倒閉,最終,尤學中接過“爛攤子”,成就了一個總資產50多億的企業。
作為80后的“二代”企業家,尤曉明與父輩們相比,更加活躍。他更愿意向公眾表達自己的商業觀點,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自己推崇無為而治。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習近平主席訪英期間,作為中國在英投資企業代表、山東唯一的民營企業代表,尤曉明參加了中英工商峰會、倫敦金融城接待晚宴、習近平主席接見中資企業代表并合影三項重要活動。
與以上幾位相比,同樣是業界強軍的山東恒豐橡塑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圣法(東營)、興源輪胎董事長宋文廣(廣饒)、盛泰集團董事長宋世德(廣饒)、濰坊躍龍橡膠董事長劉新剛、山東銀寶集團董事長劉永華(壽光)等人,都頗為低調,很少有關于他們的新聞。
山東永盛橡膠集團董事長劉占一(廣饒),在2016年4月份上過一次新聞,不過曝光理由比較奇葩,“因尋釁滋事被當地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15日。”
也有一些企業開始注重參與其社會公共品牌形象。 2017年4月,本刊記者曾跟隨山東融媒體團走進京博控股。客觀而言,作為一個以化工為主業的企業,京博敞開大門宣傳自己企業品牌形象之舉頗有時代新風。據企業負責人介紹,這項活動已舉辦多年,由此,京博控股的“仁孝”企業文化也漸漸被大眾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