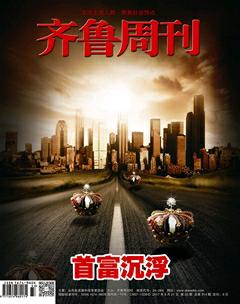史偉云:大師的“仁信”之道
賈文佳

本刊專訪中華醫學會角膜病學組組長、山東省眼科醫院院長——
作為中國眼科學界的領軍人物之一,史偉云一直致力于角膜病臨床及相關基礎研究工作,是國內極少獨立完成角膜手術超過1萬例的專家。
在眼科醫學這條歷史長河中,他已行走了30多年。中華醫學會角膜病學組組長、山東省泰山學者攀登計劃專家、山東省眼科研究所所長、山東省眼科醫院院長……諸多榮譽背后,史偉云始終堅持著他的“仁信”之道,默默付出、披荊斬棘而又自得其樂。
角膜供體之困與1萬例移植手術
8月16日上午,記者見到了剛剛從牛津大學講學歸來的史偉云。“這次談的還是關于角膜病的課題,現場討論非常熱烈。”記者面前的史偉云儒雅而自信,渾身散發著學者氣質。
采訪伊始,史偉云迅速切入了自己專注研究二十多年的角膜病學。“角膜病是僅次于白內障病的第二大致盲眼病。我國約有400萬名“角膜盲”患者。如能用健康透明的角膜手術替換,患者的視力是可以恢復的。”
但是,目前國內每年僅能實施人體捐贈的角膜移植手術不到3000例。“很多角膜病患者在等待角膜供體時病情加重,往往失去手術的最佳時機,甚至帶著遺憾走到生命的終點。”
關于異體角膜捐獻,我們目前面臨一個無奈的現實。
以山東省為例。據山東省紅十字會統計,截至2016年12月,全省累計登記角膜捐獻志愿者為6267人,實現捐獻903人。其中,2016年角膜捐獻登記志愿者為478人,實現捐獻153人。
可以說,隨著對角膜捐獻的認知度越來越廣,山東省登記的角膜捐獻志愿者也在逐年增多。“盡管如此,省內的捐獻量遠遠無法滿足需求。山東是角膜病發病大省,幾乎每一對捐獻出的角膜都有上百名患者排隊等候。”史偉云說。
一方面,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國捐獻意識淡薄。另一方面,目前也沒有相關法律支持角膜捐獻。史偉云告訴記者:“在美國,每年做角膜移植大約4萬例,但每年能取到的角膜供體就有10萬多例。因為很多州的法律都規定,只有同意捐獻角膜者,才給頒發駕駛執照。”
“其實角膜捐獻并不可怕,現在采用最新的方法,只取角膜,不損傷眼球,整個過程也只需要5-10分鐘。”史偉云說,取下來的角膜要立即放入角膜保存液中保存,看上去很像泡在護理液中的隱形眼鏡。保存在營養液中的角膜可以在7天內進行移植手術。
“我們接受的信息90%以上來自眼睛,患者把這么重要的東西交到我手上就是對我的信任,這種信任是不能辜負的。”在角膜供體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史偉云就想辦法節流——根據患者角膜的損傷程度來進行移植修補,“一個角膜甚至可以做四五臺移植手術,既節省了角膜,又減少了手術并發癥。”
在史偉云醫治的患者中,有80多歲被家人攙扶而來的徐州老太太,也有來自西藏楚布寺的活佛拉巴大師,還有很多從黑龍江、浙江、江蘇等地慕名趕來。目前,史偉云已累計讓全國30余個省市的1萬多名疑難角膜病患者復明,成為國內極少獨立完成萬余例疑難角膜移植手術的眼科醫生。
從“半路出家”到蜚聲國際
時光倒流至上世紀70年代,史偉云最不喜歡的地方就是醫院,“里面總是彌漫著一股青霉素的味道。”
1977年,18歲的史偉云參加高考制度恢復后的第一次考試,填報的志愿是化工,結果錄取的卻是醫學專業。上學期間,他多次想要調換專業都未能遂愿,畢業后,他被分配到一家縣醫院成為一名外科醫生。
“那家醫院的院長是眼科專家,可能覺得我有一點天分,就問我愿不愿意轉到眼科,做他的助手。”至此,史偉云開始與眼科結緣。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竟然喜歡上了這個行業,其實,很多快樂都是患者給的。患者重見光明的那些驚喜瞬間、眼睛里再次綻放出的光彩帶給我很大的成就感。”
衛校畢業十年,史偉云考取了中國工程院院士謝立信的研究生,先后獲碩士和博士學位。2000年,史偉云赴美國跟隨世界角膜病大師Herbert Kaufman繼續角膜病的基礎研究工作。
回憶起當年美國求學的經歷,史偉云依然印象深刻。“人的角膜厚度只有0.5毫米,做角膜移植手術至少要在上面縫16針。”為了將手術能力練得“爐火純青”,他向小鼠角膜移植發起了挑戰。“小老鼠的角膜直徑只有3毫米,厚度只有0.1毫米,這上面我要給它縫8針,比人眼難多了。”
多年的眼科臨床診治和基礎研究,遠赴英美的海外求學經歷,讓史偉云從一個“半路出家”的眼科助手,成長為一名擁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和嫻熟手術技巧的頂尖專家。
為了解決角膜供體奇缺的問題,史偉云還創造性地與中國再生醫學國際有限公司合作完成全球首個生物工程角膜研究。“簡單來說,就是用豬角膜基質經過脫細胞和去抗原的處理后,來替代人角膜基質。”史偉云說:“生物工程角膜保留了天然角膜基質膠原蛋白結構及透明性,生物相容性好,安全性高,能與周圍組織快速整合,移植角膜透明,患者視力快速恢復。”
作為一項擁有完整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劃時代產品。2015年4月22日,全球首個生物工程角膜獲批上市,極大地改變了我國的角膜移植手術角膜供體奇缺的困境。
隨后,專業人才奇缺又成為阻礙角膜移植手術順利開展的重要因素。“目前真正能做角膜移植手術的醫生不足50人,具備相關條件的醫院也就三十家左右,與上百萬“角膜盲”患者的需求相比,缺口實在太大。”史偉云強調:“人工生物角膜與捐獻人角膜在移植技術上有著明顯的區別,不論從手術適應癥到圍手術期處理都有著獨特的技巧。”
作為中華醫學會角膜病學組組長,史偉云認為自己有義務去推廣傳授相關技術。為此,這些年來的每個周末,史偉云都奔波在全國大大小小的城市講學布道。“有時候一個周末跑三四個城市,希望醫生通過培訓,回到醫院后就可以進行角膜移植手術。”
史偉云還建立了國際角膜移植手術培訓中心。去年10月,史偉云在哈佛大學醫學院麻省總醫院分享“中國首個人工角膜的研制歷程和心得”,1個多小時的英語演講震驚四座;今年3月,史偉云就生物工程角膜相關臨床問題,接受了美國哥倫比亞電視臺的專訪。從事多年醫療采訪的美國記者十分驚訝并贊嘆不已:“觀看史院長做手術就像在欣賞一場精彩的演出。”
文化基因與人文情懷
專注于眼科醫學30多年,史偉云坦言最喜歡的還是臨床和科研。他曾擔任國家“863計劃”、“973計劃”項目負責人并榮獲山東省科技進步一等獎四項、國家級科技進步二等獎兩項。“我90%的工作時間都在臨床和科研上,做行政就完全是工作時間以外來做了,行政對我來說是副業。”
實際上,所謂“副業”,史偉云也干得風生水起。
2003年底,山東省眼科醫院創立,“那時候我們在電力醫院租的房子,醫生護士都是從青島帶過來的。”現在,醫院已經有業務用房3萬平米,開放床位200張,醫生護士200余人,成為國內最大的集醫療、教學、科研、防盲為一體的國有省級三級甲等眼科專科醫院之一。
“醫院的核心在人才,不在大樓。”作為院長,史偉云十幾年來始終致力于醫院的人才隊伍建設。目前,醫院的醫師總數70余人,高級職稱醫師15名,30%以上醫生具有國外留學經歷和博士學歷,碩士及以上學位人員占比超70%。
在山東省眼科醫院,似乎有一種看不見的文化基因,在他們的血液中流動,內化為他們所堅守的人文情懷,外化成他們所遵循的學術規范。
談及紅包現象,史偉云顯得有點激動,“我從來不收紅包,也要求醫院的醫生一律不準收紅包。”醫生是個良心活兒,史偉云說,他最反感做手術收紅包行為。他和同事們一直堅持一個慣例,只要符合手術條件的患者都要安排手術,而且一般不會超過兩天,有時即便加班也要把手術做完。
角膜移植手術可謂“眼球上的藝術”。“手術需要在顯微鏡下放大8-9倍進行,只有控制好自己的手,才能將移植留下的疤痕控制在最小,達到最好的復明效果。”為此,史偉云行醫30多年來始終極少飲酒。
“醫學是一門經驗科學,醫患關系不能是商業關系,而應該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是一種相互的信任。”史偉云表示:“如果病人對我完全信任,那么即使冒一定風險我也一定要盡全力把病人治好。”
目前,史偉云每周有一次門診,至少50臺手術。只要沒有別的工作安排,史偉云幾乎每天7點就到醫院上班。“每天晚上7點能下班就不錯了”。而周末基本都是出去交流學習,“周末的活動已經安排到了今年年底。”
臨床、科研、行政、講學……史偉云的時間表密集而充實。他坦言自己沒有時間培養興趣愛好,“我曾經報名3次學車,全都過期了,根本就沒有時間去學。去年年初買了車放在那,連方向盤都沒有去摸過。”
生活中的史偉云低調謙和又不乏幽默感。采訪結束,他還不忘提醒:“我們每個人都要保護好自己的眼睛,愛護好自己的角膜,要盡量防止角膜外傷。”
《論醫》中說:“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作為中華醫學會角膜病學組組長、山東省眼科醫院院長、從事眼科基礎研究及臨床診治工作30 余年的頂級專家,一路走來,史偉云始終堅持著他的“仁信”之道,默默付出、披荊斬棘而又自得其樂。
——山東省濟寧市老年大學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