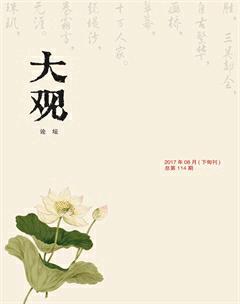評議李白《草書歌行》的真偽問題
摘要:自宋敏求將《草書歌行》一詩收入《李太白文集》中,北宋以來文人學者們頗多爭議。本文大致列舉歷史上前人對此詩真偽的看法,并試從宗教、酒和二人的性情方面,探討二人交游的可能性。
關鍵詞:李白;懷素《草書歌行》真偽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箋麻素絹排數廂,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后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如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遍。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全唐詩》卷一六七)
這首《草書歌行》贊嘆懷素的草書“天下稱獨步”,氣勢如萬馬奔騰,“字字飛動,圓轉之妙,宛如有神”(《宣和書譜》)。但自從宋敏求將《草書歌行》一詩收入到《李太白文集》中,北宋以來文人學者們對此頗多爭議。李白作為唐代著名的天才詩人,所作詩歌極多,有“李白一斗詩百篇” (杜甫《飲中八仙歌》) 之稱。但由于李白長期處于漂泊流離的生活狀況,加之其晚年經歷戰亂及牢獄之災,造成其詩大量散佚,至北宋樂史編輯《李翰林集》、宋敏求編撰《李太白文集》,方廣為搜集,但《李太白文集》一經面世,就不斷受到人們質疑,其中就包括這首《草書歌行》。
歷史上比較著名的論調基本如下:
蘇軾最早提出李白的《草書歌行》是偽作這一觀點。他在《東坡題跋》(叢書集成本)卷二“諸集偽謬”條中說:“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詞格。”但仔細追究就會發現,蘇軾沒有詳細論證為何這些詩“皆貫休以下詞格”,也沒有說出讓讀者信服的理由,因此我們對蘇軾是從哪個角度認為這首《草書歌行》是偽作的也并不清楚。
陸游在《入蜀記》中記載:“或日十詠及歸來矣、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他們都因為舊集沒有這首詩而提出疑問,可是我們又如何得知這里所言的“舊集”根據的是哪個集呢?
相比之下,朱諫從詩的風格分析此詩,頗為在理。他在《李詩辨疑》中說:“此詩格力雖不足,然辭氣輕順,頗有音節。較于李白,固所不逮,猶不失為唐人風調也。”
胡震亨在《唐音癸籤》卷三十二稱:“太白集亦大有偽詩攙入。”所舉例子就是蘇軾曾指出的幾首詩為例證,其中就包括《草書歌行》這首,并在其《李詩通》中將其視為偽作,置入附錄。可見胡震亨并沒有經過自己的考證,只是人云亦云,并無力證,就簡單將這首詩納入偽作行列。
沈德潛在《唐詩別裁》云:“笑矣乎,悲矣乎,懷素草書歌等,皆五代凡庸俗子所擬,后人無識,將此選入。”同樣,沈德潛是從哪個角度指出這些詩“皆五代凡庸俗子所擬”的呢?我們不得而知。
北宋書法理論總集《墨池編》則稱:“此詩本藏真(懷素字藏真)自作,駕名太白者。”認為這首詩是懷素所作,而非李白。此說法倒是頗有新意,可惜缺乏有力論證。
清人王琦按云:“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貶王逸少、張伯英以推之,大失毀譽之實。至張旭與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詩稱詡有‘胸藏風云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數,太白決不沒分別至此,斷為偽作,信不疑矣。”王琦從詩的內容推論此詩不是李白所作,卻并不能使人信服。眾所周知,李白生性不羈,他在寫詩的時候主要是抒發自己當下的內心情感,其詩常是即興創作,隨性而來,如《將進酒》等,如何要求他在創作時兼顧如此多的人情關系?即便李白在詩中借用張旭、公孫大娘二人之名,其目的也絕不是要貶低他們,而是希望借此突出懷素草書的精彩絕倫。
時人詹瑛則從詩中找實證,在《李白詩論叢》中云:“懷素生開元十三年,晚太白二十五歲。今詩中一則云:‘吾師醉后倚繩床,再則云:‘我師此義不師古,太白一生倨傲,斷不至對一少年上人若是之崇也。”李白的倨傲是針對性的,并不是對所有人都倨傲,更不用說是對和李白一樣好美酒,藐成法,目空一切,充滿強烈自信心的懷素了。盡管從年齡上說,二人的確相差過大,但從性格層面來說,二人卻是同類人,李白欣賞懷素的率性,其實也就是欣賞他自己,更何況懷素還是佛門中人,李白將其稱之為“師”又有何不可呢?
詩中又云:“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遍。”詹瑛據此作出批評:“湖南七郡,謂長沙郡、桂陽郡、零陵郡、連山郡、江華郡、邵華郡,此七郡皆在洞庭湖之南,故曰湖南。”他據此而論之曰:“按新唐書方鎮表,廣德二年置湖南節度使,共轄五州,湖南二字用作政治區劃之名,當始于此。至宋太宗置湖南路,始統潭、衡、道、永、邵、郴、全七州,一桂陽監。太白卒于寶應元年,而此詩已有七郡之稱,亦至可疑。”詹瑛從歷史地理角度分析詩中的“湖南七郡”似有道理,但瞿蛻園、朱金城校本則針對這一論證反駁詹瑛:“至詹氏摭湖南七郡之語,謂廣德二年始置湖南節度使,此又過泥。湖南猶江南、嶺南,形之于詩者,非必作為行政區域,唐詩中如錢起之‘湖南遠去有余情,比比也。”可見,詹瑛的解釋并不能使人信服。
李白與懷素二人雖年齡相差較大,但卻同在一個時代,并且在二人之間又有著諸多的因緣際會和性格、身世上的相似之處,那么從宗教和酒這兩個方面著手,也許能看出二人交游的蛛絲馬跡。
一、宗教聯系
佛教東傳之后,經過幾千年的融合,在唐代與中國文化完全融合。懷素幼時好佛,出家為僧,一度客居京兆,與諸多文人交游。唐代詩人又多入于儒、出于道、游乎禪,李白亦如此。李白自號“青蓮居士”,王琦在《李太白年譜》“長安元年”條寫道:“青蓮花出西竺, 梵語謂之優缽羅花,凈香潔, 不染纖塵。太白自號, 疑取此義。”而李白也的確學過佛。他在《贈僧崖公》一詩中就曾回憶其學佛悟禪的那段經歷:“昔在朗陵東,學禪白眉空。大地了鏡徹,回旋寄輪風。攬彼造化力, 持為我神通。晚謁太山君, 親見日沒云。中夜臥山月, 拂衣逃人群。授余金仙道, 曠劫未始聞。”“鏡徹”,瞿朱注曰:“《華嚴經》:觀諸世間大地山河如鏡鑒明,來無所粘,過無蹤跡,”“輪風”,王琦注以“《法苑珠林》依《華嚴經》云: 三千大千世界,以無量因緣乃成,且如大地依水輪,水依風輪,風依空輪。空無所依,然眾生業感,世界安住。”從詩的內容可見,先從白眉空受禪,后遇太山君學佛理的李白是深諳佛典的。
再看《與元丹丘方城寺談玄作》:“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滅除昏疑盡,領略入精要。澄慮觀此身,因得通寂照。朗悟前后際,始知金仙妙。”此詩正是李白對佛教基本人生奧秘的參悟。首句說,覺醒者因為了悟了佛法真諦,感嘆人生即如一場大夢;“騰轉風火來”則是說,世間的一切都是地、水、火、風四大物質假合而成,并無實體。“滅除”句指出,只有滅盡種種無明的疑惑,才能了悟佛法;“澄慮”四句認為,貫通佛家頓悟之學,明心見性,才能領會金仙——佛之奧義。這首詩將佛法妙諦,娓娓道來,顯露出李白的佛教思想。開元十三年( 725) 春三月, 李白出三峽。沿江舟行, 抵江夏。與僧行融“賦詩旃檀閣, 縱酒鸚鵡洲。”李白比擬行融與自己的關系為“梁有湯惠休, 常從鮑照游。峨眉史懷一, 獨映陳公出。”將自己與行融的禪交深情表露無遺,同時我們亦可窺見歷代文人與僧侶的交往對李白的影響。同期,李白還曾與“群公臨流賦詩”贈別林上人,有《江夏送林公上人游衡岳亭》,稱贊這位林上人“落發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秋抵金陵,曾往游城西南隅之瓦官寺,為作《瓦官閣》詩,有詩句“漫漫雨花落,嘈嘈天樂鳴。兩廊振法鼓,四南吟風箏。”“雨花”“天樂”“法鼓”諸般佛教語匯中詩中自然嵌入,了無痕跡,足見李白對一般佛教典籍的熟悉程度。因此“游于禪”的李白與佛教徒懷素是擁有溝通的基本可能性的。
酒對于創作者的意義巨大,它是創作的催化劑,可以激發靈感,可以擺脫俗念。這點在懷素和李白的身上表現的尤為明顯。
懷素喜飲酒,陸羽《僧懷素傳》說懷素“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朱遙《草書歌》云:“連飲百杯神轉工。”錢起詩也說:“狂來輕世界,醉里得真如。”《佩文齋書畫譜》卷三十引《金壺記》說:“懷素嗜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凡一日九醉,時人謂之醉僧書”。由此知酒與懷素草書結下了不解之緣。《書畫匯考》收懷素《酒狂帖》,帖中懷素以“酒狂”自稱。宋代朱長文在《續書斷》中稱懷素的酒量很大,他“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顛狂。”醉意朦朧的懷素“一顛一狂多意氣,大叫一聲起攘臂。揮毫倏忽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翕若長鯨潑剌動海島,欻若長蛇戎律透深草,回環繚繞相拘連,千變萬化在眼前。”極其生動地表現出酒后癲狂的懷素,借酒的神力揮灑出動人心魄的作品。
同樣,李白也是“酒中仙”,他一生好酒未有稍懈。不僅如此,李白還在詩中比較完整地體現了自己飲酒的情態和對酒及飲酒的看法——《月下獨酌四首》: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后各分散。永結無情游,相期邈云漢。在酒精和狂歌勁舞的影響下,詩人想象著自己飄然成仙,和月和影相約在遙遠的云漢相會。不僅狂飲、痛飲,李白還要為自己狂飲、痛飲找到理論上的依據: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圣,復道濁如賢。賢圣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晉書·天文志上》說:“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饗飲食。”(卷十一)《神異經》說:“西北荒中有酒泉,人飲此酒,酒美如肉,清如鏡,其上有玉樽,取一樽,復一樽出,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長生。”(《藝文類聚》卷七十二)詩人說,不光是人喜歡酒,連天地都喜歡酒,否則,天上就不會有酒旗星,地上也不會有酒泉的存在了。天地既然同時愛酒,那么好酒好飲就自然不愧對天地了。在詩人看來,不飲酒既有悖于自然常理,也有悖于人性、人情。《三國志·徐邈傳》說:“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圣人,濁者為‘賢人。”詩人說清如“圣人”、濁如“賢人”的各種酒既已嘗過,那又何必求什么神仙呢?飲三杯即通常理、正理(即“大道”),飲一斗越發順合人事規律(即“自然”)了。既得“酒中趣”,又何必要告訴“醒者”呢?詩人在這里化用陶淵明“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飲酒二十首》其十三)詩意,意在說明悠然自得的“醉”和小心翼翼的“醒”是兩個不相關的世界,不能溝通也沒有必要溝通。但縱觀懷素和李白二人的愛好及對酒的喜愛,我們可以想見這兩個好醉且狂之人,則是不用溝通也能交流的了。原因便在于此二人所飲之“酒”是和追求獨立人格與自由精神緊密聯系的,體現在李白的詩文中就是其詩歌表現出的率性、自然和灑脫,不受理性觀念的約束,體現在懷素的書法中便是其狂草所散發出的大氣磅礴、氣象萬千,這種人手合一、肆意馳騁的狀態充滿了解放精神和超越精神,為此二人所共有。
懷素和李白二人都有著自信、率真、狂放的性格特點,又都有著不如意的坎坷人生。懷素早歲家貧,“幼而事佛”,從小飽嘗酸楚苦澀,即使在成名前后也備受士大夫階層的凌辱和嘲笑。于是他借酒佯狂,見壁即書,為的是表達心中的憤懣和怨氣,卻體現出他的真性情。他的《藏真帖》《自敘帖》《律公帖》《苦筍帖》等風格多樣,但都蘊含著一種超世拔俗、性靈豁暢的氣質。而其代表作《自敘帖》的雄渾摯健、沉著豪邁,則完全是心靈自由奔放的象征,躍動著生命的激情和悲壯,顯示出耿介傲世的獨特氣質。李白則常以管仲、樂毅的政治才能自許,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稱要: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后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一心想要效法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李白卻在實現人生抱負的道路上屢屢受挫,盡管如此,他依舊能做到“不屈己、不干人”笑傲權貴,平交諸侯的真實本色。面對李邕對年輕后輩矜持的態度,他在《上李邕》一詩中回敬道: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時人見我恒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輕年少。表現出李白的自信與傲岸。從這些方面來看,李白與懷素二人是大有可能通過佛家的牽線搭橋,發現并欣賞對方身上的種種個性特點,進而交游唱和,那么宋敏求將《草書歌行》收入《李太白文集》中似乎也沒有什么不妥。
【參考文獻】
[1]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清]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7.
作者簡介:尚夢珣(1992-),女,漢族,安徽合肥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文學碩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