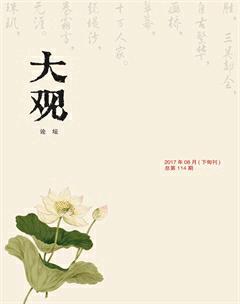溫情書寫下的人性精神家園
劉曉梅
摘要:作家遲子建以女性特有的敏銳、溫情、寬容的胸懷關注并書寫著北國的原始風景和淳樸敦厚的民俗風情。她熟悉世間的悲歡離合,堅定地守護著人類善良的秉性,看似樸素的文字下卻蘊含著脈脈溫情,這種溫情來源于她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理想的憧憬。在小說《白銀那》中,作者用全知視角和日記體交互呼應的方式敘事,溫情書寫的同時用細節來刻畫人物形象,加之樸素的生活化語言,使小說呈現了獨特的創作特色。
關鍵詞:遲子建;白銀那;溫情主義
小說陳述了在我國北部邊遠一個叫白銀那的小村子,遇到千載難逢的特大魚汛,漁汛給村民帶來了希冀的同時,也帶來了鄰里間的抵牾、轇轕和靈魂的紛爭。 黑龍江中的冰排消逝的第二天便來了魚汛,白銀那這個村莊的人們開始拿出了許久不用的漁具,不辭辛苦夜以繼日的捕魚,這些魚給他們平淡的生活帶去了驚喜。他們在漁汛中取得豐收后卻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馬占軍夫婦私抬鹽價,引起了大家的公憤。面對突如其來的漁汛,白銀那沒能及時與外界取得聯系,以至于魚販子沒能及時來收購。鹽價的大肆提高,讓大家的心里充滿了擔憂,因為捕來的魚既沒有魚販子來收購又沒有鹽來腌制很容易就會腐爛,那么他們在漁汛中的辛苦和希望都會付之東流。就在白銀那的村民堅決抵制購買高價鹽的時候,鄉長的妻子卡佳為了不讓魚腐爛獨自一人上山采冰塊,途中遭到熊的攻擊而喪命,這便將小說的發展推向了高潮,更是由此展開了人性的善與惡、欲望與良知的較量。
一、多種寫作視角的交互運用
遲子建的小說地點多發生在她熟悉的東北黑土地上,《白銀那》中的白銀那就是座落在黑龍江上游的一個小村子,小說的故事情節內容也是由此展開,其敘述的手法也多樣化,充實了小說的可讀性。這篇小說的一個獨特之處就是有兩種視角,一是全知全能的視角,多角度,全方位的介紹白銀那以及發生在那里的事;一是外來訪問者古修竹的視角,古修竹以日記的形式用第一人稱描述了在白銀那短暫居住的所見所聞所感。這兩種視角相輔相成,互相補充印證,使小說敘述故事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切入,同時以旁觀者局外人的身份對這里發生的一切,進行切身的感受與評述,使作品情感得到升華。
全知視角的應用表現在敘述者的視野覆蓋著白銀那人,如同一架攝像機可以自由進去白銀那的家家戶戶,進去他們的內心世界。采用這樣一種俯視的視角來觀察著白銀那的動態,能很好的記錄每天發生的事件,使故事情節更加連貫有序。遲子建在構思這篇小說的時候目光不僅局限于一種敘述視角,全知視角固然可以全方位的敘述,但是對于作品中人物的內心世界還是很難表現出來的,所以作者又巧妙的融入了另一種日記體的敘述視角。這種獨特的敘述方式能更加全面的勾勒出小說的整體框架。在小說中全知視角和古修竹的日記相得益彰,客觀之中夾帶著主觀,能將白銀那這里發生的種種和人物的內心世界呈現出來。
除了采用全知視角和日記體的敘述視角,作者還精巧地利用順敘和插敘的交替互補及時間橫面的跨度,有效地控制了作品的節奏。從白銀那發生漁汛到馬占軍夫婦抬高鹽價間接使卡佳遇難,這些作者都是采用順序的手法來寫,而對于卡佳為什么來到白銀那這段描寫則是采用了插敘手法,就好比一條平靜向前的小何中突然激起一朵浪花,使從容徐緩的的文風節奏更加具有跳躍感。
二、充滿溫情主義的書寫
遲子建的小說立足民間生活,著眼于富有活力的大自然,一貫散透露著溫情的光輝。她曾說溫情的氣力就是批判的力量。溫情批判的矛頭始終指向兩個方向,一個是鄉土社會內部打亂人性溫情的因素,另一個是從根本上威脅著鄉土社會的外來現代城市文明。前一個因素,遲子建在小說《白銀那》中有充分的展示,馬占軍夫婦想通過暴利謀財的欲望試圖掙脫鄉土溫情的制約,便嚴重威脅鄉土社會的溫情世界。馬占軍夫婦破壞了白銀那固有的溫情,在人們享受漁汛帶來快樂之際故意抬高鹽價欲謀取暴利。遲子建筆下的白銀那是美麗的,永遠帶著好客的風俗。一些在多年以前曾經到過白銀那的人想要故地重游時都不免對著地圖發呆:白銀那哪兒去了?這時候熟悉那一帶漁民生活的人會爽朗地告訴你:“白銀那還在,快去吃那兒的開江魚吧,那里的牙各答酒美極了!”[1]白銀那的人們是善良的,他們的生活仰仗著大自然的恩賜,鄰里間相處和睦。
對于馬家夫婦遲子建主要著重他們”惡化——善化“的過程,以前馬占軍夫婦遇到鄰里左右出了紅白喜事也樂于出錢出物,但是由于馬占軍得了病,鄉親不愿意借錢才致使他們往”惡“的方向發展。對于馬占軍夫婦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惡“,作家還是采用充滿溫情主義的書寫去消解和感化人性中的”惡“,正如作者所說:對心酸生活的溫情表達卻是永遠都不會放棄的。
遲子建的小說寫作在滿懷溫情關懷的文字書寫中既不躲避現代文明對古典的充斥和人性陰暗面的揭露,又始終堅持積極、強健的價值取向和審美取向。白銀那這個村莊可以看做是原始風景的一種,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善良淳樸,但是能引起這個村莊絲絲漣漪的竟是與外界的隔絕。小說中的最大的矛盾就是人們打撈的魚卻無法把它們賣出去,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沒能向外界傳達消息。小說也有寫道;雖說白銀那通上了電,一些人家還擁有家用電器,一家鄉辦企業正要從閨中出門,但老人們仍覺得生活正在可怕的倒退。馬占軍夫婦設計使白銀那與外界失去聯系,讓他們賣不出去魚從而故意抬高鹽價,間接性的致使鄉長的妻子卡佳喪命。鄉長由最初對馬占軍夫婦的恨轉變為釋懷的諒解,這里面正是融入了作者的溫情主義書寫。這種溫情主義的書寫可以在《暢飲“天河之水“——遲子建訪談錄(代序)》中可以得以印證:如果說我沒有感受到生活中的“惡”,那絕對不是事實,我也曾在一篇隨筆中寫道:”我從來沒見過猙獰的鬼,卻遇見猙獰的人”,可我更信奉溫情的力量同時也就是批判的力量,法律永遠戰勝不了一個人內心道德的約束力。所以我特別喜歡讓“惡人“心靈發現”,我想世界上沒有徹底徹尾的“惡人“,他總有善良的一面會在不經意當中被挖掘出來。[2]
三、細節塑造人物
白銀那是側臥在黑龍江畔的偏僻、深遠、落后、美麗的小鎮,黑龍江養育著一代又代辛勤、仁慈、淳厚、樸實的鄉民,這個在地圖上沒有立足之地的小鎮,卻有很大的魅力,冰排、魚汛、牙各答酒、獨特的生活方式。然而,悠悠的江水、茂密的深山、神奇自然,并沒有給立足在那里的農民帶來福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他們仍然貧窮落后,和外界很少聯系的他們獨自承擔生活的艱難、不幸、屈辱。在小說的敘述中,馬占軍、馬川立、王德貴、卡佳、陳林月都是個性鮮明的人物,馬占軍的固執、“殘忍”、精明;馬川立的善良、執著、可愛;王德貴的大度、溫和、負責;卡佳的風情、溫柔、真誠;陳林月的純真、無邪、大方等,這些人物無不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者很是注重剪裁取舍和謀篇布局,它的每一個細節都是高質量的,從而保證了人物的生動、情節的縝密或意緒的流貫與意境的渾成。就拿作者寫馬川立和陳林月在黑夜中約會的甜蜜就充分利用了細節描寫,馬川立因為把河水里的冰排比作冰棺材而被陳林月搡了一把,他趔趄著一腳伸進冰冷的水里,被涼氣逼人的江水激得打了一個冷戰,就勢抱住陳林月讓她賠他身上的熱氣。當然那熱氣很快就在擁抱中回到他身上。這段逼真的細節描寫充分將兩人愛情中的甜蜜表現出來,同時也勾勒出了馬川立的可愛之處。
在塑造人物時,事件是最直接、最直觀體現人物性格的要素,作者在描敘這些事件很是細致,細節之中就將人物生動的塑造出來。對于卡佳的喪禮準備,鄉長的一系列表現都充分的體現了他對妻子的留戀和不舍。鄉長堅持要為卡佳打造一口新的棺材,因為她不喜歡用別人用過的東西,這些鄉長都記得并為她堅守著,這件細微之處就將二人間愛情的矢志不渝表現出來。
四、樸素的生活化語言
遲子建認為小說最終的好是樸素——語言、意境、用詞、生活態度,乃至人格,樸素是最高境界,樸素還是生活化的反映。《白銀那》的語言風格淳樸大方,精練流暢,語氣輕緩,飽含詩意美。發生在白銀那一樁樁難以忘卻的苦難記事,沒有對與錯正與邪善與惡的二元對立,在作者詩意的筆觸、語調中更多的是悲憫與同情,是對生命、人生的真誠的感受、體悟。作品寓苦難失意于詩情畫意中,在充分享受作者細膩、樸素、自然、詩意的描寫的同時,讓人心情逐漸的沉重起來,最終又脫離文本,引起對生命的思考。白銀那村莊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在作者樸素的語言表述中是如此的凄迷,如此的縈繞心懷,如此充滿魅力,如此的揮之不去。
小說生活化的語言中蘊含著強大的溫情力量,在鄉長的兒子準備給母親卡佳報仇時反問父親難道不恨馬家,鄉長一句樸素的話語:我這輩子最不喜歡聽“恨”這個字……雖然簡短的幾字卻將所有的仇恨化解,這句話不是什么驚天動地的話語,但從鄉長口中說出來,使人物形象籠罩著人性的溫情之光,在繁瑣、庸常的生活中安慰人心,給人帶去希冀。
五、人文關懷的流露
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壇的創作精神不斷變化著,小說創作逐漸的從一種“共同的話語”空間中剝離出來,向普通化、世俗化、商業化靠攏時,遲子健仍然堅守著作家的藝術良知,不媚俗、不惑眾,在創作中始終保持著高品位的審美追求,不忘初心的追求著自己靈魂精神的歸宿。在遲子建的作品中,有著對鄉村世界中人與人相互眷注的深入窺探。在中篇小說《白銀那》中,遲子建以直接的生活事件、藝術形象和環境描寫,通過人性和物欲的激烈沖突,抒發了對理想化的人際關系,對良善、饒恕、和諧向往的祈望。
在這篇近乎寓言的故事內容,既有對鄉民寢露品德的剖析,更有含有遲子建溫和的寬宥和悲憫,從而高高舉起了人文關懷的旌旗。遲子建曾這樣解釋她對鄉民生活的認識:“中國老百姓大多數都是處在這么一種尷尬狀態中:既不是大惡也不是大善,他們都是有缺點的好人,生活得有喜有憂,他們沒有權也沒有勢,徹底沒有資本,他不能做一個完全的善人或惡人,只能用小聰明小心眼小把戲,以不正當手段為自己謀取利益,在這一過程中,他會左右為難備受良心折磨,處在非常尷尬的狀態中。[3]遲子建對人性有著很高的期望,她”要把一個沾滿陋習的人身上那僅有的人性美發掘出來,以求溶化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堅冰。人與人之間應該多一些眷注和體解,少一些狐疑和痛恨,這樣才能讓生活中多點幸福感與和諧美,才能實現在互相尊重個性和精神個性的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包容、將心比心和認可。
六、結語
小說的開頭作者就交代白銀那村莊坐落在黑龍江的上游,這里的白銀那表征著傳統與現代碰撞中的人性美的回歸,河流的出現使得遲子建小說中的白銀那具有了亙古不變的滄桑感,它承載著對漂浮魂靈的安慰和塑造精神家園的重擔。在主題內涵上,作品中處處彌漫著真、善、美的情懷和溫潤的憂愁,展示了作家對自然的屬意、對生命的感悟和對愛的追隨。全知視角和日記體的相得益彰使小說的敘事更加富有張力,滿含人文關懷的溫情書寫,樸素生活化的語言和各色各樣的人物形象在《白銀那》中得以充分體現,這些無疑是作家卓越的創作特色的展現。
在當代文壇中,遲子建的創作風格是極具特色的,通過小說展現出的那樸實而原始的北國風采、那蒼涼而溫情的敘述風格,我們能切身地體會到來自作家靈魂深處的傷懷之美,給小說抹上一層溫情而憂傷的背景色,具體體現為有靈性的自然、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以及對死亡平淡的敘述,這些都試遲子建的小說創作更加具有深度和可讀性。
【參考文獻】
[1]遲子建.中國當代作家選集叢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6.
[2]遲子建.中國當代作家選集叢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353.
[3]遲子建,阿成,張英.溫情的力量——遲子建訪談錄[J].作家,1999,(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