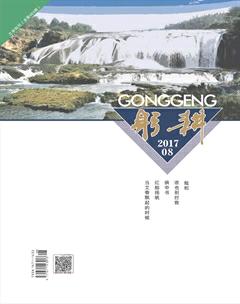籬笆、泥巴與炊煙
逯玉克
籬笆
籬笆,是村莊粗布衣衫的一塊補丁?還是鄉村秀發上一枚發卡?
舊時,鄉村的庭院和鄉野,籬笆是很常見的。
籬笆,其實也是一種墻,只是它不能承重,只起隔離作用。那時,磚墻極少,大多是磚石根基的土坯墻。土坯墻厚實,但筑起來太耗費人力錢財。莊戶人家日子緊巴,奢侈不起,他們只好扎起籬笆。費些力氣,不用花錢的。那年頭,力氣也不值錢。
材料嘛,當然是就地取了,樹枝、玉米桿、高粱桿,逮誰是誰。南方的籬笆用竹片,我們這兒沒有,有也舍不得。籬笆扎起來也不難,先是挖一溜半尺深的溝,再每隔一段距離埋一根木樁,然后將那些樹枝、作物桿莖什么的在溝里埋好踩實,上邊再束上腰,固定在木樁上,籬笆就算是扎成了。
籬笆和厚道的鄉親一樣好說話,門前院后,土坡溝底,哪兒都可安家。在村里,籬笆通常只有半人或一人高,主要用來防止禽畜。如果防人,決不是不可逾越,它更多的是一種象征意義,告訴人們,這兒是我的領地。籬笆這種樸素的語言,連那些不識字的鄉親都看得懂。
其實,鄉親的心中也有一道籬笆,在他們心中扎了多少年了,那就是傳統的道德,世代相傳,就形成了淳樸的民風。即便是淘氣的孩子,見到那些一躍即過的簡易籬笆,也是心存敬畏的,因為,他邁不過心中的那道籬笆。
勤勞的人家,會隨著時令在籬笆旁種上眉豆、豆角、倭瓜、絲瓜、葫蘆、燒湯花、美人蕉等。當然,有些花是不需要種的,如牽牛花,總是不請自到,所以古人有“牽牛延蔓繞籬笆”的詩句。
籬笆朝陽的那面種滿了花果,主人家洗碗刷鍋的水就有傾倒的地方了。籬笆也隨和,從不說什么。任性的風可以曲徑通幽溜進來,調皮的光可以見縫插針擠進來,甚至,孩童還可以童言無忌把尿撒在這兒來個雨打芭蕉。
青藤纏繞,綠葉婆娑,于是,鄉村籬笆,成了一道綠色的屏風,春夏疏疏落落開幾番花,秋來半掩半映掛一架果。即使到了冬天,籬笆掛滿枯藤敗葉,一派灰黑的水墨色,猶能留得殘荷聽雨聲呢。
要做飯了,好說,到籬笆邊,隨手摘一把豆角或掐一把南瓜花,或炒或涮。平時,鄰里鄉親路過,順手摘些蕓豆什么的,是沒有人計較的。雖然籬笆隔出了院里與院外,但人老幾輩,鄰里鄉親那份親情恩怨,就像籬笆上纏繞的藤蔓,沒法分太清的。
庭院的籬笆,蓄滿了莊戶人家天倫親情的煙火味道,而鄉野的籬笆,里里外外,滿是靜謐悠遠的田園風光。有籬笆,就會有柴扉,就會有茅屋,就會有小徑。倘是菜園,就會有流水,若是果園,就會有在林間辛勤勞作或抽煙歇息的農人,就有枝頭啁啾的小鳥,還有草叢悠閑覓食的土雞,還會有吠叫著不知從什么地方竄出嚇你一跳的黃狗,碰巧了,興許還會遇到主人家臥剝蓮蓬的無賴孩童呢。
有一種籬笆,其完美堪稱極品。鄉野果園四周,密密栽種一圈花椒樹,花椒樹的枝條多得像千手觀音,幾年下來,長得蓊蓊郁郁,無數帶刺的枝條交錯纏繞,城墻一般,別說人,連條狗鉆進去都難。夏秋季節,花椒成熟,整個果園都彌散著獨特濃烈的香味。花椒采摘下來,又是一筆不菲的收入。這種花椒籬笆越長越高大密實,根本無法逾越,也不用擔心破舊損壞維修什么的,既看家護院,還能收獲果實,真是一舉兩得。
一村人家、幾縷炊煙、幾畦菜地、幾道籬笆。清苦的歲月里,炊煙,裊娜成鄉村的羊角辮,籬笆,則美麗成鄉村秀發上的一枚發卡。
籬笆,守護著莊戶人家透風漏雨磕磕絆絆的貧窮日子,守護著鄉村泥土芬芳的原生態,守護著鄰里鄉親淳樸的民風。后來,隨著時代的變革,籬笆,被土地流轉的大潮沖蕩了,成為社區整齊劃一的鐵欄,成為高樓內陽臺漂亮的圍欄,成為各家各戶嚴實如籠的防盜窗。
住進高樓的鄉親日子充裕了,但他們總覺得少了什么。少了什么呢?過去,鄉親們隔著籬笆就可以跟鄰居拉家常,端起碗走幾步就能湊到一塊話桑麻,如今,那樣的日子成了遙遠的童話,平日大家都忙忙碌碌,很少走動了。有吃有喝的,有住有穿的,可咋就老是忖著哪兒不得勁,感覺心里空落落的呢?
于是,他們又想起了被籬笆圍起的日子。曾經的籬笆,爬滿藤蘿開著鮮花結著豆莢的籬笆,“秋菊繞舍似陶家”。搖曳著鄉村風情的籬笆,成了記憶中牛背牧童的那支短笛,信口無腔的質樸與悠揚,霜雪一般,月色一般,飄散融化在歲月的深處,撿拾不回了。
籬笆,鄉村的一抹風情,歲月的一闋小令,人在高樓悵然遠望時老家上空那縷漫卷的鄉愁……
泥濘
泥濘,是鄉村特有的一塊胎記。
鄉村喜歡雨。靠天吃飯的年代,雨是上蒼的恩賜,當山地、丘陵、平原、河川,那滿眼的莊稼被一片如煙的雨幕籠罩時,村村寨寨的鄉親也被欣幸與愜意籠罩了。
雨下在田里是甘霖,下在路上便成了泥濘。
鄉下是土的世界,街道院落、田間小徑、出村大路,全是黃土鋪墊的,經不起雨的浸淫。一場雨就能把平日硬實的路面泡得黏黏糊糊,如果連下幾天,鄉下人就會被困在村子里,沒有關緊事,一般是不出門的。但迫于生計,鄉親們閑不住,也閑不起,一年四季總是風里來雨里去。這下路就遭災了,來來去去的人走過,總是踩出一溜歪歪扭扭深深淺淺的腳窩,鞋被泥巴糊涂得看不出模樣,褲腿也濺滿了泥點。要是不小心摔一跤,弄半身水淋淋臟兮兮的泥水,那就狼狽到家了。最糟糕的是馬車或拖拉機碾過,路會被軋出幾道深深的車轍,水積在那里幾天都不干,像是沒有愈合的傷口。拖拉機還能憑著一身蠻力,不管不顧地冒著黑煙聲嘶力竭地掙扎著過去,小汽車呢,底盤太低,容易擱淺,就只能望路興嘆,矜持著它斯文優雅的貴族氣質了。
泥濘的土路被曬干風干后還保持著當初慘遭蹂躪的模樣,這就叫坎坷。
坎坷,是泥濘的固化,它以另一種形式延續著行路的艱難。多年前,一個窯匠的一車瓦罐瓦盆翻倒在路上,多日摳土挖泥兩鬢蒼蒼十指黑的辛苦,化作坑坑洼洼中的一堆瓦礫,我至今仍記得他氣惱懊喪無助悲戚的眼神。
古代,乘車是一種身份和地位的顯示,風光是肯定的,但舒服與否,那要看路況了。笨拙的木輪或鐵輪在波峰浪谷的路上顛來簸去也未必好受吧,所以,陶淵明才“安步以當車”呢。
小時候,村南二里外用鵝卵石、料礓、砂礫鋪成的石子馬路,已是我所見到的最為高級的路了,雖也不甚平整,但畢竟不怕雨了。下著雨,上面還不耽擱跑車呢。遇著水坑兒,汽車也不減速,還會表演似的驕傲地濺起一片水花呢。
后來,石子路加寬墊高裁彎取直修成了柏油路。哪見過這么好的路啊!又寬又平的柏油路讓鄉下人驚喜不已。再后來,鄉下好多村道也鋪上了水泥,鄉親再不用因泥濘而扛著自行車回家了。
兒時的鄉間土路,泥濘坎坷里,滿是生存的艱辛。現在明白,泥濘坎坷是無處不在的,只不過,它以另一種形式出現或潛伏而已。
炊煙
記憶中,有一首鄉韻濃濃伴我成長的歌謠,依依裊娜在故鄉的上空,那便是:炊煙。
裊裊的炊煙,那是煙的舞蹈吧,那是流向天上的小溪吧。
炊煙來自哪里?來自灶臺。孩子們可能會一臉的陌生,灶臺是什么?現在,恐怕只有民俗博物館里才有吧,但半個世紀前,那可是鄉下家家戶戶必備的做飯工具。
貧瘠的鄉下,燒煤是件很奢侈的事,做飯的主要燃料只能是柴草,而在林木稀少的平原地帶,就連柴草的獲得也并不容易。兒女相親,有心人從對方門前或院內柴草跺的大小和齊整與否上,就能看出這戶人家是否勤儉會過日子。
孩提時,每到放學,我們就結伴到野外打豬草、挖野菜、撿柴禾,只要一抬頭看見夕陽西下,村莊上空炊煙升起,就知道那是母親在招手喊我們回家吃飯啦。
炊煙里,有飯菜的香味,炊煙里,有母親的呼喚。
炊煙消散在何處?只知道風把它們帶到了天上,那煙一樣悠然舒卷的云,是人間萬家炊煙的歸宿?還是天上仙人的炊煙?
飯做好后,灶中火炭尚未全熄,我們會取一個紅薯埋進去。一頓飯吃完,就會有濃濃的烤紅薯的香味彌漫出鄉村農家的味道。
而飯后的父親,總是夾一塊火炭點燃他的煙斗,坐靠在土墻根的一塊石頭上吞云吐霧,過往歲月里多少往事,成了他口中不絕如縷的裊裊香煙。
那些柴禾,大半燃成了火,三分飄成了煙,剩下一點便是草木灰了。百畝之田糞當先,草木灰是上好的肥料,鄉下人是從來舍不得扔的。
后來,30里開外的萬安山開挖了煤礦,鄉下人大都壘起新式灶臺,先用散煤,后改用煤球,那攜裹著飯香的裊裊炊煙,那滿是煙火色的黢黑土墻,被歲月之風吹得沒了蹤影。
只有野煙依舊瀟灑在山林曠野上空,抒寫著鄉村特有的田園詩意。
秋高氣爽云淡風輕的秋天,山野、河畔、田間地頭,常有野煙如衣袂飄飄的飛天仙女,變幻著曼妙的舞姿隨風斜升裊娜入云,也許是貪玩的牧童點燃了一片荒草,也許是勞作的鄉親燃起了從將要深翻的土地里清理出的莊稼根莖和雜草。縹緲的云煙,把遠山近樹,曠野阡陌,中國畫般浸染出“隱隱飛橋隔野煙”的悠遠詩意。
炊煙,是溫馨的,裊娜著清苦歲月里的鄉韻親情,父親的辛勞在里面,母親的慈愛在里面,童年的記憶在里面。
野煙,是詩意的,曠野長天,幾處云煙繚繞,隨風而飄,隨風而逝,點綴了秋野的空曠,涂抹出季節的自然之美悠然之趣。
炊煙,是一曲田園詩般深情的老歌;
野煙,是一幅悠遠淡雅的山水畫卷。
煙,從化學成分說,不是什么好東西,但它曾經承載著人類的文明。最初的一縷炊煙,讓人類開始走出茹毛飲血的蠻荒時代。現在,工業煙囪里的滾滾濃煙讓我們困惑無奈,戰火硝煙尤讓人糾結心悸。
只有炊煙,能帶給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的深深懷念和溫馨感動,只有野煙,能帶給我自然的親切質樸和浪漫詩意的遐想。
炊煙生處有人家。炊煙相招,鴿哨相邀,那是一幅多么溫馨醉人的游子歸鄉圖啊。
人間煙火,其原意是否就指裊裊炊煙和萬家燈火呢?
居家過日,一日三餐,炊煙應是最具人間煙火味的。
遺憾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許多古典的詩意的飽含多少代人記憶和感情的東西,正悄然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如炊煙、漁火、野渡、扁舟、山歌、民謠、習俗……
哪片煙云下,才是我記憶中的故鄉?
故鄉的溝壑,多了一座父親的墳塋,再也見不到父親煙斗里那小溪般的裊裊香煙,只有清明時節兒女哀思綿綿的如煙細雨。
炊煙,那是過往歲月一縷悠遠記憶吧,那是逝去的親人放不下的牽掛吧,但故鄉的天空,已然沒有了炊煙的纏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