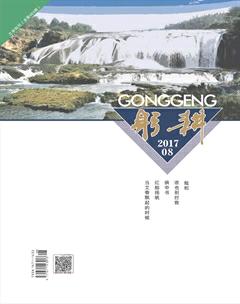當艾香飄起的時候
包簡
當我在門頭插上艾草,吃上用艾葉煮好的雞蛋、粽子和蒜頭時,又一年的端午節就這么來了。
秦皇島本地沒有端午節煮蒜頭的習俗,似乎很多地方都沒有,這種吃法自然是來自我的故鄉。扒開一瓣軟泥般的蒜粒放在口中,聞著艾草的清香,便想起了我的故鄉。
我的故鄉是豫西南地區的一片寬闊平原,土地平整肥沃,北面遠山依稀,日夜不停的趙河水在村東流淌了許多個世紀。
故鄉的五月初五不叫端午節,而是叫做五月當午。
那正是麥子成熟的季節,平日里被當作雜物的艾草,這時候就變得格外稀罕起來。田埂上,地頭上,河溝旁,到處都長滿了艾草。它那濃郁的清香四處彌漫著,飄過河畔,飄過麥田,飄過村外的樹林,飄進院子里,透過窗戶飄進屋子里,仿佛在向孩子們傳達著五月當午來臨的消息。
天亮的很早,艾草的香味和布谷鳥的叫聲把我們從夢中早早喚醒,手脖腳脖上是頭天夜晚母親趁我們熟睡時綁上的五色線,床頭桌子上擺著母親用艾草和蒜梃新做的料布袋兒,屋外門窗頂上都插上了艾草。
當院里的石臺子上,放著一桶香噴噴的洗臉水,那是昨晚我們將新采來的棗葉、核桃葉、柿葉、石榴葉、艾葉混放進滿滿的水桶里,經過一夜的月光和露水滋養制作成的“五香水”,濃香清涼,聞一聞洗一洗神清氣爽,五毒不犯。我們從小就聽說,月亮里的黑影是一位彎腰搗制仙藥的月奶奶,她一年到頭搗藥不停,直到每年五月當午夜里才會把搗好的仙藥撒向人間,撒進院子里的水桶水盆里,撒在路邊密密麻麻的草尖上,人們可以用來祛除各種毒氣和邪病。
洗完“五香水”的臉,抱著小妹在灶火屋做飯的母親便對我們說:都出去洗個露水澡吧。
要洗的當然是月奶奶將仙藥撒在路邊草尖上的露水,最好是地頭小路上的蛤蟆皮草。兒時的我曾一直模糊地以為,月奶奶的“仙露”摻合著癩蛤蟆爬過草尖時留下的唾液驅毒更好。
我和弟弟光著膀子,每人拿條干毛巾,跑到村口偏僻的小路上,選塊干凈的蛤蟆皮草,用毛巾蘸著草尖上晶瑩的“仙露”,渾身上下搓洗起來。毛巾濕漉漉、冰冰涼的,冷得我們咬著牙關直哆嗦,但心里卻無比高興,總是一邊洗一邊逗著笑:
“弟,你冷不冷?”
“不冷。”
“不冷你咋哆嗦哩!”
“哥,那你冷不冷?”
“俺真的不冷。”
“不信,騙我吧,不冷你牙咋打架哩!”
回到家穿好衣服,母親已經將早飯端到當院石臺上:一盆艾葉煮蒜頭,一盆煮雞蛋和咸鴨蛋,兩碗小米綠豆粥,一碗煮羊奶,還有一碗雄黃酒。那時候我還沒聽說過有粽子,后來直到上中學才知道端午節、屈原和炯子的說法,上了高中才在學校食堂里明白了原來炯子就是糯米做成的粽子。
我們猴急般地坐下,拿起雞蛋嘎嘎笑著互相對撞起來,碎了再換新的撞,不一會就撞碎了七八個。正在喂雞的母親看到就訓斥我們:
“先抹雄黃再吃飯!自各撞的雞蛋自各吃,撞恁些能吃完嗎!”
我們搶著回答:“俺一人能吃七個,倆人能吃十多個,這還不到九個哩。”
按照母親的吩咐,正式吃飯之前,我倆先互相給對方抹雄黃,用艾葉蘸著雄黃酒,抹在對方的耳朵眼、鼻孔和肚臍上,據說可以驅毒防蟲吧。
平日吃不到雞蛋的我,一口氣就吃了五個雞蛋,兩個咸鴨蛋,三頭煮蒜,還有滿滿一碗綠豆小米粥,半碗煮羊奶。六歲的弟弟只比我少吃了一個咸鴨蛋。
吃過早飯,脖子上掛上料布袋兒,我和弟弟拎上飯盆飯缸,去村東河灘上給父親他們去送飯。
成熟的麥子不等人,各家都在搶時間忙收割,父親、爺爺和十來歲的姐姐一大早就去河灘割麥子了。
三里地的路,走到時已經累得我倆氣喘吁吁。
太陽很高了,熱辣辣地照著黃澄澄的麥田,熱氣蒸騰起來,路邊的艾草混合著麥田的味道,濃烈地鉆進我們的鼻孔里。布谷鳥“不夠不夠”地叫著,偶爾一群麻雀從眼前掠過。
父親他們已經割完了一大半,正蹲著腰捆麥個。我家的老山羊被拴在地頭楊樹下,不緊不慢地吃著地上五月當午的艾草。剛生下不久的小羊圍著老羊又蹦又跳的,見到我們便咩咩地直叫喚,好像知道有人帶好吃的來了。
姐姐坐在麥個上低頭玩著,看到我們送飯來,趕忙跑過來,手里似乎捧著什么。
“咋才送飯來呀?我都餓得啃半塊饃了!”
“快瞅這是啥?”她一邊埋怨著,一邊攤開手掌讓我們看。
“誰街倆雞娃兒跑地里了?”我吃驚地問。
“這是鵪鶉娃兒,我瞅見的。”姐姐一臉得意。
天哪!還真是兩只小鵪鶉!毛茸茸的,灰里帶黃的小小鳥,圓圓的小眼睛,連嘴叉子都是初生的黃。以前遇到過會飛的大鵪鶉,這么小的鵪鶉我還是頭一次看到。
爺爺老遠招呼我們,到跟前了,他指著地上說:你倆一人一窩,帶回家明天煮吃嘍。
原來是爺爺割麥割出來的兩窩鵪鶉蛋。
父親他們開始吃煮蒜頭和雞蛋了。我和弟弟拿起他們的鐮刀也割起麥子來,一人兩壟,生硬而賣力地割著。我們也想割出一窩小鵪鶉來。
父親邊吃邊朝我們喊:“瞅住點,白割住手腳嘍!”
忙活半天,不但沒割到小鵪鶉,連一窩鵪鶉蛋也沒割到,最后只看到一只圓嘟嘟的老鵪鶉,撲楞著翅膀貼著麥地直直飛走了。
“你倆別割了,去把河邊把飯盆刷刷,再舀點水回來飲飲羊吧。”父親要過我們的鐮刀,就把我們打發走了。
河邊離我家地頭很近,走過稀稀拉拉的楊樹林就是河灘,河水正嘩嘩地響著,遠處幾只水鳥伴著清脆的鳴叫不時飛起飛落。當我們快到河邊時,姐姐拿著鐮刀追了上來,說是大人們不放心,讓她過來瞅著我倆。
這一段河水很寬,但是很淺,剛剛能沒過膝蓋,姐姐以前總帶我在這里摸螃蟹。
“姐,咱們再摸點螃蟹,擱飯缸里帶回去吧。”
刷完飯盆飯缸,在我的提議下我們摸起了螃蟹。河里幾乎每塊石頭下面,都住著一兩只螃蟹,有的會在我們翻開石頭的瞬間趁著混水快速逃走,有的只會靜靜呆著一動不動,或是舉著兩個鉗子等著我們去捉,但也有被它夾住手指的時候。翻了一會石頭,我干脆拿起姐姐的鐮刀在河岸邊挖起螃蟹洞來,有時一窩能挖出許多只螃蟹。
還沒到中午,我們就捉了滿滿兩飯缸螃蟹,飯盆里也有很多只。直到父親牽著羊過來飲水,我們才想起要舀水飲羊的事情。
吃飽了艾草的老山羊酣暢淋漓地喝著河水,時而抬頭叫喚下它歡實的小羊羔,嘴里的河水順著它的胡子流淌下來,連同嘴里的艾葉渣子都流進河里,順流而下,漂向遠遠的長江大海。
喝趙河水吃艾草葉的山羊下著艾香味的羊奶,小羊羔歡快地吮吸著,多余的羊奶每天早上又供著我們幾個分享,這在平日吃不到肉和雞蛋的童年歲月里,無疑是最美味最有營養的滋補品。艾草滋養著山羊,羊奶滋養著我們。若干年后,我們的子侄又喝著它后代的羊奶健康長大,如今年邁的老父親也靠這艾香的羊奶補養著他多病的身體。
端午時節,五毒出蟄,陰濕上升,老天便把吉祥的艾草賜給了我們,艾草、煮蒜、雄黃和五香水也自然成了避邪祛毒、彰顯正氣的一種文化。這些端午文化既是一個村莊或一個地區的習俗,也是種族繁衍的象征,更是華夏民族屹立于世界的標志性符號。
每年端午,艾草的清香便會從故鄉飄起,飄向各地,由北向南,自東到西,世代相傳而生息不止。
“你也吃一瓣吧。”我掰下一粒煮蒜遞給了孩子。